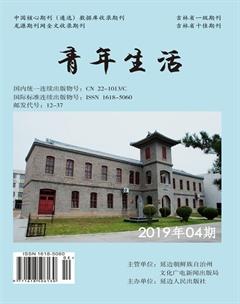寬容精神的憲法解讀
周媛
美國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龍在《寬容》一書中曾指出:“寬容就是毫無偏見地包容與自己觀點相異的見解與主張,對他人的行為與自由予以充分的尊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從人類決定共同生活的那一刻起,“寬容精神”就已經扎根。小到日常的生活習慣不同,大到人生觀價值觀相異,寬容精神讓我們“求同存異”。
若從憲法角度對寬容進行解讀,宏觀上看,憲法是寬容的產物。例如,美國憲法就是各個州代表相互寬容和妥協的結果。“參與立憲的利益(或利益集團)是多元的,立憲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協商和妥協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憲法必然是一個多元利益相互妥協的產物。”[1]
可是,作為憲政意義上的寬容并非毫無界限,并非毫無原則,劃定寬容之界的標準應是我們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但基本人權之寬,泛泛而談意義甚微。筆者認為,在基本人權中,公民的信仰是憲法對寬容精神最好的體現。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了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政府通過具有監聽、監視功能的“電幕”控制人們的行為,嚴厲打擊思想上的異端分子。信仰作為一種世界觀,能夠決定一個人的人生道路,若是憲法在這一個層面上“放手”,則是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寬容。因此,筆者將從各國憲法中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權這一視角,來解讀到底什么是寬容精神。
(一)寬容精神以自由為基礎
縱觀寬容和宗教的歷史淵源,從米蘭寬敕令到奧古斯堡教自由,從法王亨利四世的南特敕令到英格蘭國會通過的寬容法,再到神圣羅馬帝國約瑟夫二世頒寬容令,給予不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一定信仰自由,許多自由權利伴隨著寬容而來。例如,在受教育的權利中,涉及宗教教室是否需要懸掛十字架等問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于1995 年所作成的“十字架案”裁定認為,法院有義務在宗教上保持中立,從而不能作成在教室內懸掛十字架的命令。
再來看英國,1215年頒布的《自由大憲章》第1條中即規定,“教會根據憲章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不受干擾和侵犯。”英國光榮革命勝利后頒布的《權利法案》進一步明確規定:“設立審理宗教事務之欽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它同類指令與法庭,皆為非法而有害。”1689年,英國通過了《容忍法案》,承認了各教派的存在,而不再視異教為邪教。
由此可見,憲法上對公民宗教信仰的寬容程度慢慢加大,從強制人民信仰某一個教派,到強制人們信仰某一些教派,再到承認其他教派的合法性,最后不強制人們信教。宗教自由首先是信仰和思想上的自由,但其價值并不局限在此,而應該囊括所有表達宗教信仰的自由,即宗教行為自由,如參加宗教儀式、出版宗教書籍、傳播宗教等。實際上,人民在宗教問題上,被憲法賦予了極大的自由選擇權。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就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指出:“在一個有法律的國家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一國憲法能夠容許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予以支持,實質上是國家對公民的寬容,并將這部分的自由權送還到公民手中。
(二)寬容精神為以平等為目標
1786年,在杰斐遜和麥迪遜的領導下,弗吉尼亞州率先通過了《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這一法案對于當時其它各州具有很大的影響,并成為后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藍本。該法案指出:每個人都有不被強迫地參加、支持或宣揚任何一種宗教崇拜的自由,而且不應該因宗教見解或信仰受到身體或財產上的損害,或因此削減、擴大,或影響到他的公民權利。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我國《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第四條規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公民。”1982年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托馬斯弗萊納在《人權是什么》說,“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各種宗教都被作為人類多樣性和人格尊嚴的一部分受到尊重的社會氣氛中,才能得到實現。”寬容精神的精神并非局限于“從封閉到開放”,從“禁止到允許”,而應該側重于“尊重”。“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寬容理應做到如此,不要求完全認可對方的信仰,但必須認同無論所信何教,我們都是平等的。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少數人群體,通常我們不會直接干涉他們的權利,但會在其他領域將其排除在外,特別在涉及到主觀選擇時,我們傾向于不接納他們。如此一來,宗教信仰自由權只是在法律層面開了一道小門,擁有主流價值觀的人們從正門走,少數人群體只能從側門彎腰通過,這當然不是寬容精神的含義。因此,寬容精神是以平等為目標的,如《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等法案一樣,點明“無論宗教信仰,人人一律平等”至關重要。
(三)寬容精神的最后底線
我國1982憲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信仰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之時,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德國憲法也規定,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時不得損害他人的人格尊嚴。
由此可見,我們對寬容精神是有要求的,對于有損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與權利不予寬容;對于違反和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行為不予寬容。“你的權利止于我的鼻尖”,寬容精神的最后底線就是“拳頭和鼻尖的距離”。人人有權截然不同,并保持平等關系,然而一旦你的權利使我受到了損害,那么就打破了寬容精神的最后一道防線。
綜上,以宗教信仰自由權的演變為視角,寬容精神在憲法層面有三個基本特征:以自由為基礎,以平等為特征,以不損害國家、社會、他人為底線。筆者希望,沐浴著寬容之風,憲政道路越走越長,越走越好。
注文:[1]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
參考文獻:
[1]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2]許育典:《宗教自由與宗教法》,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
[3]劉潤仙:《論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5.
[4]《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陳建樾:《以制度和法治保護少數民族權利——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路徑與經驗》,載《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6]江國華:《憲法哲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7]黃溫泉:《論憲政的寬容精神——從和諧社會的視角看寬容的憲政價值》,載《人大研究》2009年第8期.
[8]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
[9]W.湯普森:《憲法的政治理論》,張志銘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10]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