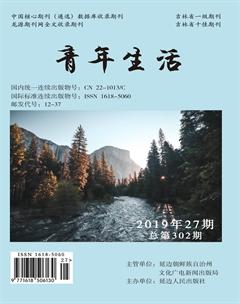“工匠精神”內在發生機制的歷史嬗變
李海潔
摘要:“工匠精神”內在發生機制的歷史演進,分別經歷了萌芽、發展和成熟階段。它在農業社會封閉的整體環境和蒙昧的主體意識中緩慢萌動,在大機器生產的板直化評價環境中曲折發展,自覺并最終成熟于知識經濟時代技術人才主體價值的確立。可以說,現代工匠精神的回歸是生態自由意志的生成。在它的引領下,技術主體逐步超越功利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傳統觀念,遵循公正性和完整理性原則,以自我價值的肯定和追求人的幸福為目標。
關鍵詞:“工匠精神”;發生機制;歷史嬗變;當代意義
“工匠精神”的發生與形成,是社會機制與個人主體精神相互制約、影響并共同發展的產物。作為一種民族性的文化,“工匠精神”的凝聚必須通過鮮活的個體生命的存在而得以凸顯,并最終形成為具有國民性格和普遍社會心理意識的民族精神依托和群體力量。其萌動、發展到確立的歷史進程,首先受到社會歷史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約;同時,主體經驗的積累和思維的反饋、過濾、轉換,又構成了“工匠精神”及其相應文化形成的內在動力。可以說,工匠精神內在發生機制的嬗變歷程,正是人類直面艱難卻永不停歇地追求實現個體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傳統農業社會視閾下“工匠精神”的缺失
傳統農業社會時期,生產技術發展緩慢,社會系統結構并不完善,缺乏廣泛社會意義的價值評價體系;該時期從事家庭手工業的勞動者,往往還處于原始的集體無意識狀態。可以說,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尚不具備工匠精神形成與發展的客觀條件。
人類從事手工生產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茹毛飲血的混沌時代。就世界范圍來看,自遠古石器時代開始,打磨石器便成為了部落、氏族社會中存在的主要手工生產勞動形式。隨著銅、鐵等工具的普及使用,家庭成為了封建社會時期生產形式的最基本單位,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亞洲的村社以及歐洲的莊園,與之相適應的出現了獨立或依附于農業家庭的手工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決定了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時期,家庭手工業始終是最主要的生產方式。
以家傳世學為主要特征的家庭手工作坊,往往借助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集生產、生活與分配為一體。傳承關系限定在嚴格的范圍之內,依靠生存環境而逐漸形成具有職業特色的家庭團體,相關技藝為內部所有,只能在封閉環境中傳播。這種初級的、非制度化的傳習形態,不僅嚴重制約著社會分工模式,還在某種程度上限制著社會的整體流動。因此,農業社會時期的階級階層之間往往壁壘森嚴。在家庭手工業為主的生產模式制約下,社會分工極度不發達,社會分化程度低下。相關的競爭與淘汰機制無法建立健全,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也非常遲緩。
具體到中國古代社會,傳統的封閉文化特質和生存環境,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工匠”主體身份的確立。由于農業社會手工業生產者的經驗傳授,往往以基本的生存技能為主。相關經驗的積累,必須通過生活、勞動過程傳授給下一代,而生存經驗代際傳遞的主要方式在于演示和模仿。所謂“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的情形更是普遍存在。不但傳統匠人的職業地位低下,處于社會分工的底層位置;許多精妙絕倫的技藝,亦被視為“奇巧淫技”,難登大雅。
尤其是在“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的基本前提下,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衍生出較為保守的意識形態結構。在個人的價值取向方面,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等謀求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統一的基本觀念。其所尋覓的是一種中庸、調和的途徑,培養個人的群體意識、順從意識,反對個人獨立意志和銳意進取。在這種倫理道德關系與價值判斷系統的影響下,手工業者的自我意識仍未完全覺醒,“工匠”的主體身份并未得到真正確立。自我主體意識的缺失,極大地限制了傳統手工業者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責任觀念和理性精神。因此難以形成潛意識中時刻影響和約束個體思想行為的深層文化,更無法升華為具有個人信仰性質的職業精神。可見,農業社會背景下的傳統手工業,顯然并不具備凝聚“工匠精神”的基本前提。
二、工業時代背景下主體意識的發展與消減
工業革命以后的大機器時代,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社會分工漸趨細密。傳統手工業逐漸被機器大工廠所取代。社會評價機制的發展、完善與固化,一方面促進了工匠個體意識的發展和形成,同時又限制和制約了“工匠精神”內涵的進一步提升。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在英國萌芽,遂以破竹之勢蔓延歐陸,席卷全球。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手工生產,是工業革命的最主要標志。這不僅僅是一場生產與技術的革命,更是社會關系的深刻變革。由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巨大變化,促使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場逐漸被大機器生產所取代,同時也加速了行業內部產業分工的形成。
工業社會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的生產組織形式,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手工作坊的要求,它首先在數量和質量上追求人才的大批量和標準化。同時,產業分工的進一步細化,產生了許多獨立的學科知識體系,從生產中分離出的科技成就,又進一步推進了專業分工的精致化和物質生產的豐富。機械化生產需要的,是大量有文化、有知識的技術工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技術崗位,更需要專精的產業技術知識和實踐能力。在類似的背景要求下,以傳授科學原理和生產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現代職業技術教育應運而生,人才培養與評價機制也得到逐步確立。此外,專利與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法律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也提供了一定的激勵機制。可以說,工業革命不僅帶來了生產系統流程化的保障機制,同時也重構了社會生產運行機制關系。
產業分工的確立和社會運行機制的日益完善,最終促進了“工匠”群體的生成。工業化以來,人類在其發展歷史上首次正式宣布了作為“工匠”的主體性。社會分工理論在充分指出社會職業意義和重要性的同時,也明確了“工匠”群體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工業時代技術工人的主體精神已經逐步擺脫傳統理念的制約,開始轉為有意識地與社會實際需求相結合,著力培養具有現代學科基礎知識、具備專業技術能力,并能夠適應機器大生產的職業勞動者。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獲得個體與組織的交互,在信念、尺度、原則方面達到較為統一的目標,進一步確立一致的價值理念與價值認同,并逐步提升對自我的價值認知和職業理想。
不過,在以工具理性[1]和趨向功利為主導的大工業時代價值系統中,“工匠”群體始終處于一種短期經濟效益的支配下,以追求專業化、效率至上等名義,將個體的價值工具化、功利化、手段化,使工業時代的“工匠”群體的主體精神在追求個人主義與短期效益的過程中消解。同時,由于社會評價機制和相關法律機制的理性強化,如專利保護所導致的知識產權壟斷等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削弱了“工匠”個體意義與精神世界的架構和完善。大工業時代“工匠”群體意識的自發形成,就這樣湮沒在社會板直化的整體評價當中。
三、知識經濟時代“工匠精神”的成熟與發揚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和遷移。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新型人才,主體精神也在逐步發展中得到進一步完善,“工匠精神”的時代內涵最終得以確立。可以預見的是,在創新成為主流的歷史發展階段,其理念所引領的時代風尚,還將得到進一步發揚。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興起,現代服務業、信息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逐步開始引導經濟發展潮流。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后,知識在科技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作用日益增強,機器化大生產的“技術經濟”將被“知識經濟”所取代已是大勢所趨。計算機大數據成為知識經濟發展階段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它顛覆了以往傳統的計算機算法,其“量”與“質”的雙提升奠定了人工智能的基礎;而人工智能又進一步加速了大數據價值的挖掘和應用。另一方面,智能制造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它是制造技術發展,尤其是制造信息技術發展的必然,是自動化和集成技術向縱深發展的結果。計算機大數據體系的建構和智能制造產業的興起,同時催生了產品的個性化定制和個性化生產。
就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市場需求從本質上講,是眾多個性化需求的集成。由于個體基本條件和消費觀念的差異,不同消費主體一般都具有獨特的個性需求。工業化時代受到生產力發展尤其是技術水平的制約,大工廠規模化生產往往不能滿足普通消費者的個性化定制要求。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大數據收集定制需求,工業機器人、3D打印技術、敏捷生產、柔性加工以及計算機集成加工為主要構成的個性化定制產業鏈已經在許多領域成為可能。
“工匠精神”的提出,是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由短缺市場環境和計劃經濟體制向中高端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只有建立起支撐工匠精神的文化體系和制度保障體系,才能夠實現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實現從制造大國順利走向制造強國的轉變。而工匠精神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文化形態,需要國家最高層面的大力鼓勵和實質性的長效激勵,才能真正得以形成。對此,國家適時推出“中國制造2025”國家戰略。并始終強調要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統籌推進各類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完善相關人才培育政策和評價機制,并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合理、規范、有序的科技人才流動機制[2]等等。可以說,知識經濟時代凝聚“工匠精神”的客觀條件已基本成熟。
而就生產的主體條件來看,正如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描述的那樣,許多生產與服務都通過自由自主的方式來完成,[3]比如家居辦公的自由職業者,包括自由撰稿、平面設計、音樂創作、網絡銷售、在線編程、遠程教學以及學者科研等等。這種彈性的工作方式,允許工作者能夠按照自己的氣質、性格、興趣和愛好進行選擇,在自由的時間和空間中充分展示個體的能力和才華。某種程度上來說,將創新個體產業有意識地納入社會分工體系,并從身份、立法、稅收和保障等方面予以確認、規范和保護,是對工業時代集體化生產等單調生產方式的彌補,也是對個人設計、個人制造及個人價值的肯定,它意味著創新創業時代技術人才主體意識的覺醒也迫在眉睫。
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推出,越來越多具有創新理念、自主創業的“創客”加入到文化技術產業的創新中來。與傳統的手工業者和大機器工廠工人不同的是,這些新型人才正在逐步超越以往狹隘的功利與工具觀,轉向對人、社會、環境、創新的關注。他們的主體意識已漸告覺醒。這些新時期的“工匠”群體,不僅具有生產能力、生態意識和合作精神,同時也是具有高技術技能、創新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個性化人才。他們往往能夠自主能動地開發自身潛能,獲得多元的智能評價方式,同時也能夠積極主動地反思職業成就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對個體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將“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和諧統一。一方面能夠引領社會潮流、創新工業文化,保持人類生產生活同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關系,以自己的能力服務經濟社會、解決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反抗技術理性對人和環境的奴役,超越發展經濟的功利性和技術的工具性,使自我作為一個具有不確定性、超越性和創造性的個體生命得以完善、發展和提升境界的價值訴求,在特定職業人格的形成過程中,認同專業知識的學習,踐行職業精神,逐步建立個人生活形態,并最終成長為經濟上獨立、情感上敬業、生命本質上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完善個體。
從“工匠精神”內在發生機制產生到最終確立的歷史嬗變過程可知,一種理念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受到包括生產力結構、社會階層、評價機制和法律體系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同時還與行為主體的精神意識密切相關。對于“工匠精神”價值取向的正確理解,必須建立在內外因素相互制約、彼此激勵、同步發展、和諧共處的整體環境中。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社會機制的良性運行,以及創新人才主體意識的進一步確立,“工匠精神”一定能夠在新的時代煥發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
參考文獻
[1]查爾斯·塞勒著,程煉譯《現代性之隱憂》[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5.
[2]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內部文件),2015.
[3]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