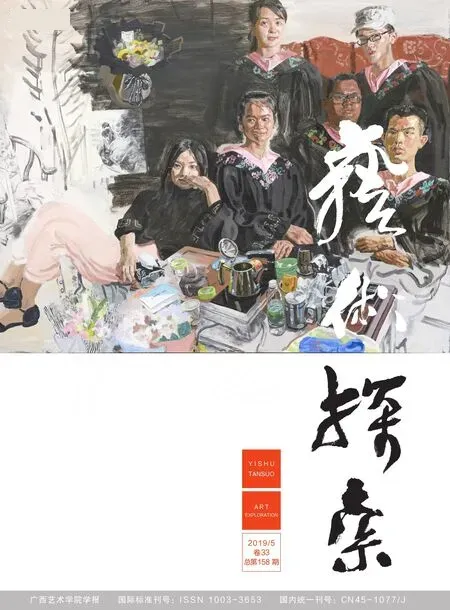論北魏“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審美意蘊
李 梅
(浙江理工大學 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8)
“褒衣博帶式”(即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佛衣(圖1、圖2)主要是中國學者,特別是藝術考古界研究者對中國佛教造像藝術中出現的寬大、飄逸的佛衣樣式的指稱。①目前中國學界對于“褒衣博帶式”佛衣的研究主要如下:阮榮春《論“褒衣博帶”佛像的產生》,文中稱“褒衣博帶”佛衣產生的源點在中國南方,其出現的時間可能比目前四川茂汶縣出土的佛像還要早;林樹中《早期佛像輸入中國的線路與民族化民俗化》,文中稱“褒衣博帶式”佛衣裝束出現時間大致在三國兩晉之際,開襟衫是其主要特點;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文中稱云岡“褒衣博帶式”佛衣最早的實例是十一窟上方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銘釋迦多寶龕,稱此現象與太和年間的服制改革有關。有別于佛教傳入初期,受印度及西域影響而形成的通肩式袈裟與袒右肩式袈裟,“褒衣博帶式”佛衣的披著方式較為接近中國傳統“褒衣博帶”的儒服。較為突出的特征表現為佛像內置僧袛衣,胸束帶結,外披雙領下垂式袈裟,多數為佛衣的右襟搭著于左袖上,袈裟下擺衣紋層疊展開,有些則如蓮花般舒展而開,也有表現為類似但又不完全一致的造型特征,從整體外形樣式上看,較為接近中國傳統士大夫的著裝方式。目前,考古界認為“褒衣博帶式”佛衣出現的最早實例為四川茂汶縣出土的刻有齊武帝永明元年(480年)銘文的釋玄崇造像碑,造像碑正面彌勒坐佛及背面無量壽立佛均著“褒衣博帶式”佛衣②費泳在《佛衣樣式中的“褒衣博帶”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繹》一文中稱,此說法見于劉志遠、劉廷壁《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第51頁,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楊泓《試論南北朝時期佛像服飾的主要變化》,《考古》1963年第6期;宿白《南朝龕像遺跡初探》,《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齊永明造像碑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92年第2期。。依據相關的文獻及考據材料可知,“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史上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或許是伴隨著佛教造像藝術傳入不久就已經發生了,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醞釀與變更,到了北魏云岡石窟的中后期,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佛衣樣式。而北魏遷都洛陽,伴隨著龍門石窟的大規模開鑿,出現了相對比較成熟的“褒衣博帶式”佛衣的造型,影響深遠。
一、佛衣樣式的演繹與“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
從外在形態上來看,“褒衣博帶式”佛衣借用了華夏民族的傳統衣著服飾,是佛教造像藝術在佛衣樣式上的漢化或者說本土化的一個主要特征。對于這一演繹過程,研究者們多側重于從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藝術樣式影響的視角作闡述,揭示了本土文化對外來藝術形式的影響①這方面的研究可參看,逢成華《北朝“褒衣博帶”裝束淵源考辨》,此文稱南北朝出現的“褒衣博帶式”佛衣與世俗人物裝束有別,北朝并非效仿南朝,而是淵源于漢魏古法,又認為南北朝“褒衣博帶”佛像裝束異源而同流,風格式樣差異不大。范英豪《同源而異趣的南北朝“褒衣博帶”》一文稱北朝“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是繼承漢魏傳統文化的結果,其服飾內涵的主體是儒家文化傳統,而南朝服飾的寬衣大袖則已經脫離儒家傳統軌道,走向形式的唯美化。張焯的《“褒衣博帶”與云岡石窟》從歷史學的角度,稱南朝盛行“褒衣博帶”系受北朝晚期官服影響,“褒衣博帶式”佛裝,是袈裟披著方式的中國化,出現時間早于北魏太和改制。。前輩學者的探尋為我們展現了佛教藝術在中國歷史上本土化進程中的一個側面,他們的分析與論述為后期相關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而對于佛教藝術本身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它得以扎根于異域并保持自身義理及藝術樣式獨特性的重要方法等方面,尚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探尋。筆者在借鑒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從佛教藝術自身發展的規律出發,探尋“褒衣博帶式”佛衣樣式中所包蘊的佛家的審美文化內涵,訪尋佛教藝術獨特的美學意蘊,努力發現佛教藝術是如何在華夏民族的文化土壤中繁茂生長的。

圖1 麥積山石窟第133窟,佛與菩薩

圖2 麥積山石窟第147窟,主佛
據史書記載,佛教自東漢明帝時期傳入古代中國②(晉)袁宏《后漢紀·明帝紀》記載:“初,帝夢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于中國而圖其形象焉”,學界多認為這是記錄明帝求法最古老、最可信的文獻。(劉宋)范曄《后漢書》也有記載明帝夢見金人而派遣求法使節的故事。③古印度佛像原有的兩種袈裟披著樣式。,主要是以經卷和畫像的方式實現佛法的傳播,佛像是否同時傳入,尚無定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佛像造像藝術在中國的出現與發展是一個漸趨推進的過程,早期的佛像制作主要受印度而來至西域出現的佛像造型影響,佛衣樣式是“半右袒式”或“通肩式”袈裟③,佛祖的形貌多被雕塑得較為健壯豐碩,尊相則偏飽滿圓融,豐碩的體魄與厚重的佛衣相映照,烘托出沉著雄健的氣勢,特別是云岡石窟早期開鑿的“曇曜五窟”(圖3)就很具有代表性。其高大健碩的身軀似有西域之風,也有北方民族初入中原時所流露出的粗獷與威猛之勢,匠師們以精深的陰線刻畫佛衣的紋飾與衣褶,呈現出厚重的質感,這是佛教藝術伴隨著大規模的開窟造像之風在北魏王朝早期所出現的特征。

圖1 云岡石窟第20窟,主佛

圖2 麥積山石窟第131窟,正壁主佛①圖片來源:圖1、圖2、圖4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 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圖3趙昆雨《云岡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藝術》,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
北魏早期的佛衣造型樣式的出現,一方面是受了西域之風的影響,另一方面,主要與北魏政權入主中原后的“興佛”與“滅佛”活動有關。據文獻記載,入主中原的拓跋氏最初并不信奉佛教,揮師南下的拓跋氏在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后,算是尋得了暫時安頓的契機,伴著大規模的移民遷徙至平城,為安撫徙民,穩固統治,元魏政權開始接受并積極提倡佛教。然而,這僅僅持續了一段時間。據史書記載,北魏太武帝“初信佛教,常與高德沙門談論佛法”,但是,又有“然帝好老莊,晨夕諷味,富于春秋,銳志武功……司徒崔浩,尤惡佛法,嘗語帝以佛法之虛誕,帝益信之”[1]2016。諸種因素的推動,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武帝發起了滅佛行動,凡有佛像及胡經者盡毀之,佛教遭遇了傳入古代中國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劫難。幸運的是,經歷了滅法后不久的佛教便遇到了它的另一位支持者——北魏文成帝,與此同時,佛教及佛教藝術也在積極為自身的發展尋求依托。云岡石窟的開鑿,正是在武帝被弒后,文成帝繼位詔復佛法之時。負責開鑿早期云岡石窟的工匠們多是從后涼遷徙而來,其造型以西域佛像為摹本,同時融入北方少數民族的審美特征,形成了典型的云岡模式,呈現出恢宏的氣勢。此外,當時的佛教藝術積極適應了“復法”后的社會情勢,厚重的“半右袒式”袈裟與佛祖肅穆的“尊相”相互映襯,給人以沉著威嚴之感,能更好地適應初入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審美傾向,也使得佛教能再次出現于北魏朝野,并促成了中國佛教藝術史上第一個繁盛期的到來,這些都是構成佛教藝術不斷適應與調整其在異域的發生方式,并與其他文化藝術互動交流并始終保持其自身獨特性的重要推動力。
“褒衣博帶”式佛衣是北魏中晚期出現的極具北魏風格的典型的佛衣樣式。就其出現的原因,諸學者都有論述,此不贅述,但是,作為北魏風格的典型代表,它的出現及傳播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劃上了濃重的一筆,它是佛教這一外來的藝術樣式積極吸收與借鑒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中的藝術及文化精神的有利見證。阮榮春指出,我國早期佛衣主要有三種,即右袒式、通肩式及“褒衣博帶”式,前兩種由印度傳來,后一種則是漢化的結果。[2]68費泳延續了這一說法,稱“褒衣博帶式”佛衣是繼“半披式”“垂領式”之后,漢地興起的又一佛衣樣式[3]73,宿白先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指出:“云岡“褒衣博帶式”佛像裝束的最早實例是第十一窟上方太和十三年(489年)銘釋加多寶龕。”[4]79從研究者的探究可以發現,“褒衣博帶式”佛衣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中獨創的佛衣造型,其普遍流行的時期應是五到六世紀,主要見于石窟寺造像,集中于北魏云岡石窟中晚期,龍門石窟最為盛行,敦煌莫高窟及麥積山石窟北魏時期的造像中也很普遍。可以說“褒衣博帶式”佛衣是北魏佛教造像藝術史上的標志性時期,其“褒衣博帶式”佛衣樣式與“秀骨清像”①“秀骨清像”是北魏中晚期出現的佛像藝術風格特征。具體表現是佛像面相清瘦,雙肩削窄,一般身著“褒衣博帶式”佛衣,整體呈現出清麗俊逸的風貌,有別于北魏早期渾厚沉著的風格特征。的佛祖形貌相結合,共同促成了佛教造像藝術由西域性特征向華夏民族藝術審美方向的轉化。最重要的是,這一形象是佛教依靠自身審美的獨特性及華夏民族藝術與文化審美的特點相促相融的結果,使得告別了印度源地漸趨衰落的佛教藝術,在走向西域流轉于中原的過程中,能夠繼續繁盛與遠播。
研究者們提及“褒衣博帶”一詞的文字出處時,大都援引《淮南子·氾論訓》,其文有云:“古者有鍪而綣領,而王天下者矣……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并指稱其為“褒衣博帶”的最早出處,但是研究者大都沒有對此處的“褒衣博帶”作深入的解釋,往往模糊地將其作為傳統“儒服”的指稱。若仔細梳理原文將會有所發現,其原文完整如下:“古者有鍪而綣領,而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5]203仔細辨析可知,這里主要是對古代圣賢者德行的頌贊,與傳統思想中所說的“垂衣而治”以及道家主張的“無為”思想有別,此處有“衣冠楚楚”之意,且“豈必”二字更是道出了德尚的重要性。從內在意義來看,后二者(“垂衣而治”的思想與“無為”的主張)意在為現有的秩序尋求合理的解說和歷史的依據,暗含了服飾與德行、秩序的關系。顯然,《淮南子》中所論更強調德行之力,并不能完全代表這一服飾樣式在歷史上的文化內涵。“褒衣博帶”較為普遍的用法是對華夏民族傳統的“儒服”的指稱,其主要特點是“長襟大袖、腰束寬帶”等,且與人的氣度風姿相關。由此來看,《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6]3035意在稱贊雋不疑衣著形貌甚有風度,呈氣宇軒昂之態,這里更接近“褒衣博帶”的歷史指稱意義。由此可見,服飾與人的德行、氣度乃至精神風貌的密切關聯,是理解“褒衣博帶”的歷史指稱意義及文化內涵的兩個重要方面,而“褒衣博帶式”的佛衣樣式與此則有著異同。
基于以上的參照與分析,可以看出,“褒衣博帶式”佛衣與傳統文獻記載的“褒衣博帶”之服有別,它是袈裟披著方式的中國化轉變,其演變與發展的契機與動因值得深思與探究。“褒衣博帶式”佛衣所蘊含的審美文化內涵與“褒衣博帶”的“儒服”指稱雖有一定的聯系,但是二者蘊含的實質意義有別,外形的相似或者接近并不能掩蓋內蘊的差異。
二、“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內在意蘊
佛教是超脫世俗世界,追求超越之美的宗教,何以會將袈裟雕塑為世俗人物著裝的“褒衣博帶式”,其間必有深意。我們知道佛教的教義是追求超脫之境的,而佛教藝術作為傳達佛教教義及義理的表達方式,最終是要作用于世俗社會的,世俗社會的審美與佛教蘊含的美學思想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并不純粹的藝術審美方式。由此來看,佛衣樣式的“褒衣博帶”造型是為了適應世俗審美的要求應運而生,事實上它也產生了極為持久深遠的影響。
服飾從來就不僅僅只為實用而出現,在古代中國,服飾最初與禮、德相聯系,如“褒衣博帶”一詞就包含著諸多的禮制、德尚,是社會秩序感的象征與體現,而于個體則承載著個人的氣度、風貌,甚至是運籌帷幄的風范。《周易·系辭》有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7]363,服飾的形制與紋飾作為德望、尊卑的區別,代表著社會的井然秩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褒衣博帶”的服飾是賢達與德才的體現,其風貌氣質于世俗社會則傳達著儒家“智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的理想追求。縱觀中國服飾發展的歷史,極易于窺見其綿延流淌的情感與文化脈絡,服飾的發展始終凝聚著實用與審美的雙重功效,甚至審美的因素時常占據著重要地位。當“褒衣博帶式”的袈裟披著方式出現在佛教造像藝術中,并且被廣泛應用之時,可以想見其審美與裝飾成分的意味深長。佛教造像藝術作為承載與傳達佛教教義與佛教思想的重要方式,其實用性的功能即是依據佛教典籍,精密刻畫佛家智慧及超脫的品質與形貌。“右袒式”袈裟及“通肩式”袈裟是印度佛教造像藝術中常見的佛衣樣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們襯托了原始佛教尚素樸與節儉的品格①依據佛教典籍可知,袈裟的做法是有這樣一層深意的。。而由“右袒式”袈裟與“通肩式”袈裟過渡到“褒衣博帶式”的佛衣,可以說是佛教傳入古代中國后,佛家美學意蘊進一步豐富與發展的表現形式。佛即覺悟、悟即通達,釋迦牟尼佛本來就是集賢達與睿智于一身的智者形象,“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佛教藝術對儒家思想的吸收,并將宗教的神秘之美作用于世俗社會,傳達佛家的審美意象。
對現實世界的否定與對智慧與覺悟的孜孜追尋,通過禪修脫離苦海達到清凈美妙的理想世界——涅槃之境,構成了佛教美學的基本出發點。建立在這一基點之上的佛教造像藝術,始終兼顧于妙、圓融和莊嚴的審美理想之中。“妙”在日常用語中表達美好之意,在佛家用語中則趨于神秘化,用于指稱佛事、佛學義理等不可思議而又無限美好的理想狀態,具有超越之意;“圓融”在佛教用語中表示圓滿周遍,一切具足的意思,“圓”即完美無缺;“融”則寓意通達無礙。佛教義理中以“莊嚴”贊美充分完滿的功德,亦用來贊美完善的裝飾,在佛教造像中的表現主要是對佛陀身體與相貌的肯定與贊美,佛教造像藝術一直深受這些審美理想的引導與影響,所以完美的佛家形象應該是妙、圓滿、莊嚴三者具備的理想狀態。由此出發,佛家意象的選擇與佛教造像的表達,都著意為實現佛陀莊嚴美好的完滿形象。服飾作為承載佛像思想與性格的造型方式,時刻也在為接近這一審美理想而努力,“褒衣博帶式”佛衣可以理解為這一造型樣式演變的有意選擇。
莊嚴與慈悲為超越現實造型的基礎,當“褒衣博帶式”佛衣與“秀骨清像”(圖4)的佛祖形象相結合,再點綴著那嘴角微微暈開的微笑,其示意前傾的姿態,完美地呈現了佛陀寓莊嚴與慈悲為一體的通達形象。飄逸的褒帶,寬大的衣袖,“清秀俊美”的體態風貌頓時使人聯想起道家仙風道骨的氣度,于靜穆中流淌著涓涓的生命之流,寓靜于動,堅守著那份看開一切俗世的超越。與道家不同的是,佛家特別是大乘佛教“普渡眾生”“濟俗于世”的義理又使得佛像的雕塑與刻畫融入現實,常常受到世俗審美風尚的影響。因此,佛陀的形象在追求超越脫俗之貌的同時,也要凸顯其和藹可親的一面,在這一點上,佛家很好地借用了儒、道相融的思想傳統,以綜合性的藝術表達方式傳達著自身的理想要求,潛在地促成了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獨特的審美文化內涵——與儒的賢達、道的飄逸相呼應的智識與通脫。
研究者們在分析北魏石窟寺中較為成熟的“褒衣博帶式”佛衣時,有時會將其與南朝留存下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的畫像磚相比較,稱北朝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受南朝世人著裝影響,有些論者認為這樣的比較不盡合理,因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磚上的人物著裝并不能代表社會上通行的禮服,畫像磚上人物著裝更為寬大,其服飾衣帽與人物的性格、風度相聯系。②這方面的研究可參看,逢成華《北朝“褒衣博帶”裝束淵源考辨》,《學術交流》2006年第4期。再參照沈從文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對此畫像磚的分析,可以作更深一步的理解,沈先生說道:“畫像人物的著裝是受了老莊思想影響,表現了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是對社會禮制與世俗的一種反叛。”[8]196筆者較認同以上的看法,據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南北朝出現的“褒衣博帶式”佛衣與“褒衣博帶”的世俗服飾內涵有別。但值得關注的是,南北朝時期,“玄”“佛”合流的現象非常突出,最為明顯的就是當時玄學名士與高僧的來往甚密,名士們常以玄學的思辨與玄理解讀佛教典籍,當時“格義”思想也是較為盛行的。所以,當玄理的深邃高遠與佛理的澄明曠達相遇,激起碰撞的火花。由此來看,當世人凝視集“褒衣博帶式”佛衣與“秀骨清像”的形貌于一體的佛像時,玄學的清雅也便應運而生。
總之,“褒衣博帶式”佛衣孕育生成于華夏民族動蕩與分裂的獨特歷史時期,其社會思想的大解放與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為藝術的審美開啟了多方的視域。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指出:“這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于質樸,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統治于儒教;這時代以后——唐代——在藝術上過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與丑、高貴與殘忍、高潔與惡魔,同樣發揮了極致。這也是先秦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學時代,一些卓越的哲學天才——佛教大師,也是生在這個時代。”[9]208可見,獨特的歷史機緣推動了佛教藝術的全面繁盛,并帶來了中國佛教藝術史上第一個高峰期。動蕩的社會,不安的靈魂,生命意識的自覺與求索,催生了世人飛升的理想與對生命的熱戀,對現實的不悅與對未來的企盼,世人諸種矛盾心境希望在佛教普渡眾生的義理中得到解脫。而集儒的賢達、道的灑脫、玄的清雅于一體的“褒衣博帶式”佛衣造型,正是蘊含了佛家完滿通達無礙的審美理想,寄托著眾生厚重的期望。
三、“褒衣博帶式”佛衣造型的寫意性特征
中國古代的匠師們往往有意淡化實物之形,而著意落在“韻味”的傳達上,如漢代俑的表現方式就很明顯,這使得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呈現出濃重的“寫意”性特征和追求“韻味”的表達之妙。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精神也深刻地影響了佛教造像這一外來的藝術樣式,如佛之軀體的雕塑在一些方面就沿襲了漢俑的形式。雕塑家多重視佛之面相、形態、衣貌、氣度的刻畫與傳達,有別于西方精密的圓雕方式,雕塑家對佛像的背面作較少的處理,甚至有些時候就直接雕刻在平面石塊上,簡單勾勒即呈現多種形貌。其意象的傳達又總是借助以“線”為生的技法,線、象、意構成了中國古代雕塑藝術語言的主要表達方式。
中國佛像的制作與佛家意象的選擇都透露出傳統藝術的寫意性特征。服飾作為承載佛像思想與性格的造型方式,蘊意豐富,其氣韻生動的造型樣式中傳達著獨特的藝術技巧。佛家尚質樸,追求通脫之境,佛教造像中佛祖的形象也常以簡樸、莊重為表達目的,匠師們除以簡潔的線條勾勒佛陀莊嚴美好的尊相,還將藝術傳達的精妙之處落在了佛衣的塑造上。從早期用粗略的線條著力于模仿異域厚重之風,到“褒衣博帶式”佛衣的出現,匠師們依據佛典而又不拘泥于規范,借助于傳統藝術的造型技巧,以流暢的線條傳達佛家簡潔、洗練的飄逸之貌。“褒衣博帶式”佛衣飄逸的造型得益于那流動性的線條,自由飛動的衣紋舒展下垂,于衣領及袖口劃下的弧線,流暢而圓潤,飄散的衣襟如蓮花般展開,烘托出佛祖沉著與莊嚴的精神氣貌。
“褒衣博帶式”佛衣隱喻了佛家對妙、圓融、莊嚴的審美理想及超脫之境的訴求,承載著豐富的審美意涵。它將中國傳統的“儒服”納入其中,顯其莊嚴之態,精密延展的紋理傳其圓融之貌,衣飾下擺依次舒展的蓮瓣極富層次感,整體呈現出規律的節奏感,所有的細節似乎都恰到好處地凸顯了佛祖的一切莊嚴與美好。這里有接近儒家“以和為美”的理想訴求,又有道家“返歸自然”的超脫,更有玄學“清遠曠達”的追尋,最主要的是“褒衣博帶式”佛衣樣式與“清秀俊美”的佛祖體貌相映,很好地傳達了佛家的妙悟之美。
學者們多稱道家哲學是最能體現中國藝術精神中飄逸之態的淵源。它促成了中國雕塑語言簡潔、明快之感,在虛與實的對比中,通過瞬間的動態,推動想象力的發揮,通過展現規律的節奏,形成具有韻律的“天人合一”的時空統一體。而當佛家對俗世的超越與追求精神的解脫與道家相遇,同樣成就了中國佛教藝術獨特的“寫意性”特征。中國藝術的“寫意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依勢造型”的創作技法,可以說“依勢造型”是中國古代雕塑的一大特點,如石窟寺的開鑿與洞窟主人出現,都得益于匠師依自然之力幻化而成。陳龍海在《建構飛動之美——試論中國古代雕塑的“線性”語匯》一文中稱:“中國雕塑的‘寫意性’,使得雕塑在中國雕塑家手里讓凝重的青銅器、石塊、泥塊具有了靈巧飛動之勢,從而實現了由體塊向線性的轉化,其意象衍生出的一個重要的藝術特點是促成了中國古代雕塑語言的精煉性。”[10]67雕塑家用簡潔明快的方式勾勒出的佛家飄逸之貌,著力講究紋飾之美的追求,展現出洗練、概括的整體美。這種藝術精神與藝術技巧極大地促進了佛教造像藝術的本土化轉向,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佛教藝術的審美理想。
依據佛教義理規定,袈裟由若干碎布補綴成條,并列縫制為衣,共有三衣:僧伽梨(大衣),用布9-25條;郁多羅僧(上衣),7條;安陀會(內衣),5條。由此可以看出,傳統袈裟以簡潔為準,并無多余的配飾,就佛教造像而言,早期造像中出現的“右袒式”和“通肩式”也都以簡練為主,除佛像肩部或衣袖有紋飾點綴外,整體以質樸見稱。而“褒衣博帶式”佛衣與傳統袈裟相比,卻增添了更多裝飾性的因素,主要以佛像胸束的帶飾和佛衣下擺重疊的衣褶為表現方式。具有裝飾意味的“褒衣博帶式”佛衣樣式,其寬大的衣袖,飄逸的帶飾,配以飛動的蓮瓣,以自由流淌的旋律,彰顯了佛家智慧圣潔的美好理想,在傳達佛家的氣質風度方面具有很好的表現意義。
顯然,從傳統袈裟過度到“褒衣博帶式”佛衣,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制作技法不斷趨于成熟與豐富的體現。曲線與圓雕的結合,虛與實相生,動與靜相映,孕育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獨特藝術魅力。中國佛像也因裝飾性的虛擬成分,更帶有一種非人間的神秘性,但經過匠師們巧妙的處理,流露在面龐的撼動人心的微笑,又具有一種和藹的親切感,適應了華夏民族的審美心理。所以,當佛教藝術在它的出生地印度衰落時,卻在古代中國的大地上開枝散葉,繁盛不已。
縱觀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第一個繁盛期——魏晉南北朝,因佛與道、儒及玄的相遇,成就了其質樸而不失高貴、超脫而不失親切的獨特氣質,北魏時期出現的“褒衣博帶式”佛衣樣式與“秀骨清像”的形貌特征集中體現了這一點。總之,北魏時期成熟的“褒衣博帶”的佛衣樣式寄予著佛陀世界的莊嚴與美好,也是時代精神在服飾上的折射,透露出世人飛升的理想與對生命的熱戀,飄灑的衣飾與簡潔明快的衣紋相映,流露出和諧的韻律與超脫的理想,整體顯出神、逸、妙的審美風格與氣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