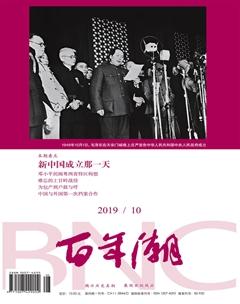鄧小平的閩粵兩省特區構想
歐陽湘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對于特區的創辦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的特區只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后來增加的海南。但有資料表明,鄧小平在1980年曾提出將廣東、福建兩省建成特區。那么,鄧小平的這一構想是否確有其事?如果有的話,為何后來沒有貫徹落實呢?
一
鄧小平將廣東、福建兩省建成特區的構想,是1980年10月底或11月初對任仲夷、梁靈光兩個人講的。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調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楊尚昆回中央任職,改調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輕工部部長梁靈光南下接替他們。11月初,任仲夷、梁靈光在廣州履任新職。在任、梁南下之前,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谷牧等中央領導同志先后接見他們。
據任仲夷回憶,鄧小平在接見他和梁靈光時說:“特區不是僅僅指深圳、珠海那幾塊地方,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你們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對于搞特區,你們要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梁靈光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鄧小平在接見他們時有類似談話。
這不是偶然的。鄧小平在倡議創建特區時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三個戰略決策:一是把特區命名為“經濟特區”;二是明確指出特區政策可以再放寬些;三是強調廣東特區是廣東全省。鄧小平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區,不僅對廣東、福建兩省,而且對全國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大視野下的中國共產黨90年90事》其中第63事“開放的窗口: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說:鄧小平說了特區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并要求任仲夷、梁靈光“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
2012年年底,中央電視臺、人民出版社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精神編寫了同名著作《復興之路》。其中第二篇“人間正道是滄桑”引用了前述鄧小平對任仲夷、梁靈光的上述談話。
從地方的要求看,廣東、福建都有將全省建成特區的愿望。
先看廣東。廣州是我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1957年開始每年舉辦兩次出口商品交易會。這是廣州獨具的優勢。對外交往多,也使群眾的觀念比內地要開放得多。習仲勛主政期間,非常重視發揮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當時,省委分工由第二書記楊尚昆兼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習仲勛、楊尚昆希望廣州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帶動整個華南地區經濟騰飛的作用。
僅就建“特區”而論,1979年年初,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舉辦“出口加工區”。省委在討論時認為,還應該在深圳、珠海辦。習仲勛表態:“要搞,全省都搞。”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對國務院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說:在廣州搞特區比在深圳搞特區要好。他的理由是,深圳只是“一片荒涼的灘涂”,基礎設施和各項條件差,對香港客商缺乏吸引力。在廣州搞特區,則可以很快見成效。對于王匡的這兩項建議,谷牧說:你的意見可以采納一半,即堅持建立特區,并擴大特區;關于否定在深圳建立特區的提議,則不予采納。
無獨有偶,福建省也設想在福州的瑯岐島和廈門的海滄建立兩個“出口工業區”。為此,福建省委、省政府還專門派出團隊到香港考察,并研究了臺港澳地區以及第三世界十幾個國家建立“自由港”和“加工出口區”的經驗。此后,香港妙雨集團派員來福建考察,提出在福州的瑯岐島建出口工業區的建議。1979年9月26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福建瑯岐島出口工業特區建設的報告》,并成立“瑯岐島出口工業特區管理委員會”,開始前期的籌備工作。
在中央層面,國務院分管特區工作的谷牧副總理很重視廣州的對外開放。1979年9月,他對習仲勛、楊尚昆說:中央要求廣東先走行一步,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要跑得更快,不僅兩個特區,還有全省先走一步。在全省,重點還是廣州市,廣州市如何進一步把工作搞上去。你們這里是在全省搞,要全黨大動員,把出口搞上去,把工業搞上去。“你們不是兩個特區,中央考慮的是你們全省。”他計劃下次來要找廣州市談,并請楊尚昆轉告市委,廣州要搞個規劃。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盡管沒有記載前述鄧小平接見任仲夷、梁靈光的談話,但在這個時間段有不少類似的談話。例如1980年10月9日,鄧小平在向日本松下電器公司最高顧問松下幸之助一行介紹中國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政策時說:我們把廣東、福建當作“特殊地區”,在廣東靠近香港的地方設立一個特區,歡迎各國的資本在那里投資設廠,參與那里的競爭。
二
到20世紀中前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總結經驗中穩步推進。中國沿海基本形成由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開放區組成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
1.借鑒推廣特區政策
1980年11月以后,廣東和福建貫徹鄧小平的上述構想,嘗試在其他地區推廣特區的政策措施。從廣州的個案來看,這種嘗試大致持續到1981年下半年。
11月22日,梁靈光在全市黨員干部會議上要求具體落實鄧小平與他和任仲夷的談話精神。廣州作為省里的重點,如何實現特殊政策與靈活措施,有責任提出辦法和措施來。次年1月31日至2月3日,梁靈光在市委擴大常委會議上說:要爭取在深圳、珠海實行的特殊政策也在廣州實行。“我省是中央確定的兩個特區之一,更要解放思想,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會議通過了廣州市經濟調整的指導思想:“經濟要調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文明,特區要前進。”
1981年5月18日,任仲夷在省委特區建設和對外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特區一定要“特”,特區如果不特,就達不到特區的目的。他還明確指出:幾個特區是全省最開放的地方。特區實行的政策和辦法,要有選擇地逐步推廣到廣州以及其他中等城市。例如,商品進出口的某些便利權,對客商的某些優惠辦法,較低的所得稅稅率等,都可以考慮在廣州實行,或稍加改變以后實行。廣州不叫特區,但政策可以一項一項地放寬,以加速廣州的現代化進程,進而帶動全省。
5月,廣州市委向省委常委的匯報多處提到要借鑒特區的做法:關于工業調整問題,提到“準許免交國營工交企業的基本折舊基金”,要求按照深圳、珠海等地辦法。關于搞活對外經濟問題,“如果從我省是一個經濟特區的角度上看”,許多方面步子邁得還夠大;最近,福建給廈門的對外經濟工作有更多的機動權。當時,合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深圳特區是15%,香港是17.5%,廣州則按國家統一規定為33%。市委認為,廣州可略高于深圳,定為20%左右。深圳、珠海和海南地區貿易外匯分成比例已分別提高至80%和50%,廣州應改按海南辦法,實行省市五五分成。
同年6月,國務院主要負責人來廣東視察,梁靈光要求允許廣州在引進外資方面采取類似特區的政策,未獲同意,那位負責人沒有說明理由。梁靈光估計是“當時北京對外開放認識不一,可能他有困難”。但廣州市委仍盡可能地往這個方面努力。
梁靈光在市委第三次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在土地使用、勞動工資、利用外資進口材料、設備減免關稅等方面,可以參照特區的做法,盡快擬定實施辦法,變通執行。”同年9月,任仲夷在廣州市委四屆一次全會上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在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經濟特區,今后廣州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他還說:“廣州市雖然不是特區,但毗鄰港澳,也是很開放的。”
2.開放沿海港口城市
早在1980年第四季度,中央就提出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在廣東、福建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實行下去。但步驟和方法要服從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
但鄧小平并沒有停止推進特區建設。1983年6月25日,谷牧在接見廣東省有關負責同志時傳達鄧小平的指示:特區要堅決辦下去,不能動搖。現在,對特區說好話的多了。特區“現在辦得不錯,中外承認,不存在抹掉不干的問題”。
1984年1月,鄧小平在王震、楊尚昆陪同下視察廣東。24日抵達廣州時,鄧小平對劉田夫、梁靈光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隨后,他赴深圳、珠海和中山、順德視察,于1月29日回到廣州。在珠海視察期間,鄧小平題寫:“珠海經濟特區好。”在中山溫泉賓館會見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馬萬祺以及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時說:“辦特區是我倡議的,看來路子走對了。”2月1日,鄧小平在廣州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春節后,鄧小平又視察了廈門和上海。
2月24日,回到北京不久的鄧小平,邀集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還建議,“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大家還就擬開放城市名單進行了醞釀。

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召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重點是解決沿海幾個城市的對外開放問題”。參會單位包括擬開放的八個沿海港口城市、四個經濟特區和海南島,及所在省區負責人。谷牧在座談會預備會議上首先提問:要不再辦幾個新的經濟特區?他自己回答說:還是小平同志指示的辦法好,選擇幾個港口城市,“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谷牧又問:“到會的幾個沿海港口城市是一齊上,還是分期分批?”他又接著自己回答:“我看這個問題不決定于主觀愿望,而決定于客觀條件。這里說的客觀條件,包括海陸空交通、對外商的吸引力等等,特別是人才、干部這個條件。應當按實際情況辦事,從創造條件入手,以分期分批為好,條件成熟一個開放一個。”

1984年,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圖為鄧小平等人一起討論特區建設問題
座談會期間,廣東和江蘇等省都要求增加開放城市。到4月4日下午,會議決定增加廣州、湛江、福州、秦皇島、連云港、南通,城市數量達14個。由于這六個城市沒有參加座談會,谷牧在會議結束時特別安排向六個城市傳達會議精神。
4月5日,廣東省委在京開會人員將會議情況電告辦公廳并轉告廣州市委:(1)中央書記處同意,廣州和湛江列入實行開放政策的沿海城市;(2)廣州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可享有省一級批準權限;(3)沿海城市會議6日結束。谷牧擬留吳南生幾天,談一談幾個特區工作的問題,南生同志擬提出在廣州劃一小片搞加工特區的問題。
3.開放三個三角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的醞釀,與鄧小平的支持有密切關系。1983年6月,谷牧在北京向廣東有關負責人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特區的發展,有個同香港統一規劃的問題,不要香港已有的東西,特區又辦。鄧小平還談到粵閩兩省,“不花自己錢的,不影響國家集中投資的,就要特殊,讓兩省自己搞”。谷牧說,他與廣東省研究過,上海搞了個“長江經濟區”,珠江也有個“三角洲”,廣州至深圳,沿途幾個縣,這個三角洲同上海不同。“華僑多、港澳同胞多”。實行特殊政策,就要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谷牧還談到,福建在臺灣問題上可以發揮優勢。
1983年12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向谷牧匯報《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規劃的初步設想》,后經由谷牧于次年1月上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1984年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曾討論這個問題。同年11月,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在廣州視察時表示:除了特區和沿海14個開放城市外,還準備把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開放地區。
當時,廣東省沿海開放城市甚至其他城市的改革開放,都嘗試借鑒特區的政策。例如1984年7月,省政府決定在廣州、湛江、佛山、江門四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明確規定:“試點城市和面上城市,都要學習外地的體改經驗,總結報告本地行之有效的體改經驗。有選擇地推廣深圳經濟特區的體改經驗。”
當時有學者認為,開發區是與經濟特區屬同一序列的經濟區域,在許多基本方面具有共同特點。事實上,開放沿海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工作,都歸口國務院“特區辦”和省政府“特區辦”管理。有學者進而指出: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重要性,同經濟特區“四個窗口”“兩個輻射”的作用,實質是一致的。如果要說有什么差別的話,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引進世界先進技術、開發新產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等方面,應該發揮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作用。
經濟開放區的性質類于經濟特區,外界觀感更是如此。在1984年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上,谷牧就批評廣東說:“有人告你們的狀,說廣東隨便宣布珠江三角洲要搞特區”。對此,吳南生辯解說:是報紙印錯了,將“經濟區”印成“經濟特區”,已作更正。無獨有偶,《人民日報》1984年7月14日第2版有廣州“準特區”之說:廣州是進一步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但實際上提前開放了五年。早在深圳、珠海、汕頭被劃為經濟特區的最初時期,廣州就在事實上成了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聯結點。那時,廣州雖然不是特區,但它有權執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被稱為“半特區”。
1987年,國務院同意把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范圍從“小三角”擴大為“大三角”,包括地處腹地的清遠縣;同時將沿海開放城市汕頭、湛江,以及茂名和惠陽地區的部分市、縣,列入經濟開放區的范圍,享受中央〔1985〕3號文件規定的優惠政策。至此,廣東沿海地區已悉數納入經濟開放區。同時,福建沿海地區的市縣也納入經濟開放區。可以說,鄧小平將閩粵兩省建成特區的構想已基本實現。
這個構想的實現在實踐中有一個在變通后貫徹落實的復雜過程。黨內“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鄧小平本人對于辦特區也是當作一個試驗,“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十足的把握。如上所述,鄧小平1984年在實地視察深圳等經濟特區之后曾斷言:“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但他1985年又說:“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直到1987年,鄧小平才放心地說:“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消除了。”
鄧小平關于將廣東、福建兩個省建成特區的構想,無疑是高瞻遠矚的。任仲夷后來在回憶1980年那次談話時說:“根據他的思想來檢查我們的工作,我們膽子還是太小了,思想還是不夠解放。如果我們當時膽子更大一點,思想更解放一點,今天廣東的形勢可能會更好。”(編輯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