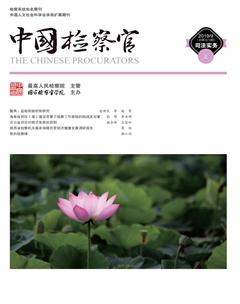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爭議問題探析
俞新民 常禎
編者按:當前,我國職務犯罪案件辦理存在監察調查與檢察偵查兩種方式。監察調查抑或檢察偵查,都是為了更好地從法律上打擊制裁職務違法犯罪行為,監察調查的部分案件最終也會移交人民檢察院進行審查起訴。然而,司法實踐中存在監察檢察職務犯罪管轄權沖突、留置與強制措施對接不暢、退查程序不完善等有礙順利懲治職務違法犯罪行為的情形。為此,本刊特組稿4篇,從權力屬性、管轄權爭端處理、監檢銜接程序與機制等方面,對監察調查與檢察偵查予以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摘 要:監檢兩機關在查辦司法工作人員特定職務犯罪權限上存在職權競合問題,導致實踐中兩機關在14個特定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上存在分歧。從監檢兩機關法律定位、檢察機關特定偵查權權限范圍、特定職務犯罪案件優先管轄權等方面進行分析論證,可以厘清監檢兩機關在查處特定職務犯罪案件中職責權限,探索解決兩機關管轄權屬爭議,理順監檢關系。
關鍵詞:特定職務犯罪 爭議 管轄權 監檢關系
一、問題的提起
《監察法》第3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審計機關等國家機關在工作中發現公職人員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問題線索,應當移送監察機關,由監察機關依法調查處置。被調查人既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又涉嫌其他違法犯罪的,一般應當由監察機關為主調查,其他機關予以協助。”2018年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根據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可以”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與《監察法》對所有公職人員違法犯罪規定“應當”由監察機關為主調查如何相協調?因監察和檢察兩機關對特定互涉案件在管轄權上存在職權競合,導致在實踐中,兩機關在特定職務犯罪案件管轄權上頻頻發生爭議:有的基于兩機關現實地位不對等,出現監察機關指派檢察機關查辦案件情況;有的兩機關爭管轄權,同一個職務犯罪線索,兩機關都認為自己有管理權,互相爭辦案權;有的對于“難啃”的職務犯罪案件互相推諉,誰都不愿意查處,尤其是近兩年掃黑除惡斗爭中遇到的“打網破傘”相關案件,因辦案難度大,推諉扯皮問題屢屢發生;還有的出現程序倒流問題,如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犯罪案件,在偵查終結后又需移送監察機關審查決定是否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既違反查辦案件程序性規定,又浪費辦案資源,影響辦案效率。這些問題是因《監察法》第34條和新《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有關特定罪名管轄權重疊、職權競合導致的。如何處理好職權競合問題,合理界定監檢兩機關在查處公職人員職務犯罪管轄權,這就需從監檢關系的法律定位、檢察機關特定偵查權的權限范圍以及特定案件優先管轄權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以明晰兩機關各自職能,準確界定兩機關管轄權限,合理解決管轄權沖突,理順監檢關系。
二、監檢法律定位分析
《憲法》第2條第3款、第127條第2款確立監察機關在我國國家權力機構中與檢察機關是并列的法律地位,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之間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平等工作關系。明確監察機關性質是履行監察職能的專門機關,是我國的反腐敗機構,其行使獨立監察權。我國監察體制改革目的是要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1]通過集合所有的反腐敗力量,創建一個統一、獨立、高效率的監察機構是成立監察委的初衷。我國監察體制改革是中央對原政府的行政監察權和行政違法預防權,以及原檢察機關的自偵權與職務犯罪預防權進行整合后,新創設的監察權,[2]其實質就是對職務犯罪案件辦理程序的“重塑”和“再造”,改過去“各個指頭”戳為監察委一個“拳頭”打,整合了過去分散的反腐力量。《監察法》第二、四章利用25個法條闡釋了監察權限,主要概括為“監督、調查、處置”等三項權力。其中,監察調查權是指監察機關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公職人員進行調查。[3]從《監察法》第34條也可以明確看出,監察委立案調查職務犯罪案件是全覆蓋的,對所有公職人員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線索,監察機關都應受理并依法調查處置,這是我國查處公職人員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原則性規定。
而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2018年3月的憲法修正案、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并沒改變檢察機關的憲法和法律定位。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與行政、監察、法院等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并不存在委托或授權的關系,只能是基于法律規定產生的平等主體關系。從法律定位來看,檢察機關應與監察機關處于同一層次,兩機關法律賦予的權力不同,但應相互平等,處于同一平面結構關系。[4]因此,在監檢關系處理上,尤其是在職務犯罪案件管轄問題上,兩機關應結合各自法律賦予的職能,按照“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工作關系處理好與對方的關系,監察機關在實踐中指派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顯然于法無據,有悖于兩機關的法律定位和現行立法精神。
三、檢察機關特定偵查權權限范圍
新《刑事訴訟法》雖保留了檢察機關部分職務犯罪偵查權,但新法更強調檢察機關對偵查權的訴訟監督效果。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偵查權僅是法律監督職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偵查權的行使,應圍繞法律監督職能行使,立法賦予檢察機關行使特定偵查權是有特定的權限范圍。
(一)檢察機關“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范圍
如何理解“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即為訴訟監督。檢察機關訴訟監督主要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訴訟監督。其中刑事訴訟監督,包括偵查監督、刑事審判監督和執行監督,主要是對公安機關立案監督和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對審判機關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以及對司法行政機關刑事執行活動的監督等;民事訴訟監督,包括對審判機關的民事審判活動是否合法,所作的民事判決和裁定是否正確進行的監督;三是行政訴訟監督,主要包括行政案件受理、審理、裁判、執行等訴訟環節。[5]檢察機關對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訴訟活動的監督范圍,限定了檢察機關“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保留的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只限定于立案查處司法工作人員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活動中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職務犯罪行為,此類案件可以由檢察立案偵查。對于這個限定范圍以外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沒有管轄權。
(二)檢察機關對“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管轄權限范圍
如上文所述,新《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在三大訴訟監督范圍內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但并不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訴訟中發現的所有違紀、違法和犯罪案件都可管轄,仍需符合兩個條件。一是立法授權僅限于對“犯罪”行為才可由檢察機關立案偵查。但對司法工作人員在三大訴訟中利用職權實施的違紀和違法行為,法律并未賦予檢察機關可立案調查,而是規定應將線索移交監察機關依法調查處置。[6]因為,監察機關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和監察權,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二是立法授權需符合“侵犯公民權利與司法公正”。既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案件,才可由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對于沒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仍無權立案調查,應當移送監察機關。根據我國《刑法》,符合上述2個條件的犯罪有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虐待被監管人、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枉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執行判決裁定失職、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私放在押人員、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14 個罪名。根據新《刑事訴訟法》對檢察偵查權的雙重限定,檢察偵查權范圍應從兩方面嚴格界定:一是對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7];二是這類職務犯罪“侵犯公民權利與司法公正”。綜上,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僅限于符合上述2個條件的14個罪名,而對于司法人員違紀或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行為,立法未賦予立案偵查權。
(三)“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管轄界線
新《刑事訴訟法》對檢察機關行使偵查權的表述為“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法律語境中“應當”是一個明確性詞語,而“可以”則常常是一個模糊性詞語,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可以”在法律語體尤其在我國刑事法律中主要有三個語意特征:一個表“可能”;一個表“能夠”;另一個表“許可”。“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中的“可以”,是立法授權性的,其義應為“許可”。新《刑事訴訟法》之所以使用“可以”的表述,是因為《監察法》已賦予監察機關行使對所有職務犯罪的調查權,后新《刑事訴訟法》又保留檢察機關特定案件偵查權,導致監察機關調查和檢察機關刑事偵查的職權競合,立法才授權性地表述為“可以”。
對職權競合問題,從比較法的經驗來看,處理大致可以從兩個思路出發解決競合問題——合并的思路與分立的思路。所謂合并的思路,就是從立法層面將涉及相同職權的規定并入到單一機構行使。從國家立法初衷看,合并的思路解決監檢職權競合問題顯然行不通。所謂分立的思路,就是按照不同的行使職權目的分別由不同的法律部門對職權對象行為加以規范,由不同的職能機關實施。分立的前提是各機關的行使職權目的和權限必須是明確的、界限清晰的。《監察法》第34條對所有公職人員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都應當依法調查處置作了明確規定,查處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是監察委的職責所在。而新《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的管轄僅限于“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可以”管轄,但規定比較模糊。因此,按分立的思路,監察機關的調查職務犯罪的職責在立法上是明確的,而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司法人員特定職務犯罪的規定并不清晰。因此,在實踐中發生監檢兩機關因職權競合問題發生管轄權爭議,按解決競合問題分立思路,應由職權清晰一方管轄,即由監察機關管轄。
四、特定職務犯罪案件優先管轄權
監檢職權競合問題,對于管轄模糊有爭議案件,上文已作爭議處理分析,再不贅述。對于檢察機關管轄明確“可以”立案偵查的特定案件,檢察機關在立案前仍需與監察機關進行溝通,協商確定互涉特定案件管轄歸屬。理由有三點。首先,立法賦予監察機關“應當”立案調查所有公職人員違法或者職務犯罪權,這是原則性規定,監察機關的權限具有廣泛性。而對于檢察機關“可以”管轄的特定案件,立法機關之所以保留檢察機關的管轄權,主要是考慮到檢察機關在訴訟監督活動中更容易發現司法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職務犯罪。另外,由檢察機關立案偵查這類案件,有利于對證據的合法性判斷和保證訴訟走向,有利于及時判斷證據合法性,保障訴訟順利進行。因此,在監檢“應當”與“可以”沖突中,特定案件的立案查處有利于及時判斷證據合法性,保障訴訟順利進行的情況下,通過溝通,檢察機關才可以立案偵查,否則,特定案件偵查權仍應歸屬于監察機關。其次,監察機關優先管轄互涉特定案件符合當前兩機關的人力配置和辦案保障實際狀況。隨著檢察機關原反貪、反瀆、職務犯罪預防等部門的轉隸,原辦案力量、辦案設備及經費保障等已全部劃轉到監察機關,檢察機關短期內辦案力量和辦案保障還不足,還需一個優化、充實過程,因此,由監察委優先管轄,可以更有效打擊此類犯罪。最后,監察權包括“監督、調查、處置”三個方面的權力,在“訴訟活動法中”,發生違法犯罪問題時總會涉及部分公職人員的違紀、違法問題,監察委優先管轄,可實現違紀和違法犯罪問題同時立案調查,更有利于突破案件,符合發現犯罪的辦案邏輯。綜上,監察機關在特定案件管轄上,具有現實優先權,檢察機關在訴訟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14個罪名犯罪案件,仍應及時與監察機關溝通管轄權問題,協調一致方可立案偵查。同時,對于立案偵查的特定案件,檢察機關偵查中,應當執行《關于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偵查終結前,應當就移送審查起訴有關事宜與監察機關進行溝通,協調一致,并由檢察機關依法對全案審查起訴。避免檢察機關偵查終結后,又移送監察機關,由監察機關決定是否移送審查起訴的程序倒流問題發生。
綜上所述,新《刑事訴訟法》保留檢察機關可以立案偵查的14個罪名案件,但立法并非將14個特定案件管轄權完整賦予檢察機關,而是兩機關職權競合,均有管轄權。在三大訴訟活動中,發現司法人員侵犯公民權利或損害司法公正,給具體案件證據合法性判斷和訴訟走向造成影響的行為,檢察機關可立案偵查,這是立法保留給檢察機關狹窄的職務犯罪偵查管轄權,界限已很明確。因此,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監檢兩機關應加強溝通、協商解決,按立法授權履行好各自職權。[8]檢察機關作為職務犯罪職權轉隸一方,不應仍依賴職務犯罪偵查權增強權威性,在大部分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的背景下,檢察權的權能結構已發生重大調整,因此,檢察機關要正確認識新時代檢察形勢的變化及帶來的影響,順應廣大人民群眾新的期待,重新定位職能權屬,重新構建檢察權。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一部署,將職權重心調整到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及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平衡發展,通過科學配置內部機構職能,彰顯檢察權司法屬性,進一步增強檢察監督的公正和權威。
注釋:
[1]參見吳宏耀:《論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的訴訟銜接》,《中國檢察官》2018年第12期上。
[2]參見劉凡、劉鑫、王勝利:《監察機關職務犯罪調查與檢察機關訴訟銜接機制研究》,《皖西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3]參見徐鶴喃:《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與統合》,《人民檢察》2019年第1期。
[4]參見王洪宇:《監察體制下監檢關系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5]參見苗生明:《淺議檢察機關特定偵查權的有效行使》,《中國檢察官》2018年第12期上。
[6]參見錢寧峰:《監察機關與執法部門之間關系的憲法定位及其具體化》,《學海》2019年第3期。
[7]參見朱孝清:《檢察機關如何行使好保留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1期。
[8]參見季衛華、李強、王勝利:《新時代檢察機關的職能優化》,《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