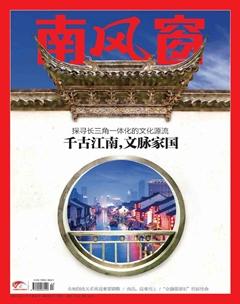金馬獎的黃昏
李少威
熬一鍋好湯很難,毀掉它卻很容易。
2018年,中國臺灣電影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李安,和當年最佳紀錄片的導演傅榆,分別扮演著熬湯和毀湯的角色。
作為全球最知名的華語電影導演,李安為了金馬獎可謂嘔心瀝血,而其心血投注的重要方向,就是動員大陸電影和電影人參加,2018年把張藝謀、鞏俐請到現場就是一大成果。然而,傅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臺灣電影人在領獎臺上的一番分裂言論,讓他的努力付諸東流。
多數情況下,湯壞了倒掉重做即可,代價只是材料和時間成本翻倍。但在一些特殊情境下,鍋很難再架,火也不容易再生。
2019年以及以后的金馬獎,面對的就是能不能把鍋再架起來、把火再生起來的問題。而這一切,將取決于大陸電影未來只是“暫停參加”,還是“不再參加”。
金馬獎的黃昏降臨了。
誰是中心

8月份消息傳出,大陸電影和人員暫停參加 2019年金馬獎。亦步亦趨,香港的電影公司隨后也紛紛宣布撤銷報名,港、臺知名演員則陸續表示不會參加。原定擔任評審團主席的杜琪峰導演,也因為“合約原因”辭任。結果就是,在今年第56屆金馬獎的入圍名單里,幾乎看不到熟悉的片名和人名。東南亞華語電影被特邀參展,是創舉還是無奈,交給人們各自去理解。
片名和人名的“不熟悉”,是就大陸觀眾而言。大陸觀眾不熟悉,不代表作品不好,也不意味著主創團隊水平不高,滄海遺珠的可能性永遠存在。
然而,“大陸觀眾”這個集合名詞,和“一個巨大的市場”是同義的。對于華語電影作品本身如此,對于希望通過影視娛樂業進行產品宣傳的商業界同樣如此。于是人們又看到,在陸港電影、影人打退堂鼓之后,贊助商也紛紛鳴金收兵。
電影獎,不是電影本身。它是一個展會,一個節慶,一場文化商業活動。因此,金馬獎的影響力和中國臺灣電影的影響力,兩者不能在邏輯上劃等號,甚至可能關聯甚微。正如諾貝爾獎由北歐國家頒發,但不等于北歐國家在科學、文藝方面占有領先地位。
獎項的權威性,部分來自歷史,歷史賦予它一定程度的壟斷性,但更重要的是來自中心的承認,由承認而維系。金馬獎的權威性主要來自華語電影圈的承認,評審中心與華語電影工業的中心,兩者一直都是錯位的。
華語電影,是一種特殊的存在。盡管它無論是產量還是票房,都在世界范圍內擁有相當的份額,但它幾乎無法闖入主流英語世界。因此,這其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圈子。
世界華人的數量,以及地理分布特點,塑造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圈子,讓它可以支撐起一種局部全球性的文化。它具有高度的分發能力,能夠把文藝作品分發到世界各地,因為,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
因而,一個問題就非常關鍵:誰來負責分發?當然是中心。
過去的天下體系,文化的分發中心是中國的中央政權,分發的產品是儒家理念,即所謂“王化”。因而在邊緣地帶,存在許多以“化”為名的地方,昭示這些地方在特定時間里接受了“王化”,成為文明所及之地。比如遵化、隆化、通化、敦化、奉化、懷化、從化、彰化……
新中國前三十年,華人世界事實上分裂成了兩塊,一塊是中國大陸,一塊是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包括中國臺港澳地區和海外華人華僑等,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制度的隔閡和對峙。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得以構建了一種文化共享機制。
這就是香港、臺灣在一段時間里成為華人世界文化分發中心的原因。
1978年以后,中國大陸逐步與外界融為一體,也開啟了重新整合世界華人文化的歷程。
這一重新交接,最終在21世紀初完成了。
中心轉移
就華語電影而言,原來的中心毫無疑問是香港。得益于華人人數之眾,它在八九十年代甚至可以和好萊塢分庭抗禮,成為“東方好萊塢”。
就全球影響力而言,臺灣的影視文化和香港不可同日而語。創辦于1962年的金馬獎之所以能成為權威,也是得益于香港這一中心的承認并積極參與。
創辦于1962年的金馬獎之所以能成為權威,也是得益于香港這一中心的承認并積極參與。
在那個時代里,作為華語電影工業中心的香港,為何要服膺于臺灣的金馬獎呢?原因在于,當時香港電影的投資主要來自臺灣,市場也主要在臺灣。
在港臺電影尤其是香港電影最為繁榮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的商業還處在孩童時期,商業對文化領域的支持更是尚處探索階段。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金馬獎基本上與大陸電影無涉—早在大陸商業電影起步之前,它就已經風光無限。
這一點,至今還會給臺灣地區的電影人一種錯覺,即金馬獎的影響力與大陸電影的參與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比如,聞知大陸電影暫停參加金馬獎,并且同期在廈門舉辦金雞百花獎,就有臺灣導演表示:“金雞獎拼得過金馬獎嗎?”
“拼得過”是一個典型的臺式語法,常常出現在新聞表達和政治表述當中,比如“拼經濟”。這種語法背后的心理,是拳擊擂臺式的,也就是說,說話者認為對手是同一個量級的,差別僅在于訓練程度,而訓練程度與訓練時長緊密相關。
這便是昧于大勢,訴諸歷史。
早在20多年前,華語世界的文化中心已經發生轉移。因為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影響力的增長,華人文化事實上已經重新結構化,滄海桑田。
轉移的邏輯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或者放寬到21世紀初以前,中國港臺影視、流行音樂風行一時,大陸基本沒有話語權。
但這是一種壁壘式的繁榮。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大陸,在文藝發展領域不存在商業機制;開放以后,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補課過程;社會制度差別使得中國港臺在觀念、信息、藝術創造力方面占盡優勢。一開始,這一游戲就是在“三缺一”的條件下展開的。
因此在稱頌繁榮的同時不能忘記一點:此岸的勝利不是因為對手無能,而是因為對手沒有參賽。
香港、臺灣的市場規模都不大,但它們得益于20世紀90年代及以前電影、音樂工業所處的特殊階段—大致上相當于工業史上的工場手工業時代。
這一階段除了對現代技術依賴程度較低之外,對投資和市場的規模要求也較低。因為技術幼稚,電影的質量與演員的拼命程度緊密相關(比如成龍電影);因為投資少、成本低,港臺電影只靠兩地的市場就能存活并繁榮。
進入21世紀,世界已經變了。
一方面,中國大陸融入世界,制度性壁壘被打破。
另一方面,此時的影視工業,已經走出工場手工業時代,進入了機器大生產時代。從一群人、幾臺攝影機就可以制造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的時代,進入到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國際化合作,投資巨大,對市場規模的依賴度也極高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里,電影工業,本質上已經是金融業的變體—金融是不同時空的價值轉換,多方資本投入,期待龐大市場給予倍數增殖。金融的特性之一,就是不斷要求更大的市場。
在新的條件下,零碎投資、局部市場、小格局的投入產出算計的影視制作方式,必然要式微,就像滿足于遐邇交換的家庭手工業無法與無遠弗屆的機器大生產抗衡一樣。
這個時候,能不能“拼得過”,談歷史已經沒有意義了—相當于說“我們祖上比你闊多了”。市場在哪里,中心就在哪里。
2018年,臺灣地區電影票房總量約為22億元人民幣,相當于河南省;同年,大陸電影票房總量約為610億元人民幣,臺灣地區年度總票房,接近《捉妖記2》一部電影的票房,而且《捉妖記2》只是排在當年大陸票房榜第6位。
在這個時代里,電影人想要努力,想要試驗,前提就是身處這個大市場里。離開了大市場,你不是一文不值,而是永遠不知道自己能值多少。
所以我們看到,進入21世紀以后,臺灣電視劇式微,香港電影衰落,即便在大陸內部,也發生了流行音樂中心從廣州向北京遷移的過程。華語世界的電影人、音樂人,百川歸海。
最后一次
金雞(百花)獎“拼得過”金馬獎嗎?這仍然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
金雞百花獎有許多缺點,這是中國大陸觀眾非常清楚的,比如,它的“土味海報”一直飽受詬病;它有時迎合流俗,把獎項頒給流量明星;有時主題先行的文藝晚會風,也讓它稍嫌刻板;它兩年才舉辦一屆,參展作品顯得陳舊。
在這個時代里,電影人想要努力,想要試驗,前提就是身處這個大市場里。離開了大市場,你不是一文不值,而是永遠不知道自己能值多少。
然而,這所有的缺點都是從與金馬獎對比中來,而且這個參照系還是過去的金馬獎,人們所假定的狀態也是過去的金雞百花獎。由于新的變數加入,所有數據都已過時。
觀眾是用腳投票的。如果有影響力的電影作品、電影人在兩個同時舉辦的電影展上集中于其中一個,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正如前面所說,一旦市場轉換,奢談歷史就回避了核心邏輯。
金雞百花獎雖然和金馬獎同期舉辦,看上去有一種隔海競爭的意味,但事實上,這不但不是一場同量級競爭,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場競爭。今年金雞百花獎辦得好不好,和金馬獎辦得好不好沒有必然聯系,因為兩者不是在同一個桌子上切蛋糕。就像兩個學生在不同地點參加考試,各自考多少分與對方無涉。
簡單地說,去年的風波,直接的邏輯結果不是金雞百花獎的崛起,而是金馬獎的衰落。
在今天的電影市場,北京的支配權不依賴于其他角色在主觀上是否承認。支配權表現在對市場的左右能力,所有的經濟、文化資源,都向著北京集中。
中心掌握著市場,因而掌握著分發權。在重建之后的華語文化體系里,金馬獎只是北京的文化分發權的一個部分,至少在過去十幾年里,金馬獎的盛況得以持續,相當程度上依賴于北京的默認。
這種權力,是由時代、社會演進自然形成的,這就是勢,勢的意思,就是排山倒海、不可逆反。
香港和臺灣,21世紀啟始階段都已完成了文化支配權的移交。只剩下金馬獎,作為一種特殊象征,得益于在特殊的兩岸關系之下對未來的共同期許,而尚能堅持。看上去是一種文化期許,實質上其基礎是政治期許。李安這樣的文化人,顯然明白其中奧妙—金馬獎的秘密,正在于形式上的“不破”。
倘若今后大陸電影不再參展,那么可以肯定,金馬獎的歷史結束了。它會繼續存在,但今后它將如澳洲的動物,在一個沒有猛獸的世界里自我感覺良好。與之相應的,是文化話語權的再一次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