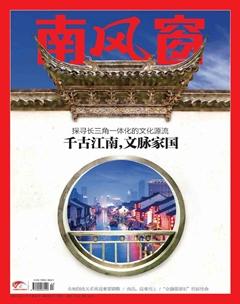蘇聯時代俄國的計算機為何不行?
徐英瑾

眾所周知,蘇聯長期以來是美國在科技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相關的人才儲備也非常豐富。但奇怪的是,其整個計算機科學領域,研究成績都遠遠落后于美國。這到底是為何呢?
實際上,早在二戰之前的1940年,美國IBM公司就借給了蘇聯政府一臺早期計算機,叫所謂“穿孔分析機”。美國人給蘇聯人這套設備的本意,是讓蘇聯在博物館展覽給公眾看新鮮。沒想到在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就以國防需要,干脆扣住機器不還了,IBM連一毛錢也沒收到。還真別說,這機器還真在戰爭中派上了大用場。1943年斯大林要去德黑蘭與羅斯福、丘吉爾開會,這樣一來,如何設計出一條從莫斯科到德黑蘭的最穩妥的航線的任務,就交給了這臺美國來的IBM的機器。因此,如果說蘇聯當局不理解計算機技術的意義,恐怕是不妥當的。
但與美國相比,蘇聯人對計算機的用處的理解還是顯得膚淺得多。二戰時,英美的計算機在密碼破譯、彈道計算、防空火力控制等各方面都大顯神通,而其在密碼破譯方面的工作又直接催生了圖靈測驗等有趣的人工智能研究課題。蘇聯的數學家雖然也很牛,但情報工作大量依靠人力諜報網,而在機器密碼破譯水平方面,可能連波蘭這種小國都比不上,遑論英美。冷戰大幕拉開后,由于蘇聯內部的技術資料管制,西方先進學術資料很難為蘇聯科學家所讀到,美國維納的名著《控制論》竟然一度被列為禁書,甚至“人工智能”也被一度打上“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名號。雖然在赫魯曉夫時代,禁錮更少的蘇聯科學家得以開始比較高調地宣揚控制論思想,但是由于信息閉塞,他們對于美國同行在符號AI與人工神經元網絡方面的技術進展的理論基礎,其實并不熟悉。同時,在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下,像“蘋果”那樣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計算機創新企業幾乎也是不可能誕生的,這也在根本上限制了蘇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
蘇聯官方試圖推進國內計算機應用水平的最富雄心的計劃,乃是六十年代復制美國IBM-360計算機的計劃。IBM為了造出這臺在當時頗為先進的機器,雇傭了六萬新員工,并蓋了五座新廠房,可謂不惜工本,由此引發了蘇聯當局的注意。然而,IBM-360在蘇聯的對應物(蘇聯代號為“ES-EVM計算機”)卻被證明是一個失敗。關于這個技術丑聞,蘇聯時代的計算機研究大佬鮑里斯·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寫的《蘇維埃計算機技術先驅》一書中所給出的診斷意見是:蘇聯科學家根本就沒搞到美國計算機軟件的源代碼,而只能從其硬件構成與桌面表現倒推出其源代碼,其難度可想而知。但也有資料顯示,蘇聯人的確通過特殊渠道弄到了源代碼,但是明斯克工廠提供的芯片質量太爛,導致產品質量還是不行。同時,蘇聯也山寨了部分美國家用電腦,如喬布斯的“蘋果II”電腦(蘇聯的對應機叫“Agat”)。但因為仿造品單價高達5000盧布(當時1美元兌0.6-0.7盧布),根本就賣不動。
不過,有資料表明,計算機更多地進入蘇聯的生產生活,恰恰是在那些質量有些問題的美國仿造品進入運用之后,這也就是說,若僅從縱向比較的角度去看,對于美國產品的研究的確提升了蘇聯的計算機生產的水準。蘇聯計算機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對高性能芯片的技術禁運,以及蘇聯因為材料加工技術的落后所導致的本土芯片的性能的落后。同時,因為缺乏真實的市場競爭,蘇聯設計者也很難真正理解喬布斯的電腦設計理念:把產品當成藝術品來設計。當年蘇聯技術失敗之教訓,今日之國人當深深借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