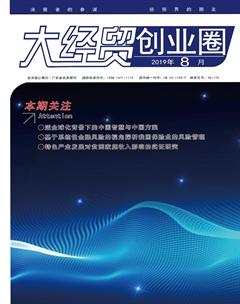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探究
【摘 要】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自設立之初就有明確的功利性目的,是刑法分則中飽受爭議的罪名。在反腐敗斗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本罪的固有缺陷導致司法應對的捉襟見肘,其應有的預防犯罪、懲治犯罪的功能也難以充分發揮。本文通過對域外類似罪名的成功立法經驗的比較和借鑒,反思我國關于本罪的立法規定的缺陷與不足,提出有針對性的修改方案,希望能夠對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幫助。
【關鍵詞】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財產申報 量刑 法定刑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自設立以來,雖然在司法實踐中充分發揮了其懲治貪污腐敗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本罪法律規定的特殊性以及不完整性,在實踐中本罪大多是作為貪污、賄賂犯罪的兜底性條款適用,很少有單獨以本罪定罪量刑的情形。這與其自身固有的立法缺陷、制度缺陷是分不開的,本文立足本罪的立法規定,認真檢視本罪立法設置中的缺陷與不足,在充分學習域外經驗的同時,結合本國的本土問題,對本罪的相關刑法條文規定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議。
一、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比較
懲治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犯罪規定并不是我國獨創,目前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與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相類似的規定。要對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進行立法完善,必須對域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經驗進行學習和借鑒。與我國相比,域外關于財產來源不明犯罪的規定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財產范圍方面
在國外的相關立法中,財產來源不明中的“財產”的范圍不僅限于公職人員本人的財產,甚至包括其親屬或其他關系人的財產,與我國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件中“來源不明”的財產范圍只局限于國家工作人員本人所擁有、支出的財產的規定截然不同。例如新加坡 1970 年的《防止腐敗法》中將財產來源不明的財產范圍界定為該政府公務人員本人、配偶及其子女所有或占有的全部財產。
這種將政府公務人員近親屬的財產也納入到來源不明財產范圍的規定,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工作人員將財產轉移到其他親屬名下以規避法律的現象發生。我國目前的立法中僅將國家工作人員本人的財產納入到本罪來源不明的財產范圍,對于與其共同生活的近親屬名下的財產則沒有規定。
(二)刑罰適用方面
目前我國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刑種確定為有期徒刑和拘役這兩種自由刑,沒有規定財產刑等附加刑的適用,但在域外立法之中,對于該類犯罪的處罰除了適用自由刑外,一般都附加適用罰金刑。例如新加坡的《防止賄賂法》規定,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重可以判處監禁刑七年,可并處一定數額的罰金。這些國家都將此類犯罪的刑罰規定為罰金刑和監禁刑兩種,這種附加適用罰金刑的規定,能夠在追回行為人的非法所得的同時,部分彌補國家和社會的損失,削弱行為人再犯罪的能力。
(三)財產申報立法方面
財產申報立法與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關系密切,財產申報制度可以說是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前提性制度。與我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財產申報方面立法的情形不同,域外各國家和地區財產申報方面的立法相對比較完善,有些國家甚至將財產申報方面的規定納入憲法之中。英國1883年通過《凈化選舉、防止腐敗法》,將財產申報制度正式確立下來。自此之后,很多國家紛紛通過制定出有關官員財產申報的法律將財產申報制度加以規定,以便對國家公務人員的行為加以約束。另外,在聯合國《反腐敗的實際措施》中也對公職人員公布財產和對隱瞞不報的懲罰作了具體規定。
國外關于財產申報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要求任職時對自己的資產進行申報,例如法國《資產透明法》規定,各級政府人員的財產清單應當在被任命或上任后 15 天內向有關部門提交;第二,財產申報范圍不僅包括本人財產,也包括家庭財產,例如美國《政府官員與工作人員道德行為準則》要求公務人員的配偶、子女必須進行財產申報;第三,將在任職期內的收入情況進行申報登記;第四,對不誠實的財產申報行為進行制約和懲罰。域外財產申報方面的這些立法規定相對來說較為完善,能夠較為全面地監督政府公務人員的財產狀況,我國在進行財產申報立法時可以在這些方面有所借鑒。
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議
(一)罪狀設置的完善
在刑法第395條“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的表述中,缺少有權責令說明的主體;同時“可以責令”的說法不嚴謹也不合理,在司法機關沒有責令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說明義務并不應該因此而免除,同時授權性的規定也不應該出現在實體法之中。筆者認為,“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的表述不當,以“偵查機關責令說明來源后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說明來源”替換較為恰當。這樣的修改既能夠避免責令主體不明和“可以責令”的說法不合理的問題,又能進一步明確國家工作人員的說明義務,為本罪作為一種不作為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作為義務來源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據。
由于我國目前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財產申報制度,本罪缺乏前置制度,很多學者認為如果將本罪視為一種不作為犯罪,行為人不具有先行義務。“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說明來源” 相對于原來條文中的“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的表述,更能夠為行為人具有作為義務這一觀點提供邏輯支持。另外“偵查機關責令說明來源后”的規定,可以進一步明確責令的主體,既能夠明確偵查機關有責令國家工作人員說明的權力,又能避免程序性的權力規定出現在實體法中,這樣修改能有效地解決原表述中存在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應該以“偵查機關責令說明來源后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說明來源”代替“可以責令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的表述,以完善本罪的罪狀設置。
(二)調整法定刑
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具體調整,應針對其存在的不足對癥下藥。下面就本罪法定刑的調整展開討論。
1.增設量刑檔次
量刑幅度的合理劃分,對正確指導本罪的量刑裁判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刑法作為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實體性依據,如果其法律規定的模式失范,勢必會導致司法程序中審判結果的失當。目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定刑量刑標準劃分不合理,法條表述僅以“差額巨大”和“差額特別巨大”為標準,而對“差額特別巨大”的認定標準相關法律、法規都沒有表述,司法實踐中對該標準認定困難。對于本罪,應當根據具體涉案金額增設量刑檔次,適當提高本罪法定刑。
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犯罪主體所受到的刑事處罰應當與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30條第一款規定:“各締約國應該確保根據本公約所確定的犯罪受到的制裁與其危害性相當”。行為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應該與其所犯罪行相適應。本罪雖然是一個推定性的立法罪名,無法確定行為人的犯罪行為,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本罪中行為人的財產來源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本罪中行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嚴重性應當說與貪污受賄等犯罪危害性相當,就目前本罪最高10年的法定刑來看,提高法定刑是必要的。但對于本罪法定刑的提高,我們必須把握一個正確的度,結合本罪是一種立法推定型犯罪的特點,過重的刑罰與其自身地位難以符合。刑法的功能首先是保護然后是懲罰,對推定犯罪事實的該罪而言,過重的刑罰具有可能錯罰的風險。結合本罪自身特點以及司法實踐要求,筆者認為將本罪最高法定刑提高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較為合適。
根據《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的標準的規定(試行)》,目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起刑點為30萬元,很多學者認為相比較貪污、受賄罪而言,本罪的起刑點過高,從“零容忍”的反腐敗刑事政策出發,本罪的起刑點的確存在過高的問題,但結合目前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本罪自身的特點,將本罪的起刑點規定為30萬元是基本合理的。對量刑標準可以進行進一步細化,增設新的量刑標準“差額較大”,將原法條規定的兩個量刑幅度改為“差額較大、差額巨大、差額特別巨大”三個量刑幅度,同時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分別將本罪的自由刑的梯度設置確定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樣劃分既能對應性地反映不同數額條件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的高低,也能夠較好地適應司法實踐中的裁判習慣。對于量刑幅度中數額的具體確定則由相關司法解釋完成。
2.增設罰金刑
根據刑法第395條規定,目前本罪的法定刑主要由有期徒刑和拘役兩種主刑組成,附加刑并沒有予以規定。有期徒刑是本罪法定刑適用的基礎性刑種,是現代刑法文明篩除肉刑和恥辱刑等非人道刑種后確立的主刑種;拘役是一種短期自由刑,是在較短時間內剝奪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將這兩種刑罰處罰方法作為本罪的法定刑是合理的。但本罪將不能說明來源的巨額財產推定為非法所得,侵犯的法益具有貪利性的特征,只規定了追繳財產而沒有附加適用財產刑,行為人在經濟上不能受到懲罰,不利于本罪刑罰目的的實現。
財產刑包括沒收財產和罰金刑兩種。其中沒收財產是一種最為嚴厲的財產刑罰種類,是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一種絕對剝奪,主要適用于一些情節較重犯罪。正如貝卡里亞所言,“沒收財產是在軟弱者頭上定價,它使無辜者也忍受著罪犯的刑罰,并使他們淪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絕境”。這種刑罰方法不僅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還多少使犯罪分子的親屬受到“連累”,是對罪責自負的現代刑法原則的超越,所以我們必須謹慎對待沒收財產刑,一般不將其作為普通貪利性犯罪的刑罰方式。與沒收財產刑不同,罰金刑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幅度功能,能夠實現罪刑均衡,避免沒收財產刑對罪犯財產的過渡剝奪。適用罰金刑還能夠通過對犯罪行為負價值評價并剝奪犯罪人的某種權利,在犯罪人心理上形成威懾貪利犯罪的“反動機”。在本罪中,增設罰金刑較為可取,不但是對行為人的一種否定評價和懲罰措施,還可以部分地彌補行為人給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損失。本罪的罰金刑設置應該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根據行為人的犯罪情節和犯罪數額,確定對行為人所處罰金的數額。可以以行為人來源不明的財產數額為基準,同時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等其他因素,按來源不明財產的百分比處罰金。
另外,對于刑事案件中違法所得應該如何處理,刑法總則中已有明確規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律條文中再規定“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有重復之感,完全可以在該條文中予以刪除。對比刑法分則中其他罪名,無論是貪利性犯罪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對刑法總則中所規定的追繳財產或返還財產的規定都沒有再次在分則條款中贅述,而僅僅規定相應犯罪所應處的財產刑。追繳非法所得的財產僅僅是一種處理方式,并不是一種刑罰方式,既然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來源因其不能說明的行為而被推定為非法所得,那么這些財產就應該予以追繳。即使該條文中刪除關于財產差額予以追繳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也會這樣判決、執行,在該條文中再次規定完全沒有必要。
綜合前文所述,筆者擬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如下方案:“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較大的,偵查機關責令說明來源后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說明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差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差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參考文獻】
[1] 趙秉志、王志祥、郭理容:《<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暨相關重要文獻資料》,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14頁。
[2] 張峰、蔡永彤:《<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視野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律困境與制度適應》,《法學雜志》2009年第5期。
[3] 許海波:《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缺陷及其完善》,《山東審判》2005年第3期。
[4] 【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頁。
[5] 仲麗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探析——以其立法缺陷及完善為視角》,《學術交流》2008年第4期。
作者簡介:李陽(1991—),女,山東煙臺人,煙臺市人民警察培訓學校,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