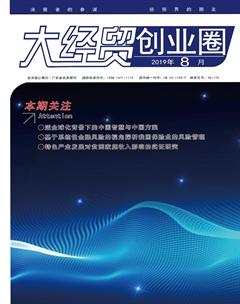本教“瑪果”儀式的文化解讀
那九 扎西羅伍 龍錯 羅伍措
【摘 要】 每年農歷的二月十三,若爾蓋縣茍象寺就要舉行“瑪果”儀式。過程是三十名身著古代鎧甲的青壯年男性俗人在寺院的大院里逆時針繞著“垛瑪”走不同的陣型,并發出整齊吼聲,最后完成在神山下的表演回到寺院方才結束,時間在十二分鐘左右。“瑪果”儀式所蘊含和表述的各種信息和意義才是筆者文內所要探討的重點。
【關鍵詞】 瑪果 茍哇 本教 儀式
一、“瑪果”儀式
(一)地理概況
“瑪果”儀式現流傳于四川省若爾蓋縣求吉鄉茍哇行政村的川北本教名寺茍象寺,茍象寺為中心的這一地區位于青藏高原的東端,安多藏區南部,處白龍江支流潘曲河的上游、川甘交界。茍哇分六個小村莊,現有103戶人家,人口600左右,其內部又分為不同的部落和族系。林地約有13萬平方米,草場約有12萬平方米,耕地約有3000平方米,境內還有若爾蓋縣第一高峰“戈藏佳則”神山,有著山川林立、原始森林廣袤、雪山草地森林并在等地貌特點,屬安多藏區游牧與農耕,附帶林業傳統的結合部。該地雖屬安多南部,但在方言上與牧區方言較為不同,諸多詞匯皆呈現出康巴方言的發音,筆者認為應當屬于康巴方言和安多方言的緩沖區,亦或交融區域。“茍哇”一詞有三種解釋:一說是因其相對于低洼地而處在高處平坎上,故名茍哇sgurba;一說是因茍哇境內因有“果倉班茍”(果倉九兄山),因此間數詞九的“茍”而得名茍哇;還有一說則是因境內有九個寨子,故曰茍哇。總而言之,“茍哇”名稱所具有的含義不僅是此地地理空間的指稱,指以茍象寺為核心,以農業為主牧業為輔的潘曲河上游流域地帶,是為地緣概念;還指世代居住于茍哇的藏族人,是人群共同體的指稱,是為族群概念。
(二)本教在茍哇境內的傳播
境內流傳“瑪果”的茍象寺全稱為茍哇象倉寺尊勝普及遍頌洲,是歷史上著名的本教寺院之一,歷史悠久,因屬寺眾多而一度成為川北本教的中心,有“南拉頂、北茍象”之說,在川北乃至如今的甘肅南部信仰本教的區域都具有很大的影響。“象倉”的“象”在藏文中亦有三種寫法:skyang、rkyang、spyang,目前認為三種寫法都只有使用頻率多少的區別,而非正誤之差,根據《茍象寺志》記載:“在茍哇境內的唐安村有一戶叫“象孜倉”(skyangrtsets-hang),簡稱即為“象倉”,因地處茍哇溝,故名“茍哇象倉”。早在唐貞觀年間的吐蕃王朝東征期間,本教就被隨軍的本教師和戍邊軍隊傳入了茍哇村在內的唐蕃交界的地區,民間傳說中就有當時的茍哇就有類似寺院的小型佛堂即傳播場所出現的說法。有史可考的雍仲本教則是由后弘期公元1080年左右誕生于茍哇唐安村的象帕大師在繼承祖先傳統的基礎上在本村陽坡上修建的象倉寺為標志傳入茍哇的,后來因為僧人數目的增加和規模的不斷增大將此小寺和原來的靜修院搬到嶺沃,隨著時間的推移就逐漸發展成為了今天的茍象寺。寺院歷任主持是由象帕及其后裔擔任的,至今共傳三十一代。由于舊寺志《苯查冒》已丟失,對于歷輩大師的傳承歷史,傳承代數也有分歧。寺院住持的傳承由最初的父子傳承變到叔侄傳承,最后由如今所見的活佛轉世制度所代替。以茍象寺為中心的“象派”在安多地區分布著眾多寺院,歷史上還出現過“內寺七座,外寺十八座,屬寺五十四座,持撅者一千五百人”的盛況。隨著佛教的深入傳播,加上大小金川事件的影響,茍象寺在內的安多地區本教信仰體系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很多寺院紛紛改宗。解放后在文革浩劫中寺院和信徒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等到1982年重新開放后到目前寺僧數量已減為20余人,寺院的眾多珍貴文獻亦遭受前所未有的損失,很多傳統亦未能恢復。
(三)茍象寺垛順節的介紹
茍象寺的“垛順節”(gdosrungduschen)”自民主改革中斷25年后,與寺院的重新開放一起于1982年得以恢復。“垛順節”在每年的農歷二月九日至十四日舉行,主要由法會和法舞、“瑪果”等重要儀式的舉行所構成。扎倉即寺院組織于九日和十日就開始準備,十一日和十二日誦讀經文。此間有個重要環節就是祭祀護法,尤其是祭祀茍象寺獨一無二的護法“阿塞騎虎者”。還為了給村民護身而在寺院的囊慶舉行招魂儀式。十三日和十四日的則是由茍象寺舉行新舊法舞和六時法舞的表演,以及展出并詳解春牛圖所構成。十三日清晨舉行由象翁仁青堅贊排練的僧仗儀式,僧人高舉各類幡幢寶傘,吹奏各種佛樂供奉曼扎。更有傳說象帕大師此時化為鷹飛抵寺院上空的奇異殊勝現象而有信眾朝拜的“拜鳥”活動。然后是來參加此次活動的茍哇村的軍人和全部俗人一起圍繞“垛”吶喊吼叫并轉圈,寺僧也會來助陣,最后在這樣一個僧俗不分的宏大場面中將“垛”拋出。另外還附帶有民間信仰亦或原始本教色彩的司巴喇達萊塢者即民間本教師舉行的祭祀山神、水神及部分“垛”的儀式,但在法會程序再度恢復之后此環節未能復興。類似茍象寺“垛順節”的活動在藏區并不少見,但這種僧俗共舞、俗人占相當比重的儀式則是此地所特有的文化現象。在寺僧主導舉行的神圣活動的同時,筆者所關注由茍哇村俗人組織的“瑪果”儀式作為“垛順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其中舉行即表演中。
(四)源流
本教信仰體系下存在的民間信仰和信仰者們即茍哇村民對于“瑪果”儀式的起源和發展與世界諸多原始信仰共同的解釋:給當地傳奇式杰出人物冠以神秘色彩并以傳說故事的形式流傳在民間。根據茍哇村民的口述和相關文獻記載可知:“在茍象寺的東邊,環繞著岷山山脈尾部巍峨而綿延不斷的九座山峰,當地人將這九座山峰認定為了九個生死不離不棄的兄弟,因而名為果倉九兄山其中的果倉佳則峰是若爾蓋縣境內最高峰,前文中就提到過。“果倉九兄山”因司巴本教萬有靈論的影響而受村民膜拜信仰,成了本教象派的守護神,不僅在茍哇還輻射周圍而成為了較有名氣和影響力的神山,千百年來就一直充當著當地人的保護神并履行職責護佑著這片土地以及人民。相傳當年本教安多三圣人之一的前文提及的茍象寺的建寺大師象帕一世活佛來到白雪皚皚、渺無人煙的果倉九兄山山頂,突然間從寂寥的山間傳出一陣陣‘嚯、‘嗬交雜的聲音,大師因不解頓生好奇心,循著聲音的走上前,到聲源處細聽是戰場殺敵的震天吼聲。等仔細觀望才看到,在白雪皚皚的山間上,有一對身穿絳紅色藏袍的軍隊披著盔甲、腰上佩戴著銀飾的帶子,右手持刀,左手拿刀鞘,面帶怒容,列隊前行,忽而作貓腰躬身、忽而又作起身吶喊狀。大師心想:如此高峰,又有如此大雪紛飛的天氣,山上怎么會有人且有如此劇烈的活動呢?繼而大師以其神通入定細辨,才發現原來是古代吐蕃遠征將士的魂魄在做戰斗狀。這些將士是在久遠的時代就已經為了吐蕃王朝的霸業、為了生存和信仰而戰死在疆場的,雖早已馬革裹尸,但魂魄沒有忘記使命和職責,而在這里繼續驅趕邪惡和維護安寧。之后象帕大師以其超人的智慧還原了這個場面,并將它編導成舞蹈儀式的形式,定于每年農歷的2月13日寺院法舞前舉行,距今約有九百余年的歷史,這才有了瑪果儀式的習俗傳承”。傳說終歸因為人們本著神圣化其主人翁的精神和目的流傳的,但其中真實可信的部分自然也是存在的,象帕大師創立“瑪果”儀式是毋庸置疑的,筆者大膽猜測“瑪果”儀式極有可能是象帕大師在果倉九兄山某處修行時創立的,因而民眾會將二者并而論之。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公元七世紀到九世紀中葉,吐蕃與唐之間戰事不斷,許多吐蕃遠征將士屯守在松州、潘州一帶的山谷及岷江兩岸。歷史上,茍哇是潘州包座七房中的一個部落,潘州與松州是兩個不同的設置衛,明代合并方稱為“松潘衛”。這些從吐蕃各地征召起來的將士在吐蕃王朝分崩離析之后,為了不忘祖先武功和履行保境安民職責的軍人使命自發的組織了重溫戰斗的“瑪果”儀式,這項儀式久而久之受歷史的長河里先后被原來隨軍的本教巫師(現在成為“萊塢”和僧人等本教信仰體系的影響,最終演化成了與寺院組織共同完成的系列儀式即“垛順節”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最初發起人的現實目的在慢慢淡化。
二、解析“瑪果”儀式
如意大利藏學家杜齊所言“儀式對理解古代人類思維活動方式是至關重要的”,瑪果儀式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當地古代先輩們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能夠溯本追源進一步窺出茍哇村的發展概況和族源等相關的歷史信息,能夠使我們對原始的本教和民間信仰的儀式儀軌在當地的出現和發展有更深一步的了解。“瑪果”的獨特性和世俗性也是我們從側面揭示其所具備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的重要原因。
(一)追根溯源-“瑪果”儀式的歷史信息
在歷史信息這一層面,儀式可以帶給我們的是關于當地人們的族源與血統的問題。根據當地人的口述,我們得知:早在直貢贊普進行第一次滅本活動的時候,就已經有一批來自阿里的逃避法難的本教徒逃到了今天的茍哇境內,并在此處定居弘法,這是我們所搜集到的關于茍哇人族源現存最早的說法。而茍哇境內的藏族居民的族源與“瑪果”之間的究竟存在著何種關聯?如何在儀式中尋出關于族源呢?這是我們將要探尋的問題。根據文獻記載的茍哇村的相關歷史變遷過程為:茍哇在內的若爾蓋縣原隸屬松潘縣管轄,吐蕃之前皆記載為帶“羌”或類似“發羌”的民族。自商周西漢時期,若爾蓋地區屬白馬范圍。北周時,始置通軌縣(在下包座),隸屬榮鄉郡,隋時改隸汶山郡。唐初仍置通軌縣,另置利和縣。吐蕃東進之后盡為吐蕃疆域。元朝在求吉鄉境內建置潘州,明朝并松州,合稱為松潘衛。民國時期屬松潘縣轄。民主改革之前是包座七房之中的大部落之一。
對于藏族的族源,學界多認同古羌人是藏族的前身,羌人起源于山川河谷眾多的青藏高原與內地的交界地區,“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祈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這段出自《新唐書吐蕃傳》的話精確的概括了吐蕃即藏族的族源、數量、居住環境、分支乃至祖先等多方面的內容。姚薇元也在他的著作中同樣也提到了這個問題:“要言之,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約當東晉時,其中一部名發羌者統一諸部建立大國,諸羌因皆號發族,而對異族稱‘大發。”羌人在古代非單一的族稱,自商周到秦漢再到隋唐,活動在西北西南地區的各族人民均被中原漢人泛稱為“羌”。《后漢書西羌傳》中記載:“羌人無戈愛劍的曾孫忍、舞的后代各自為種,任隨而立。或為牦牛種,趙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這里所說的牦牛種、白馬種、參狼種大體上與藏族古代“四大氏族”之一的“董”氏后裔日臻繁衍成眾多大小不一的部落相同,其活動的范圍在今安多藏區的果洛地區、甘南及川西北藏區,而這正是漢文文獻中常出現的黨項羌活動的地區。吐蕃悉布野王朝從青藏高原腹地山南雅礱河谷崛起后迅速向東擴張,高原上的各部族先后被贊普王室所統一,第一次實現了有共同祖先的各部落的統一,這其中自然不乏前文所述之西羌各部族。在近千年的歷史長河里憑著三十幾代贊普的努力逐漸統一了諸部族和王國,到三十二代松贊干布時期建立起的強大的吐蕃王朝完成了從雅礱河谷到拉薩河谷,從松散的部落聯盟到逐漸具備精細分工明確的行政機構的過程。而青藏高原嚴峻寒冷不利于人類生存繁衍生產的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極度匱乏使得處于新生的帝國必須通過不斷征戰擴張來拓展疆域、掠奪戰利品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保持自己的強大。所以唐與吐蕃的戰爭是在所難免的,根據《舊唐史吐蕃卷》記載: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吐蕃和唐就因為首次和親失敗的原因在松州一帶進行了第一次忽有勝負的第一次交鋒。在吐蕃統一青藏高原的過程,吐蕃人與當地原住民(羌、氐、黨項、吐谷渾等族群)開始交融,“古羌人同當地藏族先民的自然融合,是安多藏族的主要來源,是其形成的基礎而且時間也最早,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終形成了今天安多藏區的部分藏族,茍哇村就屬于其范圍中。其實,任何一個民族的形成都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族源所演變而來的,演變過程和基因也不是固定而絕對的。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中融合同化,再融合再同化的范疇。而“瑪果”儀式所存在的茍哇村就處在這條狹長的唐蕃即后來的漢藏交界處,此地的藏族即是屬于藏人四大支中的“東”(ldog)氏后裔,是典型的上文所述的安多藏族,但在方言和各類習俗上還是有著細微的差別。
(二)“瑪果儀式”的社會功能
任何文化的存在都具有其功能意義,文化實際上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文化是一種物體、態度、活動的體系;它是一個整體,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文化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使新的文化手段產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的領域對文化有著不同的解釋,這就決定了宗教與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是我們所不容忽視的。藏人的社會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宗教儀式,這些儀式有著不同的性質目的和表現形式。同樣儀式作為一種文化的范疇,它必然具備了文化所應當具備的各類功能,“瑪果”儀式亦是如此。
1.精神慰藉的功能
“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重要危機都包含強烈的感情沖動、精神沖突和可能的崩潰。人們要想得到好的結果,就必須與憂患和兇兆作斗爭”。在藏人的日常生活或重大節慶時舉行的宗教儀式一般都有著精神慰藉的功能,這些儀式給處在氣候惡劣、生活生產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繁、人口死亡率高的這一高原民族提供了一套能夠抑制和超越現實痛苦的心理調節機制,使人們能夠安靜地適應和接受現實的變遷。茍哇的老輩僧人是這樣解釋“瑪果儀式”的:“首先是因為以前當地人們的生產和認識水平有限,面對各種不能夠抵御和防治的自然災害,自然認為這些動態的背后一定也有個力大無窮的指揮者或主人,舉行“瑪果”儀式就是討好性的祭祀當地的最大的神山果倉九兄山,祈求它用它的力量保障當地的男女老少安居樂業。后來藏族社會分崩離析十分混亂,在茍哇也是出現了偷盜者與搶劫者橫行的情況,這時候舉行“瑪果”儀式并聚集身強力壯的男性是為了震懾那些匪徒。”當地人們認為舉行了“瑪果”儀式的時候,神山的力量會附著到三十名表演者身上,會使得前來侵犯的現實惡人、另一種生存狀態的污濁物種望而卻步,從而保一方平安。現實中三十個平民組成的隊伍無論身體還是心理的素質都決定了他們的戰力并不會如人們想象的如此強大,正是因為冠上了信仰的元素才實現了觀念與心理意義上的強大。在儀式舉行的前后時間段里,村民們的心理狀態從渴求得到滿足,并在儀式完成后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安慰。雖說現在社會和諧,人們安居樂業且沒有紛爭,但果倉九兄山一直是當地人心目中最神圣最有威力的神山,他們相信牧草豐茂、牛羊肥碩、糧食豐收都是神山對人們的恩賜,所以“瑪果”儀式解決了神山與當地人之間的關系,而解決方法就是在用慰藉人心理的方式去慰藉神山,從而達到一個平衡共存的狀態。
2.文化功能
文化是相對于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的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在藏區,各種相關于宗教的儀式儀軌文化無處不在,很少有儀式同宗教的活動和行為脫節。宗教活動在基本都是以寺院為中心而舉行,而藏傳佛教的寺院兼備著傳播宗教和傳播文化的雙重功能。“瑪果”儀式雖然是唐安土官主持進行的,但其所隸屬的“垛”的整個過程都是茍象寺在負責舉行,所以它離不開寺院和寺院的影響。舉行“瑪果”儀式時,茍哇整個地區的人們都要來參加瞻仰。一方面寺院配套的在當天舉行的一些講經布道和教育的法事活動,使得平時忙于從事農牧業勞動的群眾得到一個可以粗略學習人文知識的機會。另一方面,長時間忙于生產生活的農牧民難得參加此類大型群體活動的機會,人們可以在此儀式舉行的當天進行隨機而盡興的交流,從上年的儀式之后不同村寨在一年內積累的不同特點的文化形式在當天得到互換,從而達到文化傳播共享的目的。
3.社會整合功能
社交是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際來往,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方式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意識,以達到某種目的的各項社會活動,社交活動的基礎必須要是建立在人群聚集的場所。在平時的生活中人們大多是見不到且認識不到除了自己的親戚與鄰居以外的其他人,儀式的舉行給當地群眾提供了寶貴的聚集機會,很多來自不同村寨的很難相見的親戚或朋友在這一天就得以一見,陌生的人們也有了見面認識的機會。一種情況是許多家庭往往會在舉行儀式的幾天里,通過與親友的交際,借機開展子孫輩的聯姻事宜,當地大部分由家族出面組成的家庭都是在這一天完成的。另外一種情況則是青年男女在當天于千萬人中自行交流,從而不乏墜入愛河組成新家庭的例子。從這些方面我們不難看出“瑪果”儀式的舉行間接地也影響到了社會結構的組合,因而不勉強的具有了整合功能。
(三)儀式的表述行為與身份的回歸
首先,作為一種身體表述實踐,瑪果的表演隊伍有著特定的表演空間和表演動作,即通過集體在特定空間中的身體運動來進行,具有自動化和規定化的雙重特征。寺院的神圣儀式一結束,瑪果的表演就立即開始,旗手會引領著隊伍,一個動作引導另一個動作,從寺院的廣場到草地,直到下個儀式跟上個儀式,才算順利完成。關于它的表演動作和形式有著一套系統的文化規定性,包括節奏、方向、排序,在何處表演或舉行,什么時間內表演等。這套規定性的解釋早已融合進了當地的傳統觀念之中,不可剝離,亦無法分離。其次,這種身體的表述行為因其文化的主體而呈現。在藏人的文化社會中,人們并非盡是使用書面或文本的形式完整的記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概念上的儀式是難以認知的、沒有文本記錄的,這一點上瑪果卻有所不同。表演時,表演者通過身體本身進行表述,看似松散的動作實際上是經過高度結構化的,它可以為族群的記憶、表述、感知提供一個共同的氛圍或場域。它旁證了瑪果儀式的身體實踐是文化記憶、生活經驗與認識并行的表述行為,并與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發展相結合的表述行為。因此,瑪果儀式在當地人的行為特性和文化特性中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關聯,在此意義上,以身體本身來表述不僅是茍哇村民觀念表述的另一種方式,且某些特殊的根本上的超越正常性的認知只能用此方式來表述。最后,它構成了圣與俗之間某種特殊的“中間表述”的類型。在茍哇村民的傳統觀念中,宇宙和世界是六道諸生亦或人、神、自然萬物共處混居的動態平衡系統。瑪果儀式作為文化的表述行為,一方面鏡像了當地傳統本教信仰形態的神圣世界觀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地歷史和現實中的社會文化結構。“族群表述實踐由于其意義指向而區分為神圣與世俗兩大類型”。瑪果儀式用身體實踐進行文化表述,但卻無法粗略地歸納入神圣或者世俗,而是用其構成了某種特殊的“中間表述類型”。它打破了原本神圣和世俗的二元對立建構,一方面使得儀式的行為本身具備了神圣與世俗融合的特性,另一方面還給當地村民在其他日常生活中打通圣俗兩個世界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表述模板和契機。這種以人為主體,并娛于神的方式不僅達到了表達了當地神圣的宇宙觀念,也在成就神圣儀式功效的同時,促成了茍哇地區世俗化族群的凝聚和整合。以身體為重要介質的文化表述實踐,在多元文化并存和文化沖擊中可否繼續保持并發展、在語言介質的文化表述中可否實現跨實踐行為和文化的理解和發展呢?這是留給我們的問題。
儀式的表述行為在多元的族群交往互動過程中衍生出來了文化外部的認同功能。一方面,通過“瑪果”儀式這個表述實踐促進“茍哇”這個文化共同體自身的認同凝聚;另一方面,通過這一表述實踐達成與他者區分邊界的目的。以認同實現凝聚的族群表述首先是一種對自我身份的一種界定,是社會文化生活共同體中形成和維持自我感覺的重要方法。但這種行為不是一種沒有依靠介質而發生的,它發生在已形成具有嚴密序列性的涉及此共同體過去社會記憶的表述對象和內容的范式中。所以,作為自我界定的儀式表述必須通過選擇性的組織起與當下主體有連續關系的動作,然后與過去相連接做出一個恰到好處的表述。在相當程度上利用起歷史中的傳統創造一些新的傳統的歷史,是可以認為是利用表述行為來消除和掩蓋過去的“我”與今天的“我”之間可能存在或者可能出現的斷裂。不論文化共同體即茍哇村民建立起的自我界定的表述儀式是源自真實的,還是經過虛擬想象,儀式的表述行為總是在一定層面上使得這種自我的認知和界定發生并加強。儀式被舉行過中成就的自我界定同時還包含一種“集體自我”。“瑪果”儀式在舉行中,個人個體性的表述并不是它所具備的目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此過程中表演個體必須竭力將自身凸顯的個性和差異性隱藏起來,仿佛如此才能更好的參與到儀式的完成即集體性的表述行為之中。“垛”與“瑪果”為茍哇村民提供了一種集體性、公共性的表述場域,建構起了具有約定俗成性與群體性的表述規則,特別的將此儀式表述加進了整個藏人的共有傳統的內在框架之中,促進了“自我”的認知凝聚和對“他者”的強調。每一次舉行儀式時,表演者即參與者所共同享有的身體經驗和他們所感知到的情感狀態不需要太多語言的中介和詮釋,他們只需在臨時建構起的“集體自我”系統進行內部交流得出特定的結果,即得到社會群體互動的基本情景亦或狀態。隨著這種認同觀念在儀式中的加強,身體所具有的知識和生命所具有的經驗變得更具普遍和趨同。因此從認同感這種層面的意義上講,“瑪果”儀式使得茍哇這一區域的社會群體被儀式中的參與人員攜帶從各方面參加和滲入到儀式的各個過程中,進而使得他們每個人的“集體自我”的強化和“個體自我”的淡化,最后導致一種特殊的“自我”感覺的出現和形成。作為一種集體性的表述實踐行為,“瑪果”儀式應該算是一種當地村民尋找并強化“自我”認同建構最行之有效的較為“自然”的方式。總之,關于此共同體(茍哇)的認同不僅取決于主體(表演場域內的村民)自身所表述的觀念傳統,也取決于表述發生的具體動機、行為和方式。這樣的文化表述實踐方式既可以維持共同體自身的存在,既能夠表達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過程,又可以不斷通過對外來文化差異的處理來調整自身的認同邊界,也可以促使處于主體身份的當地人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理解自己,以便對“我”與“他”進行區分。
三、問題與反思
儀式自八十年代與茍象寺一同恢復以來,表面上是一種逐漸復興、影響不斷擴大的狀態,但有些傳統卻在歷史的前進步伐中漸漸消失:由于本地“萊塢”大多去世或后繼無人,最能體現民間本教色彩的為參加儀式的俗人進行作法護身、招魂等系列的內容現已被忽略而消失;很多村民對此儀式只有特別有限的認知(有關傳說、由來、形式等),認識的程度參差不齊村民參加儀式的目的也不僅是最初的尋求庇護保佑,伴之諸多獵奇思想;新一代接受過系統學校教育的年輕人也在對其儀式迷離模糊的認知中徘徊,他們接受新知識在一定程度上給儀式的傳承造成了潛在的威脅;多數村民都是莊嚴來簡單走一下儀式的神圣程式,而并非因為其初始目的而參加。這些關系儀式的傳承與發展的問題,無疑例外的都是受到了外界文化的沖擊。
“瑪果”該何去何從,儀式場域中的當地人或繼承者們又該如何在儀式中反觀歷史、面對現實、走向未來呢?(一)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利用政府的財力和號召力對其進行宏觀的保護(如用電子產品記錄儀式的整個過程);(二)建議寺院在儀式舉行期間單獨安排時間對村民進行普及性的講解和介紹,使村民明白儀式存在和舉行的意義所在;(三)僧俗文化人士應當通過加強整理和編輯相關資料的力度,使儀式傳承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條理性的來源;(四)在儀式舉行過程中,應主動引導對儀式感興趣的青壯年參加,使他們認識和掌握儀式舉行的程式和意義,為以后的傳承奠定基礎;(五)大力倡導村民讓孩子接受雙語教育,這樣能夠對其對了解和研究儀式、對儀式的傳承提供便利;(六)通過對外界的介紹,吸引外來人員參觀游覽,進而造就一些經濟效益,從而在整體上帶動村民保護“瑪果”的熱情。概而論之就是與儀式有關系的人們必須以建立文化自信心為基礎,接著讓諸多有著作用力的方法在其上進行輔助性的保護。
【參考文獻】
[1] [英]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 李菲.《嘉絨跳鍋莊:墨爾多神山下的舞蹈、儀式與族群表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3] 周華.《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4] 高曉楠.《若爾蓋縣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經典若爾蓋茍象寺“垛”》[M].成都:成都市源佳印務有限公司承印.2012年版
作者簡介:那九1996年藏族甘肅迭部西南民族大學藏學學院2018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藏漢翻譯)碩士研究生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學武侯校區(610041)
扎西羅伍1994年7月男藏族四川省若爾蓋縣西南民族大學本科畢業單位信息:四川省甘孜州白玉縣藏醫院 (627150)
龍錯1995年2月女藏族四川省新龍縣西南民族大學本科畢業單位信息: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人民法院 (626800)
羅伍措1995年12月10日藏族四川省若爾蓋縣本科畢業于西南民族大學(62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