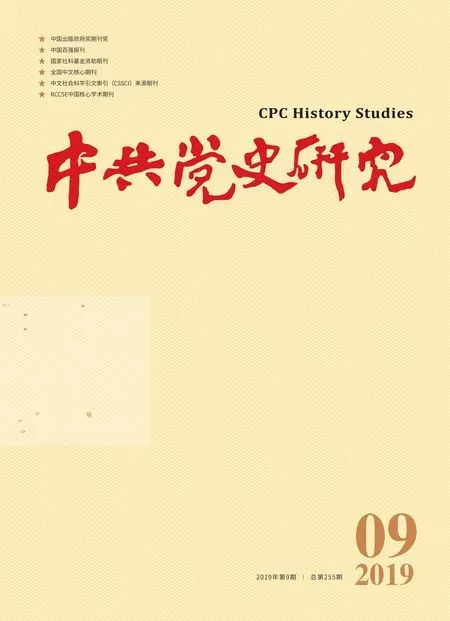新中國學習外國科技的轉向(1956—1966)
張 靜
冷戰時期,在堅持自力更生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中國科技對外交流大致經歷了由向蘇聯學習到向包括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外國”學習的轉向(1)學界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外科技交流的研究,大多關注中蘇雙邊科技合作與交流的過程,并從國際和國內因素分析雙方合作破裂的原因。而在中蘇科技合作出現分歧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對向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外國”進行學習的號召及其歷史語境,則并未受到學界足夠重視。。20世紀50年代,通過大批聘請蘇聯專家,大規模派遣留學生和技術人員赴蘇考察進修,大量翻譯蘇聯各類科技文獻和引進技術設備,中國國內掀起了學習蘇聯科學技術的高潮(2)沈志華總結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向蘇聯學習的三種途徑;張柏春等考察了蘇聯對華技術轉移的歷史;高白蘭(Izabella Goikhman)借助跨文化轉移的分析范式,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中蘇學術互動的實踐及其背后的中國政策,意圖挑戰既有中蘇學術交流研究中的“沖擊—回應”范式,強調中蘇學術交流中的互動性。參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35—336頁;張柏春等:《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高白蘭:《中蘇在1950年代的學術交流:質疑“沖擊——回應”模式》,白思鼎、李華鈺編:《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29—358頁。。在科技領域,中國學習的對象由特指蘇聯轉向泛指外國,無論在語義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既非緣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蘇交惡、學習蘇聯受阻,亦非萌發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局,而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面向蘇聯學習最高潮之時便已發生(3)關于中蘇科技交流從合作到分歧的時間,至少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蘇共二十大特別是波匈事件后、1960年蘇共中央全會三種說法。參見李濱:《“三扁擔,扁擔三”:蘇聯專家在中國人民大學(1950—1957)》,白思鼎、李華鈺編:《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第329—379頁;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第210—214頁;張柏春等:《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第349—354頁。。
本文在厘清“向外國學習”的內涵與語境的基礎上,將科技人員的跨國交流與科技文獻的跨國流動作為考察科技領域“向外國學習”的兩個主要方面(4)本文借鑒了高白蘭提出的國際學術交流的三個主要層面——政治政策、實踐和話語形成,但限于篇幅和資料,包括設備引進的實踐、專業性學術話語的形成、兩次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的實際執行等問題,不在本文研究范圍內。。前者包括各類外國專家的引進,以及科技人員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展開短期訪問,參加培訓,出國留學等;后者包括科技文獻的多邊互換、通過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帶回、直接訂購,以及通過第三方、第三國間接購買等。通過梳理分析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冷戰背景下中國科技領域對外交流學習的態勢,本文將探討新中國學習外國科技中的“變”與“不變”。
一、“向外國學習”的內涵與語境
論者在闡述中國領導人“向外國學習”思想時,大多溯及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然而,若從政治與執政思想上追溯,這種轉變的發生或許更早。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毛澤東在會議最后一天講話,論及是否以及如何向外國人學習,質疑有些人持有的“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用夷變夏’,就有問題”的觀點。在他看來,向外國學習的目的既不是“用夏變夷”,也不是“用夷變夏”,而更似“洋為中用”。他說:“社會主義不是出在俄國,俄國也學會了。外國的好東西,我們統統拿過來,變成我們的東西,要在一、二十年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他還以漢唐樂舞為例論證道:“漢朝、唐朝就是這樣的,唐朝奏樂舞蹈有七種,有六種是外國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變成中國人的。”(5)《學習文選》,出版社不詳,1967年,第106頁。
為了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中國需要知識分子,需要科學技術。在毛澤東看來,發展先進科學技術是新中國在工業上、軍事上擺脫對外依賴的前提,也是應對現代戰爭、保障國防安全的基礎。他說:“我們吹牛皮吹不起來,工業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重要的工業裝備和精密機器都不能制造……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這就需要依靠大批科技人員、知識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趕上世界水平”。我們“應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發達的國家”。他指出:“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6)《學習文選》,第108—109頁。
周恩來在此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時,更明確地強調了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他指出:“高度技術”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前提。科學是關系中國國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條件同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在一起,無論在和平的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戰勝帝國主義國家。”所以,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然而,中國科學文化力量的現實狀況卻是“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上也要低得多”,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鑒于此,周恩來強調: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最終目標是“在不很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實現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號召——‘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為了實現此目標,周恩來號召:“我們必須首先打破那種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松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要“作出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有系統地利用蘇聯科學的最新成果”。總之,要“認真地而不是空談地向現代科學進軍”。在“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下,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加強理論科學研究,為發展科學研究準備圖書、資料,改善外國書刊進口工作,擴大外國語教學和外國書籍翻譯等問題,也被一一提出。(7)《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60、181、182—183、180、189、167、185頁。
從上述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此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來看,科學技術被視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國家安全的關鍵,而向外國學習是中國縮小并最終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的重要途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領域,蘇聯不再是“無限期地依賴”的對象,“其他國家”也被當成中國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目標。會議結束后,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報》以《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毛澤東同志號召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為題,在第一版報道了這次會議以及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席卷全國。
三個月后,毛澤東先后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談“中國與外國的關系”。這被認為是毛澤東“向外國學習”思想的經典表述。(8)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有學者援引《論十大關系》講話中第十部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的內容,論證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其論述中一個重要的邏輯便是毛澤東主張向國外學習。不過,其所賴以分析的《論十大關系》講話文本,均為1975年鄧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頓時為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第5卷而讓胡喬木整理的稿本,亦即1976年12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版本。該版本隨后被《毛澤東年譜》《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輯錄。而目前已知,除了兩次會議記錄的未刊稿本、其他領導人的傳達闡釋本外,至少有三個下發傳達稿本。經過不同整理者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刪改、增添后,想要由1976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本探求講話原貌,自然是十分困難的;況且因為毛澤東本人不同意,幾個版本未能在其生前正式公開發表。總之,今人以1976年公開本分析毛澤東1956年時的思想,難免“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參見張建勤:《論毛澤東關于“向外國學習”的思想》,《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文英:《“向外國學習”:毛澤東的一種對外戰略思想》,《延邊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陳勝余:《略論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王海光:《〈論十大關系〉文本的形成與演變及其經典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李桂華、齊鵬飛:《毛澤東生前未公開發表〈論十大關系〉的原因》,《黨的文獻》2018年第5期。從目前能夠找到的三個版本的論述來看(9)1956年四五月間兩次講話的記錄稿在此后20年間被多次修改成不同稿本。這里所說的三個版本是:1956年4月25日的記錄稿、1965年陳伯達整理的版本(參考“文化大革命”時期流入社會的由群眾組織編印的出版物),以及1975年胡喬木主持修改并印發全黨的討論稿本即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公開本。不同稿本的差異可以用來厘定毛澤東思想的變化及政治情勢的變遷;其共通之處則能夠呈現毛澤東1956年已經成型的思想與觀念歷經20世紀六七十年代依舊大致未改的本相,有助于后人參透其根本意旨。參見《鄧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7—273頁;《學習文選》,第131—133頁;《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44頁;王海光:《〈論十大關系〉文本的形成與演變及其經典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其所呈現的語意共通之處有五條:其一,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提得對”,但要堅持兩點論——一切國家、每個民族都有長處和短處,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學習的方針是“長處都(要)學”,“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其二,不要學短處,也不要毫無主見地跟風。其三,要學的是普遍真理,但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批判教條主義。其四,中國有兩條缺點,但同時也是兩條優點:一方面,中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我們的革命是后進的,輪不到我們來驕傲,不過,一為“窮”,二為“白”,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其五,將來“工農業很大發展了,科學文化水平大為提高了(國家富強了)”,也還是要謙虛謹慎,還是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一萬年都要學習。(10)括號中的內容是1976年公開本添加或修改的。此外,在1965年本里,沒有第一點中“我們的方針”和第二點中“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等內容。
顯然,第一條的兩點論是看待外國的基本原則;中間三條分別強調對于外國不學什么、不要怎樣學,要學什么、要怎樣學,以及看待中國自身也要堅持兩點論;最后一條確立了中國如果學會了、大發展了、富強了該如何自處的原則,特別提出要警惕“翹尾巴”。三個版本的論述前后跨越20年,對毛澤東“向外國學習”思想的呈現雖有所不同,但核心要旨一致:要在堅持兩點論的基礎上向世界上一切國家、每個民族學習,也就是為了中國的發展與富強,不再只是全面向蘇聯學習(11)毛澤東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后,中央領導人紛紛發表談話,強調不要盲從和迷信,不要一切依賴專家,學習蘇聯經驗要有分析。參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第210—211、225—226頁。,還要有選擇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而需要學習的時限則是“一萬年”。(12)具體分析三個版本第十部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的內容,在1965年稿本中沒有而在其他兩個稿本中出現了的,共有四條:其一,對待資本主義國家要區分“腐敗制度”與“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對于前者的批判不妨礙對于后者“好好學習(好好學過來)”。其二,“對待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比如,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三,“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筆者無法確定這一點是否出現在1956年稿本中,但1976年12月《人民日報》公開本中肯定是有的。)其四,在講中國因為“革命是后進的”所以“輪不到我們來驕傲”一句后,增加了幾句話:“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后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此外,1965年稿本中在談到一窮二白的狀況時,有幾句話是另外兩個稿本中沒有的,包括:“我們窮得很,又是知識不多。”“當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國勞動人民有豐富的智慧,而且已經有一批不錯的科學家,不是說都沒有知識。”“一窮二白,使我們的尾巴翹不起來。”
此時恰值全面向蘇聯學習的高潮,毛澤東卻發出了“向外國學習”的號召,其所釋放的微妙信號,很快被蘇聯駐中國臨時代辦B.利哈喬夫敏銳地捕捉到。1956年8月22日,他在致蘇共中央的報告附件《關于毛澤東所提出的十項方針》中提出:“特別應引起注意的是毛澤東關于利用蘇聯經驗的指示……毛澤東強調,中國應該向所有人學習,其中包括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學習人家的好東西。”他結合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描述了自己觀察到的跡象:“除了學習蘇聯和民主國家的經驗,現在正在積極采取措施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1956年,中國派往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增多。1957年計劃從資本主義國家購買多一倍的書籍。”此外,他還敏銳地發現:“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國黨和政府領導人的講話里出現一種傾向:號召以批判的態度利用蘇聯的成果。作為這一立場的依據,經常提出要反對機械地把蘇聯的經驗搬到中國,反對中國工作人員忽視中國的具體條件和形勢的特點。”(13)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6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25頁。
1956年不僅是中國領導人號召“向外國學習”最多的一年,而且大約也是從這時起,他們對于誰是要學習的“外國”、為何學習、如何學習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開始發生微妙改變。在厘清語義之外,發生這種變化的歷史語境及其呈現出的中國領導人的心態,可從三方面分析。
第一,從當時中國的外交狀況來看,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政府第一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并促成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協定的簽署;1955年的亞非會議是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重要實踐,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第一次臺海危機的較量打破了美國的軍事訛詐和“兩個中國”的外交圖謀,解放軍收復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1955年8月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啟,暫時緩和了臺海緊張局勢,中方提出了愿與美方就緩和遠東局勢、開展兩國人民往來及文化交流、在平等互惠基礎上準許對方新聞記者采訪等建議。在和平外交占據主導地位、外部環境趨于緩和的境況下,毛澤東于1956年初作出“世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可能維持和平”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論斷,認為和平的局勢有可能讓我們有12年時間,來基本上完成工業化(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17頁;《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頁;《學習文選》,第108頁。。正是在緩和、有利的外部局勢下,中國領導人擁有了不懼“用夷變夏”的心態和重現漢唐氣象的魄力。
第二,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已呈高歌猛進之勢,自信與樂觀是中國領導人無懼“以夷變夏”心態的底色。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兩天后,毛澤東在1956年1月22日會見外賓時說:“你們要看我們的落后,看落后如何向前進行,怎樣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逐步向工業國前進。我們現在不好,但將來會好的,我們是有希望的。”“這是從古至今的一條基本原則:弱小而進步的戰勝強大而落后的。每個民族都有長處,都有缺點。各國經驗可以互相交換,哪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經驗。”1956年4月10日,在同丹麥首任駐華大使談話時,毛澤東又說:“我們很愿意向你們學習,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1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16—517、559頁。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指出:“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16)《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7、89頁。
第三,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接連興起,科技界知識分子思想中“親美”“崇美”等所謂“洋奴思想”被清理。在全面學習蘇聯科學的大潮中,蘇聯科學界對某些科學理論的批判也被一同引入中國。(17)王揚宗:《思想改造運動與20世紀中國科學的轉折——以科學家的自我批判為中心的初步討論》,《中國科技史雜志》2016年第1期。在不斷高漲的政治運動中,高校與科研機構中的黨委、黨員、團員與“舊教授”,特別是留學歐美的非黨員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越發嚴重,后者的政治地位、學術地位岌岌可危,以至于性格溫和、行事平淡的周培源在1954年9月同北京市高校黨委辦公室來調查的人員對話時,說出了一段有些“出格”的話。他說:“科學工作者如何發揮作用問題,至今未很好解決,幾年來科學工作者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覺得發揮力量不夠,英雄無用武之地,懷才不遇,心里總是很不開朗。這種感覺很普遍,覺得黨沒有把我們的才能肯定下來。”(18)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43頁。不過,當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又很快成為不可或缺的力量。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說:“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沒有他們就不行了,單是我們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們的黨員作廣大的教育。”第二天,他特意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道聽取了中科院四位科學家的報告,并提議“今后每月可組織兩次這樣的科學報告,對大家都有好處”。(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15、516頁。中國科技界“百家爭鳴”的短暫春天很快就要到來了。
二、科技人員的跨國交流
科技知識的跨國流動歸根結底要以人為載體,科技人員的跨國交流是分析新潮舊浪此起彼伏之波涌的最佳切入點。
第一,從派遣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考察、進修以及派遣留學生的情況來看,在日內瓦會議前后,中國政府便已開始設法通過出席國際會議和各國學術會議、考察訪問等方式,加強科技人員與西方國家科學家團體的接觸(20)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國科學院黨組于1953年11月19日呈送的《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其中提出要“團結科學家”。中共中央的批示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科學事業的基本政策,首次提出建設以中國科學院為中心、包括高等學校和各生產部門科學研究機構在內的全國科學研究工作體系的方針。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在科技方針政策方面的奠基性文件。在1954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五周年的慶祝活動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英國、日本在內的多國科學、文化代表團訪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物理學家J.D.貝爾納還在訪華期間受邀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作了一系列專題報告。1955年12月初,中國科學院1955年抗生素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蘇聯、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蒙古、越南、日本、緬甸、印度尼西亞、朝鮮、丹麥等11個國家的12名科學家應邀到會。這是中國科學院首次廣泛邀請國外科學家參加在中國舉辦的學術會議。參見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41、60—61頁;葉逸征:《各國科學家來我國作友誼的訪問》,《科學通報》1954年第11期。。以中國科學院為例,按照出席各國學術會議、考察訪問兩種形式統計,1955年至1957年,與中科院開展雙邊科學技術交流最多的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占比達93%;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分別為印度(3批次)、巴基斯坦(2批次)、日本(2批次)、法國(1批次)。與之相比,中科院派遣科學家出席國際會議的批次盡管很少,但增速很快,其中1956年更是多達16批;目的地方面,近90%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4批次)、比利時(4批次)、法國(3批次)、荷蘭(2批次)、瑞典(2批次)、芬蘭(2批次)、意大利(2批次)、英國(1批次)、西班牙(1批次)、瑞士(1批次)、加拿大(1批次)、愛爾蘭(1批次)、奧地利(1批次)、葡萄牙(1批次)。

表1 中國科學院派遣科學家代表(團)出國情況統計(單位:批次)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內部印行,1956年,第212—213頁;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年)》,內部印行,1957年,第312—317頁;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內部印行,1958年,第392—396頁。
中國科學家赴西方國家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是打破封鎖和突破孤立的重要方式。然而,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為在國際社會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既成事實,竭力支持臺灣方面更多參與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和學術會議。為了打破美國的圖謀,大陸科學家不得不拒絕參加有臺灣學者出席的國際會議。(21)參見張九辰、王作躍:《首次國際地球物理年與一個中國的原則》,《科學文化評論》2009年第6期。例如1955年8月,第一屆和平利用原子能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由于美、英兩國政府不承認所謂非聯合國成員國的“分裂國家”,并堅持邀請臺灣與會,大陸科學家最終未能參加這次會議(22)參見涂長望:《關于日內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國際會議的報告》,《科學通報》1955年第12期。。不過,對于以科學家個人而非國家行為體參加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科學家不但能夠積極參與,而且在會上還敢于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科學家接觸。1955年八九月間,41個國家、600多位科學家參加的國際天文協會第九屆大會在都柏林舉行,三位中國科學家出席會議。回國后,中科院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科學通報》(23)《科學通報》是中科院編譯局主辦的綜合性刊物,1950年5月15日創刊,主要報道與介紹中央人民政府的科技政策、中科院內外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的工作概況、生產技術部門的活動、國際重要學術動態、國內外科學的發現與發明,以及學術論著受到的評價等。參見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第12、30—31頁。刊登了天文學家、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參加此次國際會議的報告。張鈺哲稱,他們的學術報告及閉幕聚餐會上的發言獲得了與會科學家代表的積極回應。“席散出場時還有些人特地走來同我們握手。有幾個和我們同住一個旅館的美國天文學家,平日同車赴會彼此并不交談,可是這天席散歸來,其中有兩人自動地來向我們致意。其中有一位是美國天文通俗期刊《天與遠鏡》的主編人,他表示歡迎我們寫關于中國古代天文的稿件寄到他的期刊里發表。”(24)張鈺哲:《參加國際天文協會都柏林大會報告》,《科學通報》1955年第12期。這篇報告能夠公開發表,表現出期刊編輯者對于報道與美國科學家接觸的坦然之態,以及萬隆會議之后中國對美政策的靈活之姿。
在“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下,1956年4月1日至4日,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第十六屆執行理事會及世界科協成立十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來自除美國之外的17個會員國的1400多位科學工作者齊聚北京。大會討論了促進各國科學界相互接觸、促進國際科技合作、擴大世界科學影響等問題,各國科學家還參觀了中國有關科學研究單位和大學。(25)趙宗:《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舉行第十六屆執行理事會和成立十周年紀念會》,《科學通報》1956年第5期。
此后,中國科學家更加積極地通過多種途徑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家的接觸。《科學通報》不但陸續刊登有關中國科學家赴國外參加學術會議并且與西方國家科學家接觸、交流的報道,而且其行文無不秉持科學國際主義的精神。1956年5月23日至31日,蘇聯科學院物理數學部和莫斯科大學聯合召開的磁現象物理學會議在莫斯科舉行,約30位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出席會議。在發表于《科學通報》的參會報告中,金屬物理學家葛庭燧特意詳細介紹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奇普(A.F.Kip)報告的內容,并寫道:“各國的科學家們進行了友好的和密切的接觸,增進了彼此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在會議期中,中國代表團……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26)葛庭燧:《參加蘇聯磁現象物理學會議報告》,《科學通報》1956年第12期。
三個月后,國際土壤學會第六屆會議在法國巴黎召開,52個國家的700多名代表出席會議,中國派出了由全國甚至世界知名的土壤學家馬溶之、侯光炯、黃瑞采、侯學煜、陳華葵、朱克貴六人組成的代表團。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參加土壤學類國際會議。六位科學家共同署名的會議報道對于國際土壤學界的新進展毫不吝惜溢美之詞。他們寫道:“通過這次會議,我們認為土壤科學在最近20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比新中國土壤科學事業,報道在肯定“有了很大發展”的基礎上,還大膽指出,我們在許多方面存在著“缺門和薄弱環節”,還有空白點。(27)馬溶之等:《國際土壤學會第六屆會議概況及學術活動》,《科學通報》1957年第2期。
與此同時,從1956年8月20日至9月15日,三位中國地球物理學家——陳宗器、呂保維、朱崗崑先后參加了國際地球物理年特別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歐區域會議、國際科學無線電協會國際地球物理年委員會在布魯塞爾召開的電離層會議、國際地球物理年特別委員會在巴塞羅那召開的第四屆大會等三個國際會議(28)這三次會議是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2月底為期18個月的國際地球物理年系列活動的組成部分。中國政府決定參加此次活動后,由于美國領導的組委會允許臺灣參加,中國最終退出了后續的科學活動。參見朱崗崑:《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會議記要》,《科學通報》1956年第12期;張九辰、王作躍:《首次國際地球物理年與一個中國的原則》,《科學文化評論》2009年第6期;Zuoyue Wang,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State-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Vol.30, No.1, 1999。。其中后兩個會議均有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等西方科學家參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屆國際地球物理年大會,這是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國際地球物理年大會。(29)朱崗崑:《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會議記要》,《科學通報》1956年第12期。
在被美國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包圍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家的出訪是“人民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體現出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1957年,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被周恩來選派作為唯一一位中國科學家赴加拿大參加首屆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便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周培源在帕格沃什大會上表示:“中國科學家急需與世界各國科學家合作。”“我們熱烈歡迎與國外科學家的合作。”孰料美國科學家外斯科夫(Victor Weisskopf)當場表示希望訪華。周培源馬上說:“我答應你,我不僅歡迎你,也歡迎其他各國科學家們訪問新中國。”在1959年第四屆帕格沃什會議上,周培源在題為《中國科學技術的國際合作和發展》的發言中,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十年來,蘇聯、東歐及西方國家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工作、中國派出留學生和技術人員到國外學習的情況,并表示:“我相信國際合作是促進相互理解,消除偏見,從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之路。”借出訪北美的機會,他還設法與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恢復聯系,“為中美關系解凍后,美籍華人科學家立即組團訪華奠定了基礎”。(30)周如玲:《周培源和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科學文化評論》2005年第6期。
第二,從在華外國專家的構成上看,蘇聯作為新中國國家建設起步階段主要師法的對象,在20世紀50年代無疑是中國引進先進智力的主要來源。至“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中國共聘請了來自70余個國家的1.5萬余名外國專家(不包括專家的家屬)。其中1949年至1960年6月,共聘請蘇聯專家12155人,數量居首;聘請民主德國專家821人,位居其次。不過,隨著中蘇關系交惡,至“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在華外國專家的構成發生了迅速、劇烈的變化:一方面,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人數驟減。1960年末,蘇聯在華專家僅剩418人。1961年至1962年,社會主義國家在華專家人數繼續銳減至僅有8人。另一方面,常常被研究者忽視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在華專家的人數和比重從1961年起逐漸增加。至1966年6月,日本專家人數居在華外國專家之首,為222人;法國專家數量位居其次,為105人。(31)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編寫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第3卷(1962—1967),內部印行,1994年,第135、42頁。外國專家構成的變化,體現出中國科學技術的外部知識來源的微妙轉向: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逐漸取代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表2 在華外國專家人數統計(單位:人)
資料來源: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編寫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第2卷(1957—1961),內部印行,1994年,第205頁;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編寫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大事記》第3卷(1962—1967),內部印行,1994年,第14、32、67、72、98頁。
除了派遣中國學者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公開報道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的交流情況,以及邀請西方國家專家來華之外,1956年、1965年,國務院先后兩次批準外交部、高教部的請示報告,分別同意在1957年向西方派遣少數語言類留學生,在1965年向不包括美國在內的法國、英國、瑞典、丹麥、荷蘭、瑞士、挪威、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國家派遣自然科學留學生(32)參見胡中波:《中美關系視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第108頁。。在國際冷戰的大背景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科技合作與交流盡管仍然受到美國在政治上與外交上的封鎖和孤立,但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外時局抱持樂觀態度。在中央政策的鼓勵下,中國科技人員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科技人員的交流得以恢復和維系。
三、科技文獻的跨國流動
從引進、翻譯外國科技文獻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盡管沒有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直接開展科學技術合作的國內政治條件和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一些文獻情報機構還是設法訂購到大量西方科技與工農業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圖書報刊資料。以中國科學院為例,中國科學院圖書管理處(1951年2月改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在1950年4月成立后,便開始注重購買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書刊。不過,由于內部要對進口書目嚴格審批,外部又受到封鎖,1951年國家只撥給外匯12.5萬英鎊,便已綽綽有余(33)原文為35萬美元,按當時的匯率折合為12.5萬英鎊。參見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77頁。。1956年“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提出后,為了廣辟書源和改變訂購不及時的情況,國務院批準中科院圖書館直接從國外訂書,并且在莫斯科、柏林、倫敦等地設立采購點(34)白國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工作50年(續)》,《圖書館》1999年第4期。。從當年起,中科院為購買資本主義國家書刊所支出的外匯猛增,1956年為180萬英鎊,1957年略有縮減但仍達到150萬英鎊。據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介紹,“這個數字,比日本、印度、蘇聯進口的數字都大”(35)《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 郭沫若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7月6日;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內部印行,1958年,第2、16頁。按:武衡使用美元記錄,數據稍有差異。參見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第277頁。。從1958年到1962年,為了加強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宣傳,當時中國負責進出口外國書刊的獨家經營單位——國際書店集中全力對外出口,以至進口圖書數量下降。1963年外文書店正式成立,成為圖書進口和發行的專業書店,國際書店則改為專業出口書店。至1966年,中國購買資本主義國家圖書報刊的外匯總額恢復到近107萬英鎊(36)原文為300萬美元,按當時的匯率折合為107萬英鎊。參見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第277—279頁。。
也是從1956年開始,科技文獻的收集與編譯工作得以制度化并迅速發展。是年初中共中央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后,中科院副院長張稼夫和武衡在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談及中科院對國際科學技術進展了解太少,且只注意向蘇聯學習,很少顧及其他國家。周恩來當即指示,要盡快建立科技文獻機構。隨后,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為了“進一步密切國際間科學研究工作的聯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換國內外科學和技術的資料”,要將中國科學技術文獻工作提高到戰略的地位上來。(37)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第288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科學院在1956年10月15日成立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由中科院編譯出版委員會指導,負責搜集、整理和報道國內外特別是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發展情況與最新成就(38)參見白國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工作50年》,《圖書館》1999年第3期;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第276—279頁。。1958年5月,國務院將國家技術委員會的情報組并入該所,使該所進一步擴大并加強,名稱亦改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并附設科學技術資料館。這使其成為全國科學技術文獻事業的中心。該所同時接受國家技術委員會與中國科學院的領導。科學技術文獻工作的任務是報道“科學技術領域內國內外的成就和動向”。當時認為,這項工作對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有著重要意義;科學技術部門開展的工業和農業技術改造,是中國在十年內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工農業產品產量在15年內趕超英國的“基礎”。(39)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編:《科學情報工作(1958年文獻匯編)》,內部印行,1959年,第1、3頁。
隨著“大躍進”的開展,“技術革命”運動很快呈現“排山倒海、一日千里”之勢,科學技術文獻工作成為“黨領導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個工具”。不過,在通過群眾運動轟轟烈烈開展的,面向生產、“解決具體技術問題”的科技文獻收集與編譯工作之外,科技文獻工作基本上堅持了“中外并舉”的原則,即“既要抓緊國內土辦法創造發明的搜集整理與傳播,也要重視國外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成就”。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分別評述各產業、各學科的國內國際水平與發展趨向”的戰略性文獻工作以及一般國外科技文獻搜集工作,一直由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及中央各專業情報機構承擔,(40)《科學情報工作(1958年文獻匯編)》,第6、8、24、11、12頁。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短暫的停滯。
國外科學技術文獻的搜集渠道有購買和交換兩種。“為了擴大我國科學界和世界各國科學界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我國科學的發展”,1956年9月25日,中國科學院第二十五次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關于科學著作國際交換的幾項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按照《規定》,中科院“可以向一切國家的圖書館、學術機關或科學家個人進行交換或贈送”國內公開發行的學術性書刊著作,不過“對聯合國、聯合國專門機構或其他中國代表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政府性國際組織,不主動提出交換;如在交換科學著作的同時,涉及對上述國際組織承擔義務的問題,則另行處理”。《規定》還一改此前由中科院圖書館統一辦理與外國交換文獻的方式,提出“今后除由院圖書館與外國圖書館及其他學術機關進行交換外,各學會及本院各研究機構均可與一切國家的研究機關進行上項書刊的交換或贈送”,并且“鼓勵研究人員同外國科學家建立學術上的廣泛聯系,如交換個人的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科學著作等,應給予各種便利,不應加以限制。尚未在國內公開發表的科學著作在不違反國家保密的原則下,亦可向國外寄送”。(41)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年)》,內部印行,1957年,第251頁。至1958年,中科院科學情報研究所除了同蘇聯全蘇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和其他兄弟國家的相應機構簽訂科技文獻交換合作協定外,還同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聯邦德國、日本、法國、瑞士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3767個學術團體和科學研究機構建立聯系,其中建立文獻交換關系的有200多個(42)《科學情報工作(1958年文獻匯編)》,第21頁。。
從1956年至1957年中科院與外國交換書刊、資料、論文數量的統計來看,同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換相比,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換盡管數量不多,但增長率較高。與此種狀況相類似,這一時期中科院出版的譯著盡管以社會主義國家的著作為主,但資本主義國家的著作數量增速更快,其中美國書籍占所出版的資本主義國家譯著的比重逐漸增大。

表3 中國科學院與外國交換書籍、期刊數量統計(單位:冊/件/篇)
注:表格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朝鮮、蒙古、越南、民主德國、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英國、法國、瑞典、聯邦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美國、瑞士、丹麥、芬蘭、荷蘭、挪威、奧地利、冰島、葡萄牙、以色列、西班牙、比利時、加拿大、新西蘭。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227—231頁;《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年)》,第351—353頁;《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第423—426頁。

表4 中國科學院出版譯著數量統計(單位:冊)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第238—246頁;《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年)》,第361—366頁;《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第437—446頁。
利用交換、購買的外文資料來編寫科學新聞、專業科技動態、專業快報、文摘、索引、述評、譯文集等,成為科研人員及科技文獻機構的重要職責。為了打破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充分利用通過各種途徑取得的外國期刊、文獻資料,中國國外科技文獻編譯委員會于1961年10月成立。至1962年,該委員會共主持出版整本翻譯外文期刊30種、選譯期刊120種,翻譯科技文獻2萬余篇、外國專利文獻4萬余篇,共約3億字。此外,在全國范圍內人數達2萬余名的業余翻譯隊伍也被組織了起來。(43)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第293頁。以中科院系統為例,院出版委員會及各類專業學會編輯出版的綜合類科技期刊和專業性學報,不定期刊登科技人員譯介外國先進科學技術設備的文章(44)例如,有專門介紹美國氣冷反應堆原子能動力設備的文章。參見武霈:《美國氣冷反應堆原子能動力設備的發展》,《科學通報》1957年第3期。。院圖書館、科學情報研究所以及各專業性學會還編輯了《科學新聞》《世界科學》等大量有關外國科技進展的綜合類期刊,以及20余種專業性科技譯介類報刊,如《科學文摘》《期刊論文索引》《譯報》等(45)參見《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年)》,第434—436頁;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編:《我國科技信息事業的改革與創新:慶祝中國科技信息事業創建45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石化出版社,2001年,第33—34頁。。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遇到困難。依據中央方針,科技文獻工作也在體制、人員、業務等方面作出調整,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被劃歸國家科委管理。總的來看,在“文化大革命”前,各部門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文獻工作者多方設法打破國際冷戰時代西方對中國的信息封鎖,為中國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電子技術、自動化技術等,以及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高新技術重大工程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46)白國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工作50年》,《圖書館》1999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5年起,中國與美國互寄科技類書刊、資料、論文,開啟了兩國在國際冷戰時代學術資料的交流(47)參見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內部印行,1956年,第229、231頁。。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編寫資本主義國家情報工作情況介紹時,專門詳細介紹了美國的科學情報工作(48)參見《科學情報工作(1958年文獻匯編)》,第135—138、162—168頁。。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49)《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頁。成為中國選擇性學習與借鑒的目標,諸如《美國的農業》(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編,1962—1963年),《美國汽車業托拉斯》《美國國際收割機公司的經營管理》《美國西屋電器制造公司的組織管理情況》《福特汽車公司的發展和現狀》(國家經委企業局編,1964年),《美國原子能在農作物和植物科學研究中的利用》(中國農科院科學情報資料室編,1963年),《美國農業科學研究機構經費及人員》《美國灌區鹽堿化概況》(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編,1963年)等大量介紹美國技術管理等方面經驗的材料,被當作內部資料在科研單位和科技管理部門刊行。
由上述科技人員交流、科技文獻譯介的情況來看,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特別是從1956年開始,中國“向外國學習”的對象逐漸有選擇地從蘇聯轉向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更多國家,甚至美國也隱約成為被關注的目標。“和平外交”為這一時期的中外科技交流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從1956年到1958年,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建立起強有力的科學技術文獻體系,一個重要的條件是“隨著我國外交、外貿、僑務、對外科學技術交流與文化交流的發展,可以直接從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情報與資料”(50)《科學情報工作(1958年文獻匯編)》,第1頁。。
四、余 論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領導人在建設思想上由“以蘇為師”向“以蘇為鑒”,甚至“以蘇為敵”的轉變悄然發生(51)王海光:《〈論十大關系〉文本的形成與演變及其經典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上擁有長處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可師法的“外國”,漸入中國領導人的視域。從各類外國專家的引進,科技人員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短期訪問、培訓、留學等多種方式開展的互動交流,以及通過國際互換與購買的科技文獻跨國流動來看,在“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之下,中國在科技領域學習的對象逐漸從蘇聯轉向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只是從“向蘇聯學習”轉向“向外國學習”,其間風雨不寧,路途坎坷。
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造成的“紅色恐慌”余波未平,全面對華遏制與孤立的政策仍被艾森豪威爾政府奉為圭臬,其他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科技交往也受到嚴重掣肘。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科學國際主義精神(堅信中國不應與國際科學界和學術界隔絕,科學家之間的跨國交流能減少緊張、促進和平)的推動下(52)其他重要動因還包括相關美國科學家和學者反戰思想、左派思想、和平思想等政治關切,以及他們對于中國的好奇,對于中國在農業、中醫、植物學、地震學、考古學、氣象學等專業領域成就的極大的專業興趣。參見斯蒂芬·麥金農著,儲峰、陳剛譯:《1972年4月的一個凌晨與周恩來總理談話的回憶》,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6),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368頁;Kath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866, No.1, 1998。,美國科學家、人文社會學者集團體之力,成立了多個促進對華科學、文化、教育交流的組織。然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得中美雙邊科技交流的前景變得晦暗不明,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科技交流也被迫中斷。隨著中美關系解凍,從1971年開始,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家、學者的到訪不僅有了零的突破,而且日益頻繁起來(53)典型事件是1971年5月,兩位美國科學家——耶魯大學植物學家高爾斯頓(Arthur Galston)、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西格納(Ethan Signer)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訪華。參見黃仁國:《政治、經濟與教育的三向互動——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博士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10年,第71—76頁。。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中國走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國家歷史任務的重心和實現手段均發生轉變:由通過軍事對抗和意識形態斗爭來實現并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完整,轉到通過集中力量推動現代化、增強國家實力來實現民族復興。科學技術現代化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而作為西方最先進科學技術代表的美國,被中國領導人視作獲得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來源(54)張靜:《鄧小平與中美科技合作的開展(1977—1979年)》,《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美國的先進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向中國科技知識人員號召“刻苦學習”的對象(55)1978年12月26日,在新中國首批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出發前,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意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第二天,《人民日報》編發的新聞標題是《我國首批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離京 方毅副總理勉勵他們刻苦學習美國的先進科學技術,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出力》。。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后,鄧小平在答美國記者問時明確表示,自己即將開始的美國之行,“目的是要了解美國,向美國的一切先進東西學習”(56)《鄧副總理會見美國記者》,《人民日報》1979年1月6日。。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的20余年間,盡管中國領導人“向外國學習”號召之所指隨著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改變,但其內涵的共通之處卻未曾改變,那就是要在堅持兩點論的基礎上,向世界上一切國家和民族學習,永遠不要“翹尾巴”。為了中國的富強,“一萬年都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