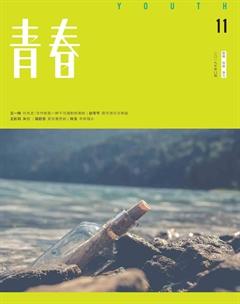市井煙火
陳戈
理發店的經濟達人
每回林師傅說起自己赴老家買房的過程,神情里多多少少有顯擺的滋味。他額頭泛著油光,眉飛色舞,得意洋洋,溢于言表且毫不掩飾。而只要林師傅開了話頭,旁邊給女顧客做頭發的老婆,便會用夾生的無錫話說道:“好咧呀,就那點家底,都讓外人曉得了。”
“我這是靠腦筋活絡,正當的收益,誰怕誰呦。”林師傅手起刀落,手上拿捏的分寸一絲不差,電推子咔嚓幾下,一個神清氣爽的腦袋就顯露出來。
坐在椅子上等待剃頭的顧客都笑而不語,他們都是常客,聽慣了林師傅買房的經歷,見怪不怪。等上位顧客付錢走人,馬上一個頭發亂糟槽的腦袋又盤攏在林師傅的剃刀下。
林師傅早年并不會剃頭,他原先是蘇北鹽城老家一家國營老廠的職工,娶了青梅竹馬,會弄頭發的老婆。老婆有手藝,就開了家美發店,生意還行,賺點錢貼補家用。林師傅一天八個小時泡在廠子里修理機器,和美平淡的日子等到兒子出生后三年,突然揚起了波折。
國營廠經營不善,這一年宣布倒閉,每個職工發一個月工資,回家自謀出路。國營變自營,林師傅在家里心神不寧地閑了半年,終日無所事事。一天老婆回家,見家里堆滿了十幾個綠油油的西瓜,懸在心中的一口氣終于落了地。此后,林師傅白天在家買菜燒飯帶兒子,等晚上老婆回家,就用那十幾個西瓜練手,拜老婆為師,學上了剃頭手藝。
有修機器的心靈手巧托底,林師傅學起剃頭也毫不含糊,西瓜皮越剃越順溜,樂得兒子天天大快朵頤。兩個月后,林師傅第一次出現在老婆的店里,現場觀摩夫人給顧客剃頭的全過程。細心觀察一周,林師傅便躍躍欲試。
第一個顧客是個老頭,一頭花白的頭發,刺毛似的戳滿腦袋。老頭要剃個板刷,這正合乎林師傅最拿手的基本功。半個小時下來,老頭心滿意足地付了錢,林師傅雖然從汗水里爬了出來,心里卻涼爽不已,一個勁地夸老婆教得有水平,絕口不提自己的辛苦努力。
十年前,林師傅舉家來到無錫發展,還是繼續干他們的老本行——理發。
老家有一些熟人和顧客,早幾年來無錫打工,落了根,發了芽。林師傅瞅準了他們住在城鄉結合部,就在那里租了個小門面,開起了美發美容。店名依舊是老婆的名字,林師傅沒同意老婆要改店名的想法。因為老婆做頭發的手藝相當嫻熟,價格比周圍理發店便宜,那些鹽城老鄉一見老婆的店名,便有了一絲念鄉的感觸。老婆理發手藝確實高超,回頭客就認準了店名,給別人推薦也只說老婆的名字,要是改了店名,反倒會流失一些潛在的客戶。
沒多久,林師傅也開始有回頭客,而且越來越多,周圍小區居民聞名而來,一回生二回熟,生意走上了正軌。在店里,林師傅專剃男顧客,老婆做完女顧客的空隙,順便招呼男顧客,讓林師傅減輕點壓力,喘口氣。
林師傅在廠里嘴碎,喜歡議論時事,天南海北的話題常常涉獵。男顧客在等待的閑暇,林師傅嘴巴也沒閑著,不經意間就滿嘴跑馬,胡侃一通。
在話題中,林師傅最喜歡談及經濟。他常說,政治話題說起來帶勁,可常常會話不遮口,說著說著,萬一跑偏了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那就麻煩了,只好偶爾談及。但經濟話題就不一樣了,民以食為天,這食就是經濟。上菜市場買菜,菜價的起伏牽動每個家庭,還有柴米油鹽,哪樣不跟國家經濟走勢有關。
“民生問題關乎國家大事,國家制定的每一項政策,都跟我們老百姓息息相關。比如懲治貪官污吏,就應該從內部抓起。”林師傅得意起來,話題就會跑偏,旁邊老婆趕緊提醒他:“焗油膏快沒了,下午去市場進點貨。”
有段時間,報紙、網絡,還有民間小道消息,流言蜚語四處蔓延,說是一到周末,所有的房產銷售大廳,停滿蘇州牌照的小車。大批蘇州人來無錫買房,趁無錫處于房價洼地,有一層一層買的,更有整幢整幢買下,眉毛都不打皺,堪比溫州炒房團。林師傅的理發店人來人往,多是本地居民,免不了對蘇州人來無錫買房評頭論足。“這房價更是民生大問題。”林師傅聊得起勁,每天都要把這個話題,在小小理發店里炒上幾遍。
這邊林師傅的理發店熱熱鬧鬧議論著無錫的房價,那邊,無錫的房價每月登上一個新臺階。一談到房價,小區居民既有興高采烈的,也有垂頭喪氣的。臉上喜氣洋洋的,一看便知是自己居住小區的房價又上漲了,心里盤算著家庭資產又增加多少。愁眉苦臉的,嘆氣說自己兒子談了女朋友準備結婚,這下買房預算虧空不少,為此,頭發又白了幾根。
林師傅自己租房,沒有心理壓力,分析房價走勢,客觀獨到,心態倒是輕松。他調侃房子漲了的居民,房價漲跟你有啥關系,你又不能把房子賣了,賣了你能買哪里的房子,買了房子要交稅,要裝修,你家那點老底,還不折騰沒了。他又勸愁眉苦臉的,這房價只會越來越高,為啥,沒看見國家鼓勵二胎嗎,今后人口越來越多,土地越來越少,明擺著,房價怎么會降。這房子,要買就趁早買,以后還會往上漲,您信不信。
說歸說,勸歸勸,林師傅心里倒是有了自己的盤算。晚上被窩里,林師傅貼著老婆的耳根說:“你看無錫的房價一炒就炒上去了,這股上漲的風頭,是從一線城市往二線三線蔓延。我打聽了鹽城的房價,基本在四五千沒動,估計過不多久,老家的房子也會跟風漲價。”
老婆回過頭:“你是不是想回鹽城買房?你要是定了,我不反對。”老婆知道自己丈夫腦筋活絡,做什么事都是心里有了主意,才跟她商量。
“我們早晚要回老家的,買套房養養老,另外,兒子學習不怎么樣,我想讓他回鹽城發展。無錫競爭太激烈,他競爭不過人家,要吃虧,不如回老家安頓。給他買套房子,做婚房。”
“一下買兩套房,你瘋了!”
“都是貸款,付個首付就行。一套以你的名字,一套用我的,我們家存款,付兩套首付綽綽有余。房子萬一漲了,首付只夠買一套,還要多付不少房款。”
“聽你的,你定。”家里的大事,一定要男人來拿主意。男人有眼光,心胸大,做事當斷立斷,這點女人是比不了的。老婆相信林師傅的判斷,他們舉家來無錫發展,就是林師傅的主意。這幾年賺了不少錢,這一步走對了。
沒幾天,理發店貼了張告示。告示上寫著,回老家有事,停業一周,敬請諒解。一周后,理發店果然正常營業。林師傅繼續高談闊論他的經濟觀點,時不時穿插一點對時事的論調,一旁老婆還是微笑著提醒他。
半年后,老婆對待顧客的態度明顯上了一個臺階。顧客來了,笑嘻嘻相迎,不是夸人家皮膚保養得真好,白皙細嫩像小姑娘,就是贊美人家頭發柔軟靚麗,摸上去像絲綢一樣光滑。
林師傅更加健談了。只要顧客對他的話題感興趣搭上嘴,林師傅就能滔滔不絕地和顧客嘮個半天。偶爾聊起房價,便會透露一下自己回老家買房的消息,眉宇間散著一股舒順氣。待顧客問鹽城這段時間房價有沒有漲了,林師傅眉目間那股舒順氣便蹭地一下躥到額頭,锃光發亮的額頭便揚眉吐氣般照亮了小小理發店。
“哎呀,你不知道,鹽城的房價漲得太快了,半年沒到,市中心一萬五都有人搶,均價都要一萬了,買房跟買白菜一樣。”
顧客問:“林師傅你去搶了沒有?”
“我才不當那個傻瓜,去做接盤俠。半年前我就分析,老家的房子肯定要漲,我下手買了兩套,那時候只要五千多,現在郊區的都不止這價。現在再去買,房子漲得那么快,老百姓一輩子收入都要貼進房子,不合理啊。國家肯定要出調控政策,您信不信?”林師傅滿面春風,天上掉餡餅都沒讓他如此意氣奮發。
“好咧呀,就那點家底,都讓外人曉得了。”
廢墟上的縫補攤
弄堂口,車來人往。一到飯點家家戶戶都會飄來煎炒爆煮的油煙氣。家有小孩的,屁股跟猴子一樣粘不住,吃兩口飯,就找個借口溜出去,和年紀相仿的幾個在弄堂里串來串去,大呼小叫地惹大人斥喝。女孩子賢淑些,跳跳皮筋,扔扔沙包,馬尾辮跟著節奏甩來甩去,或者安靜地坐在小板凳上,趁天亮做些功課。老人則坐在竹椅上,搖著蒲扇詳和地看著人世浮華。
老人背后墻上,是一個大紅色的字,拆!殷紅殷紅的。
漸漸的,這戶人家和左右鄰居打個招呼搬走了,那戶人家在一個早晨悄然上了搬家公司的卡車。不出半年,弄堂人氣消散,只剩下殘垣斷壁,默默陪伴著陸阿姨搭在弄堂口的縫補攤。細細長長的弄堂,油煙氣清淡了許多,有路人走過,呸的一聲,往破舊瓦礫吐一口濃痰,也沒人在意他的無理。
陸阿姨坐在縫紉機后面,只管低頭做她的活,對于眼前近半年時間發生的一切,她見怪不怪。她的縫補攤支在一座老式四層樓的墻角,樓上住戶早走得一干二凈,陸阿姨就找了一戶窗戶還算完整的人家,用塑料布把窗戶縫釘死,拉來一條沒人要的沙發,中午累了,就在沙發上小憩一會。
一臺縫紉機,一臺穿線機就是陸阿姨賺錢的工具。她有一雙靈巧的手,這雙手曾經在麻紡廠的機器轟鳴聲中,不停轉動的紡錘中找出斷頭斷線,并且嫻熟地將它們捻在一起。也曾經在機械穿梭的紡機上,事無巨細地找出布匹中的瑕疵。要不是陸阿姨身體不好提前退休,她可能隨著麻紡廠搬遷、掙扎、倒閉而最終消失在社會的經濟浪潮中。
閑在家中沒事,她在弄堂口支了這個攤子貼補家用,主要為附近居民提供修補拉鏈、褲子縫邊、破洞修復等服務,沒料這攤子一擺,就擺了十五六年。她給褲子縫邊的手藝那是沒話說,針腳細密,走線筆直,一圈下來,沒有斷頭斷線。
客戶褲子拿來,陸阿姨皮尺一量,然后就問:“是一般縫邊還是留原褲的邊?”
新來的客戶不懂,陸阿姨就耐心解釋:“一般縫邊就是按您褲腿長度,裁去褲子原來的邊,我這里重新給您縫邊。留原邊就是保留褲子出廠時的褲腳邊,那樣費時,收費貴。”
“你看我應該選哪種?”
遇到客戶猶猶豫豫拿不定主意,陸阿姨就會笑著回:“您要是相信我的手藝,就一般縫邊,美觀還便宜,和原邊沒啥區別,絕對讓您滿意。”
打聽到廢墟上縫補攤的客戶,基本都是口口相傳介紹來的,對于陸阿姨的手藝沒有不信任的道理,要不,這個攤子也不會支撐到現在。客戶點頭接受陸阿姨的建議。
“好咧,您急著用這條褲子嗎?急得話,您先坐會,等個幾分鐘就好。”陸阿姨麻利地量好尺寸,粉餅沿著尺子劃出一道直直的線,大剪刀咔嚓一下,整齊剪除多余的褲腳料。踩動縫紉機,麻利的手指在褲腳那里捏、整、平、壓,穿線,挑針,斷線,一氣呵成,用時不到五分鐘。陸阿姨便把褲腳用熨斗熨平整,折疊好遞給客戶,說道:“好了,五塊。”
摸著平整細密的褲腳線,客戶滿心歡喜。這一趟沒白來,便宜又實惠。
陸阿姨身后總有一堆小山似的衣服褲子,等待著她一雙靈巧的手去撫摸它們。有做不完的活,這對陸阿姨來說,不僅沒有怨言,反倒讓她每天都充實和忙碌。從早上八點出攤,到傍晚五點收攤,中間休息一個小時,陸阿姨十幾年都這么過來了,并沒有因為這里面臨拆遷,造成來照顧她生意的客戶減少。
許多客戶是原本附近的居民。雖然拆遷搬進新房,畢竟是平常百姓,新褲子縫個邊,舊衣服補個洞,能省就省,省下錢給小孩多買點好吃的好玩的。拉鏈壞了總不見得重新買一件,拿來給陸阿姨捯飭幾下,又能穿上幾年。一只真皮名牌包,皮依舊光鮮柔軟,拉鏈耐不住折騰,扔了怪可惜。便有人打聽來陸阿姨的手藝,開著車尋攤子,鄭重其事地把包交給陸阿姨,關上車門等著。
對待這種客戶,陸阿姨臉上掛著笑:“急用嗎,急的話現在幫你弄,不過費用貴點。”
使著名牌包,哪在乎這點小錢:“阿姨,明天去喝喜酒,我那件大衣搭配這包,顯得優雅。錢是小事。”
“得咧!”手藝在心,陸阿姨不慌不忙,小心拆下原來的拉頭,從鐵皮盒里找出一粒全新的,用小尖嘴鉗三下兩下,便把新拉頭裝了上去,來回試幾下,開關自如,對著小車喊道:“好了。”
客戶鉆出小車:“多少錢?”
“五塊,另收五塊加急。”
“這么便宜?”客戶爽快付錢開車離開。陸阿姨瞧見客戶在車里和她擺手打招呼,嘴角一揚,笑著點點頭。
有一次,一男人穿著一件皮衣,急匆匆讓陸阿姨修理。陸阿姨一瞧,心里一樂。原來,男人拉拉鏈的時候急了點,鏈齒沒對準就硬拉,結果,拉頭拉到一半,下面鏈齒脫鉤,造成拉頭卡在衣服中間,上不行,下不得。這下可好,皮衣脫不下來,穿著出去不倫不類,好在男人的婆娘還記得陸阿姨,趕緊讓他來找陸阿姨幫助。
男人急得滿頭是汗,陸阿姨安慰他:“別急,小事情啦,很快的。”陸阿姨讓男人抬頭挺胸,拿出小尖嘴鉗,給拉鏈加點潤滑油,慢慢把拉頭往上挪,待拉頭到了最上端,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法,陸阿姨輕輕一拉,拉頭便脫出鏈軌。接著,陸阿姨順著鏈軌一邊,把拉頭從上端一直放到底端,拉鏈恢復原樣。
“呼!”男人低下頭,憋在胸口的氣終于徹底釋放了出來,連聲道謝,拿出皮夾子問道:“多少錢?”
陸阿姨擺擺手:“這點小事,幾秒鐘的事,不要錢。”
從此以后,男人家里所有需要縫補的衣褲,都拿來給陸阿姨處理。
陸阿姨一雙憂郁的眼神,時常蒙著一層朦朦朧朧的水霧,盯著四周殘垣斷瓦出神。她擔心,一旦拆遷工作完畢,這里將會變成大工地,到時候,她賴以生存的攤子,就沒有立足之地了。她拿到的拆遷安置房正在裝修,年前就能搬進新家,只是,安置房遠離市中心,也不可能讓她隨便在小區里支個攤子,繼續她的縫補手藝。要是在外面租個店面,店面租金就占了大頭,要保證正常開銷,免不了漲價。再說,那些老客戶要是來這里遍尋不著,肯定失望而歸,失去他們,就等于失去一大塊收入。女兒正上著大學,自己身體不好,丈夫做著保安收入不高,收入減少意味著日子又要過得緊巴巴了。
周圍有幾戶人家,拆遷款沒談攏,賴著沒搬,留下老人看守老房子。老人寂寞,常常聚攏在陸阿姨的攤子周圍,曬曬太陽,拉拉家常。有時,也開導開導陸阿姨。
“樓房住著就是比棚戶區舒服寬敞。”
“就是嘍,琴芬,你擔心什么,那邊安置房住著幾千戶人家,到時候,就怕你嫌手腳不夠來不及做。”
“你那手藝,到哪都不愁呢。”
聽多了,陸阿姨的心結漸漸化開,匯成一股暖流,在冬日的陽光下,像那寒冰融化成清冽的水珠,一滴一滴滴在心頭,讓陸阿姨感覺到春天已經在呼喚她。
她雙腳用力,踩動縫紉機的踏板。針頭牽著一根細線,飛快地在褲腳織出一道漂亮的邊。縫紉機隨著陸阿姨踩動的節奏,發出歡快的轟鳴,在冬日弄堂蕭條的廢墟上,回響著。
虞美人的土雞
走過賣魚幾個潮濕的攤子,一排四開間,攤販賣土雞的吆喝聲,便撲面而來。
“正宗蘇北土雞呦,便宜又好吃。”
“您看這河北散養雞,您瞧瞧老母雞的油,又黃又肥,煲湯特別養生。”
“老母雞要伐,20塊1斤,價格公道,童叟無欺嘍!”
眼角滑過前面3個攤販,走到第4家跟前,嘿,眼前突然一亮。只見那女攤販正閉著眼,戴著耳機,雙臂做出各種伸展姿勢。她跟前雞籠上支著一臺蘋果ipad,耳機線連著機器,屏幕上播放著跳舞的視頻,她也跟著扭動胯部,一副陶醉其中的模樣。女攤販一頭卷曲短發,姣好的瓜子臉,皮膚白皙,勻稱豐滿的身體,散發著女人成熟的味道。你會驚嘆,無論從穿著、模樣、氣質、表情甚至是氣場,她跟其他賣雞的攤販,包括整個菜市場的小攤小販們,應該是活在兩個不同世界中的人,卻被生計被生存殘忍地捏合在了一起。即使如此,她也是鶴立雞群,能讓任何人看一眼,便記住了她。此后,一進入菜場,就想起有這么一位活色生香,跳著廣場舞,與眾不同的,賣土雞的女人。
待到她睜開雙眼,你又不由得贊嘆造物主造化弄人。那是雙黑暗中閃爍著明亮星星的雙眸,黑漆如電,顧盼之間,清泉一般涌動,讓你剎那間忘記,這是在臭水橫流,雞屎熏天的菜市場。她對著你凝視,你便如浴春風,溫暖舒心。她雙眸滿含笑意,你便融化心中最后一絲猶豫,打定主意就在她這里買只老母雞回去。
她輕啟朱唇,柔聲問道:“先生,您是要老母雞還是小公雞?是紅燒還是清蒸?老母雞補身,小公雞補氣,你來多大的?”
你內心忐忑:“要只老母雞。”
“老母雞煲湯最合適,小孩子吃了補身,老人吃了健體。雞油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來只大的,雞油要黃,要多,殺好后替我去掉雞頭雞屁股。”
“好咧,先生您稍等哦。”
你目不轉睛,看著她麻利地稱好份量,扭轉雞頭,一刀飛快下去,雞喉嚨噴出一線熱血。老母雞蹬兩下腿,便安靜下來。旁邊一只大桶里,開水升騰著水汽。她拎著雞腿在開水中浸沒幾下,雞全身濕漉漉冒著熱氣扔在砧板上,戴著塑膠手套迅速在雞身上撕扯劃拉,轉瞬間,一只溜光嫩滑的老母雞赤條條呈現在你的眼中。接著開膛破肚,拉出各種內臟,把雞胗、雞腸、雞肝、雞心處理好塞進肚子,剪去雞頭、雞屁股,放入塑料口袋遞給你。你一手交錢一手取回口袋,心里卻恨不得她殺雞的手腳遲緩點,亦或讓光陰體諒你的心情,放慢它消逝的腳步。
殺雞當間,她手中剪刀上下翻飛,一口細軟吳語卻娓娓動聽。
“常吃我的雞呀,還能健腦呢。有個常客,他家兒子去年高考,幾乎每個禮拜到我這里來買老母雞燉湯,這不,考上了名牌大學,高興的呀,買了兩只雞犒勞一家人。”
“還有呀,有位老伯,原本走路都顫顫巍巍,一搖二晃的,自從用我的雞煨了雞湯喝,再加點黨參,當歸補氣,喝了沒出半年,自個一大早就出去溜小鳥了。哎,告訴你啊,那煨雞的方子還是我告訴人家的。”
“我進的土雞,都是山里人家散養的,從來就只吃蟲子長大,不吃那些亂七八糟的工業飼料。先生,您今天回家吃過嘗過,一吃就清楚,味道絕對跟別人家是兩樣的。”
你心里明白,那是她在給自家的土雞做廣告。但那聲音就是潤物細無聲般地鉆進心里,軟軟的,沙沙的春風吹拂一般,很是受用。
旁邊一臉橫肉的大媽級攤販看著眼熱,冷不丁插來一句:“虞美人,瞧你那股騷勁,你老公知道了肯定給你臉色看。”
哦,這虞美人還真配得上她。
從此,你心里便刻上虞美人三個字。每次去菜場或者路過菜場,虞美人就從心里浮現出來,還有她身后一籠一籠的土雞。那雙晶亮的雙眸,會肆無忌憚地穿越空間距離的約束,伴隨著你的背影,直到你轉過街角,還依依不舍地望著你。
和磨刀石廝磨一輩子的石師傅
石師傅活動范圍只限在無錫西面,沿著梁溪河往西,一直延續到榮毅仁的梅園附近。
從地圖上看,也就巴掌大小,不過,當你用雙腳去丈量這塊巴掌大的土地,就會發現,無錫西邊這塊土地,人文薈萃,地杰人靈,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而且,梁溪河一頭通衢古老的京杭大運河,另外一頭,連接浩瀚閆淼的太湖,是宜居宜住的風水寶地。無錫古有別名梁溪,自古梁溪河是無錫人的母親河。難怪石師傅會選擇在這里做他的磨刀生意,住在梁溪河兩側的居民,不下幾十萬人口,這里面蘊藏著多少把需要打磨的切菜刀啊。
石師傅心里這筆賬還是拎得清的。
石師傅的老爸,老石同志,并不想讓兒子繼承他的手藝。老石同志繼承了他的父親,也就是石師傅爺爺的手藝,那是子承父業,天經地義的事,但這并不妨礙老石對磨刀這個行當鄙夷的想法。年輕時挑著擔子走街串巷,憑著一股子牛犢勁,一天下來沒覺得累,等年紀一上來,各種腰酸背痛就找上門。特別是膝蓋,長年累月的行走江湖,風里來雨里去,膝蓋骨加劇磨損,一到陰天雨季,如有根刺長在骨頭縫里,戳得他睡覺都不安穩。
這還在其次。磨刀這個職業,從古至今,都是一大早出門,城東轉到城西,城北行至城南,主動上門尋找生意。一張臉,日曬雨淋,沒幾天就被風刮成關公。肩膀上挑著全部的磨刀行頭,幾十年如一日壓著肩頭,瞧瞧鏡子里的自己,亂糟糟的頭發,躬著背,黑著臉,又矮又挫,姑娘見了唯恐躲之不及。要不是媒婆費盡心思,踏破鐵鞋給老石挑了個深山野溝,不懂世面的婆娘,石師傅現在在哪里晃悠,真不好說。
老石的擔心和鄙夷并沒有阻止石師傅繼承磨刀的手藝。打小,小石就喜歡跟著父親走街串巷,看父親給別人磨刀。看著一把把磨得锃亮鋒利的刀交到顧客手里,小石比老石同志還高興。
兒大不由娘,小石長大了,老石更管不了他。小石的脾氣跟他的姓一樣,又臭又硬。他就是喜歡磨刀手藝,一根筋地要傳承磨刀行業的優良傳統。和老石吵過幾次,抗爭過幾次,小石甚至有離家出走的跡象,這讓老石老夫妻倆心驚肉跳輾轉了幾個晚上。老石無奈,便隨兒子去,把磨刀擔子交給小石,任由他去折騰,去傳承。
春去秋來,小石挑著磨刀擔子,每天在錫城各個弄堂小區里喊著:“磨剪刀嘍!”一晃三十多年,隨著無錫城區面積擴大,小石漸漸把足跡駐留在梁溪河沿岸一帶的居民區。他的稱呼也由原來的小石變為石師傅。
“石師傅,您看一下我這把剪刀,鈍得連張紙頭都剪不動。”
“石師傅,剛買的菜刀,昨天砍肉骨頭,才幾下,刀刃就卷成這副德性。”
“石師傅,現在刀具質量太差了,才幾個月,銹成這樣,還怎么切水果。”
“石師傅……”
現如今,走街串巷會磨刀的手藝人屈指可數,用鳳毛麟角來形容都不為過。許多勤儉慣了的人家,經濟條件再怎么改善,家里的幾把刀具,總是舍不得扔。今年磨一磨,明年再磨一磨,一把刀用上十幾年是常有的。石師傅沿梁溪河轉一圈,有時個把月才輪轉一回,許多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盼著石師傅的身影。一旦石師傅出現在小區門口,很快一傳十十傳百,聚攏起一幫大姐大媽,圍著石師傅的磨刀攤子七嘴八舌。這一刻,石師傅像喝了口蜜水似得心滿意足,磨起刀來也加倍用心。
磨刀是個體力活,眼神要刁鉆,刀刃上任何細微缺口,一眼就能找出來。磨的時候,丹田聚氣,腰部卯足了勁,眼神、肩膀、手臂筆直用力,左右手指按實刀的兩邊,刀刃呈小五度角緊貼著磨刀石,奮力壓下去,只需兩三下,小缺口就能磨平。
大的缺口卷邊麻煩點。用砂輪磨平刀刃,再打磨,差不多厚薄,上磨刀石細細研磨。磨到一定程度,石師傅舉起刀具,對著陽光查看刀口,用大拇指橫對刀刃摸一下,便知刀刃鋒利幾何。
每一把刀具一上手,掂量幾下,刀具用料的好壞,金屬硬度的選材,后期的淬火處理,石師傅敲一敲刀身,再用手指感知刀背的涼度,心中對這把刀的質量七七八八便有了數目。這種本事,沒有十幾年以上的磨刀功力,是琢磨不出來的。
“我磨過的刀,比你們吃過的飯都多。”這是石師傅時常掛在嘴角的一句話,雖然夸張了點,但大家見識過石師傅的手藝,無不點頭稱是。石師傅磨刀挑的擔子,也早換成了腳踏三輪車,與時俱進嘛,磨刀師傅也需要改善工作環境。石師傅在車上備了一把巨大的遮陽傘,遇到日曬雨淋,不用再擔心會曬成黑炭,淋成落湯雞。石師傅還在三輪車上做了條廣告,印上一行字:磨刀石師傅,磨各種刀具,手藝精良,價格公道,下面是聯系電話,看來石師傅想把生意做大。
一天,一個男人拿著一把刀具來到石師傅的磨刀攤前,指著廣告上各種刀具四個字問,“我這是一把木工用的刨刀,師傅磨嗎?”
“磨!”石師傅指指廣告:“各種刀具,絕不是吹牛。”
“師傅姓石?磨刀石的石?”
“當然,如假包換。”
“姓石,又跟磨刀石打交道,有點巧。”
“您不信?我拿身份證給你瞧。”說罷,石師傅停下手中活計,擦干手,掏出身份證:“看清楚沒,我老石,坐不改姓,就姓石!”
男人呵呵一樂:“跟師傅開個玩笑,別在意。家里還有幾把刀要磨一磨,明天,明天師傅還來吧?”
“來,沒問題。”
第二天,男人抱著刀具來到小區門口,石師傅果然在。不過,石師傅三輪車上的廣告詞下面多了點內容,男人湊近一瞧,原來是石師傅的身份證復印件。彩色的,放大了,上面的石師傅還顯年輕,嘴角微揚,朝每個人笑著。當然,敏感內容被馬賽克了。
男人放下刀具,轉身笑得肚子疼:“這磨刀石師傅,真是太有意思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