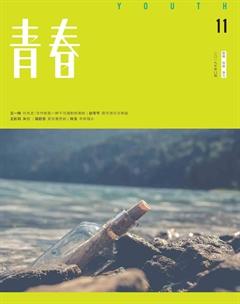院落一萬重
鄒葉
我曾在文字中,不厭其煩、一提再提居住過的院落,僅僅是因為經常思念它們。這思念和春天里其他許許多多無處安置的思念一樣,被托付給了同樣無處安置的文字。
1999年深冬,我來到人間,住進一座帶有濃濃上世紀八十年代氣息的黨校宿舍樓。除一整面年年夏日欣欣向榮的爬山虎墻外,萬物都以緩慢而必然的趨勢,走向衰敗——坑坑洼洼的水泥樓梯,花開愈疏的老梅枝,斑駁的刷有鮮紅標語的圍墻,院門口曬太陽的脫毛老狗……我懷疑大好陽光之下,那種從衰敗中升騰至每個角落的,虛幻、憂郁、坦誠老去、從容赴死的氣息,一直占據我隱秘的心靈一隅,從來無法觸及,卻長久且無聲地散出對于懷舊的執念與擅長,成為我耽于幽美的重要原因之一。
隔壁樓則是老圖書館,走到一條長滿法國梧桐的街道盡頭,穿過一潭死寂的池子,沿一段彎曲弧度詭異的石梯往上,可以窺見一屋豐富雜亂的書本,天花板極低,窗子開得極大,日光便毫不留情地登堂入室,照亮那些舊書上的霉斑。一個老頭守在那兒,與街道池子石梯舊書霉斑一起流淌出潮濕陳舊,卻叫人心安的氣場——他們彼此相識,熟悉得不再需要表面功夫。老頭嚴肅中帶點可愛,偶爾早退,正對門口的一樁大鐘早已叛變,存在的意義不再是報時,而是以美妙的“嘀嗒”聲,點綴舊光陰。
那時候幼兒園還僅僅作為父母托管孩子的場所——除了“老師好,老師再見,吃飯前洗手,午睡不尿床,排排坐,吃果果”等好習慣以外一概不認真教——于是在我那曾做過幼師的母親和寵愛有加的外婆的聯合赦免下,我三天兩頭請假,成為黨校第一大閑人和圖書館第一無知總角小兒,專門挑圖片好看的圖書亂翻,惹得看守老頭一邊呡綠茶,一邊修補破爛書封,一邊還得空出半分心思,斜睨著眼睛瞧我。
童年時外婆家的院落則煙火氣十足,左鄰右舍大到娶媳婦抱孫子慶生辰過節日,小到包餃子捏青團搖桂花摘薄荷,甚至給貓貓狗狗剃毛洗澡,都必須在公共院子中聚會一場,大家乘興而來,盡興而散,充滿玄妙的儀式感。
院落正中央有一塊青瓦圍成的黃土地,一棵香樟與三兩桂花樹下,大叢海棠花疏疏朗朗,四周空閑則被居民分成好幾份,變為私有菜地。那些退休老農民見縫插針、合理分配種菜的技術,使我懷疑他們在石頭地上也能累累碩果。
但海棠花占去的大塊沃土卻無人垂涎,任由它們閑閑地開,閑閑地落,一會兒有一會兒無地貢獻閑閑的花香。我曾問大人,怎么不把花拔了,好讓菜地直接大出一倍。他們理都不理我,繼續埋頭在細窄的土縫間,播撒青菜種子。
院子里惹人憐愛的除了海棠花姑娘,還有林家姑娘。我對她的印象停留在纖細的美麗寡婦——她的愛情病死了,隨后再嫁往北方,不復相見。夏天她常端一碗自家做的涼粉凍給我,里頭加了雙倍芝麻和冰糖。她瓷白的小臉上有一層金色細汗,隱現出潤澤的微光。
她第二次出嫁穿大紅錦繡鑲金邊百褶裙,炮竹霹靂,煙火壯麗,排場大得叫一院子人津津樂道十余載。
人去人來,海棠花依舊。外婆后來也搬走了,幾年后那兒成為辦公用地。有一回春節路過,好奇地探頭探腦,門衛大叔得知我也曾在老院子中度過童年,熱情萬分,擺出瓜子和小板凳叫我吃叫我坐,意欲大談此地的前世今生,我趕緊找借口溜走。
屬于我的最后一個院落依偎在青山腳下,春日浸潤在浩浩蕩蕩的茶香里。古老的樹木結出板栗,石榴與楊梅,繞院墻瘋長的野薔薇于某一場雨季腐爛,還有初中畢業后種下的滿院子向日葵,僅僅輝煌了一個夏天,便在九月的涼風里飛快地枯瘦下去。
那個夏天外婆還帶回來一窩鵪鶉,十來只褐色或深灰色的小小生物,從院子這頭呼啦啦擁到那頭。它們每日誕下精巧的蛋,帶著許多好看的斑點。傍晚以撿蛋為借口混跡鵪鶉群,手心毛茸茸的溫暖觸感,到如今也沒有忘記。
院落外頭總是有賣小吃、豬肉、西瓜等各種玩意的小車子經過,各自有各自獨特的吆喝。山灣人家遠遠大喊一聲,回音蕩漾,那些小販就停下,倚在車把手旁等待。我喜歡賣麻糍的小車,那個如同麻糍般溫暖厚實的女人,日復一日給我買的那份中加很多很多的冰糖黃豆粉。
最后的院落不敢多想,因為它仍然真實存在著,在這春夜深處一想,又要動幾分歸去的心思。然而渴望的不過是無意中被記憶和想象美化過的,無聲無息、亦真亦假的舊時光。最終我又能歸往何處?且不去想,就在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