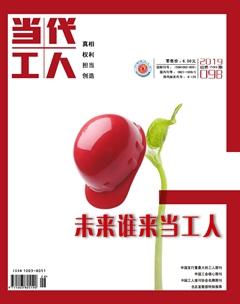有醋感90后才會浩蕩向工廠
尚尚
又到一年開學季。剛剛廝殺過高考并順利駛過獨木橋的孩子們,即將迎來美好的大學之旅。但這一切都與郭林無關,因為他再次落榜了。“難道還要再讀一個高五嗎?”郭林一家陷入愁云慘霧中,兩次高考失利讓選擇變得無比慎重起來。
“要不就去讀個高職吧,好歹有個文憑,還能學門手藝。”面對郭父的提議,郭林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畢業以后當工人?我可不去,太沒面子,我都不好意思跟同學提。”
“那你準備咋辦?沒學歷你能干什么?”郭母問。
“當網紅啊。”郭林脫口而出,“只要噱頭足夠,就會有人給我刷游艇。各位老鐵,雙擊666走起來……”
顯然,這是兩個時代的對話。郭林的父母并不理解網紅的概念,也完全不清楚何為“游艇”“老鐵”“666”,他們鬧不明白兒子為什么如此排斥工人這個職業,卻喜歡網紅。
和郭林父母一樣鬧心的還有施緯。
施緯有兩個身份。現實世界中,他是富士康的一名普通員工,在網絡世界里,他則是“富士康電子廠”賬號的主人,擁有10萬粉絲,每天固定做三次直播。
近幾年,愿意進廠操作流水線的工人越來越少,為了擴大招工,富士康開始鼓勵員工發展新員工,成功推薦一個工人獎勵1080元,如果在用人旺季,招工獎勵會升至2500元,用工急的部門甚至還會再提高獎勵金額。
看準“商機”的施緯很快在快手開設了一個賬號,工廠門口的刷臉機器、食堂飯菜、加了特效的走路帶風的漂亮廠妹、站在樓頂拍攝的人流……施緯依靠“揭秘”富士康吸引對其感興趣的潛在招工對象。通過網絡,2018年他介紹了上百人進廠。
今年施緯卻明顯感到招人形勢大不如前。“來找我的人少了一半。”施緯說,“當然,今年可能是例外。”
可這真的是一個意外嗎?今年年初有媒體報道,浙江的企業主表示,今年招工“收成”少得可不是一點兒半點兒,甚至面臨“顆粒無收”的局面。“招工太難了。”這是很多制造業老板或者招聘人的心聲。
可見,這不僅僅是富士康一家制造業公司面臨的困境。
那人都去哪兒了呢?
今年3月,光大證券宏觀發布了一份就業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17屆本科畢業生進入制造業的比重僅為19.2%,較2013屆下降了6.6個百分點;90后藍領第一份工作從事服務業的比重為30%,較80后下降了17個百分點。
如今,“成為一名技術工人”絕對不是年輕人的熱門選擇,生活服務業成為他們的新寵,進入共享汽車、快遞和外賣行業的年輕人與日俱增。2015年美團外賣騎手人數僅為1.5萬人,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躍騎手人數已接近60萬,而餓了么旗下蜂鳥騎手的注冊人數早已突破300萬。從業者的平均年齡在26歲到30歲,35歲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
為什么年輕人寧愿送外賣、做網紅,也不去工廠打工呢?
所謂上岸
施緯每天早上6點起床,先花半小時挑選素材,再剪輯成視頻,8點上班前的20分鐘、午飯后的30分鐘、下班后的一小時,準時開啟直播。
“累,太疲憊了,早上8點上班,加班到7點下班,還要繼續忙著招工。”晚上不到9點,施緯紅著眼眶打起了哈欠。可他不敢怠慢,這是他的生財之道。
第一次拿到招工獎勵時,施緯才有了“原來錢這么好賺”的暢快感,守著工資單的苦日子終于要過去了,那是扒著手指頭一點點兒摳的日子:底薪2650元,到手六七千元,扣除房租水電,再往老家寄點兒錢,能結余兩三千元,一年攢三萬元,春節回趟老家花掉一萬元,一年忙到頭剩兩萬元,10年才20萬元。
不過,這條發財路已經快行不通了。廠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進進出出的還是80后那一代打工仔,95后已經不肯進廠了,好不容易進來,被罵了幾句就會跑,“畢竟做網紅、開直播都要比做工賺錢。”施緯解釋道。
進廠已經10年的施緯其實還不到30歲,也曾想過離開,沒有采取行動是因為他把致富希望寄托在裁員上。“我們都想被裁掉,求之不得。”施緯想著,按N+1計算,以他的工齡最低也有近10萬賠償,如果只靠現在的工資,不吃不喝近兩年才能達到這個數。
施緯還在流水線里掙扎,李迪已經成功上岸,做了一名快樂的網約車司機。
李迪畢業于技師學院電焊專業,經過一個月的崗前培訓后,他正式成為一家油田注汽鍋爐設計制造企業的一名普通焊工,每天早8晚5,午休時間一個小時。作為新手,他負責焊接結構件或非主要焊縫。
“從我上班起,就沒正點兒下過班,加班到七八點是常事,周末都不得休息,還沒有加班費。人少,活兒多,沒辦法啊。”李迪如此介紹他的工廠生活,“防護服又重又熱,還必須得穿,不然非得燙傷不可。焊花哪哪都能鉆進去,有一次我鞋帶沒系好,腳上立刻燙一個大泡。”
工作強度大、環境差、危險性高……諸多因素的疊加,讓李迪打起了退堂鼓。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很快降臨。
公司規定,職工不得擅自離崗,離崗時需要將工作證換成離崗證,且離崗時間不得超過10分鐘。“我只是忘記換證了。規矩那么多,哪能一下子記得住,公司還非要罰我。”李迪略顯委屈地說。
企業一向信奉“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約束職工行為以提高生產效率的規章制度自然很多。這些都讓李迪無法適應,他只覺拘束、刻板、枯燥。
生在互聯網時代、長在移動互聯網環境的95后,更向往自由,也更鐘情于互聯網帶來的新興行業。李迪注冊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專跑機場線,每天根據平臺派單,往返于市內與機場。脫下防護服,換上體面的衣服,車內舒緩的音樂替代了工廠機器的轟鳴,曾持焊槍的手,如今正握著方向盤行駛在路上。李迪感覺很不錯,“自由度很高,不想接單就收工回家,還可以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或許網約車司機的入職門檻,進一步促成了李迪的這次職業選擇。
熱播電視劇《小歡喜》有過這樣一段劇情:黃磊飾演的爸爸中年失業,怕孩子擔心,每天依舊按時出門,在商場游蕩順便找工作。有天碰到一位外賣小哥,聊天之后發現外賣小哥的收入很不錯,“你們那招人有什么條件嗎?”正在為工作發愁的黃磊問道。對此外賣小哥只說了一句話:“長得不嚇人就行。”
成為技術工人,非“不嚇人”這么簡單。
我們就以焊工為例。上崗前,技校畢業且具備操作能力的焊工需要考取安全操作證、壓力容器許可證,兩個證都不是終身有效,需定期檢證。如果半年內沒有進行實際操作,那么證書作廢,想上崗,必須重新考。
入職后,企業會定期組織培訓,不斷提升工人技術,讓工人在實際操作中可以做到“分毫不差”,保證產品質量。“這是一個必須保持終身學習,并且難以很快出成績的過程。”中國天然氣第八建設有限公司高級技師、全國勞模、國家級焊接比賽裁判劉宇志說,“從一名普通焊工到撫順市技能競賽氣體保護焊、手工電弧焊雙料冠軍,我用了11年的時間。”
除了不斷的學習磨煉與漫長的等待,技術工人狹窄的職業發展通道,也讓一些年輕人望而卻步。
企業里,職工身份基本固化。一線工人只能按照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晉升職稱,大學生則不同,大學生入職后屬于技術人員,從事管理技術崗,按照助理工程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等晉升。普通工人即使技能水平再高,也較難成為管理層或技術人員。“以前或許還有點兒可能,因為那時候大學生少,工人可以升到管理崗。現在基本沒有了。”劉宇志如是說。
勞動明星效應
每一代人的成長似乎都伴隨著被唱衰,當年的80后如此,如今的90后、00后亦如此。
在央視《對話》節目中,董明珠在談到互聯網渠道創業時說:“90后不愿意去實體經濟里工作,在家開網店,一個月賺一兩千不用受約束,不用打考勤,這一代人對國家經濟發展是有隱患的,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沖擊是嚴重的。”
對此00后于凡表示不服,“我愿意成為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人。”
2019年3月1日晚,2018年“大國工匠年度人物”發布儀式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還在技校讀書的于凡守在電視前等待節目播出。“看新聞報道說,今年有一個90后當了大國工匠。”于凡口中的90后大國工匠名叫陳行行,他畢業于山東技師學院,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機械制造工藝研究所工人。
“陳行行,一個從微山湖畔小鄉村走出來的農家孩子,10年時間破繭成蝶,成長為數控機械加工領域的能工巧匠。”電視里陳行行手握獎杯,在舞臺上閃閃發亮。“這才叫真逼格,我被小哥哥圈粉了。”于凡興奮地說道,“看來學技術還是有前途的,工人也能很牛氣。”
同樣被感染的還有馬躍。馬躍一直對自己畢業后的佛系生活很滿意,在商場做維修電工,上一天班休一天,不但輕松還不耽誤“吃雞”、打王者榮耀。去年兒子出生使馬躍突然有了使命感,他開始利用休息日送快遞,全年無休,賺錢養家。最近則動起了去工廠上班的念頭,“因為我在華晨寶馬工作的同學,刷新了我對工人的認識。”馬躍說。
畢業那會兒,馬躍對當工人是排斥的,覺得工廠環境不好,工人看起來都是油汪汪的,不清爽。可他發現在華晨寶馬工作的同學不一樣。有干凈整潔的工裝,現代化操作車間,人性化管理,還有職工文化之旅、家庭日活動、暑期少兒足球訓練營……“他總在朋友圈曬幸福。我充當家屬參加過一次家庭日活動,參觀了華晨寶馬鐵西工廠,真的覺得特別好,想去寶馬工作。”馬躍滿眼羨慕地說。
于凡、馬躍不會是孤例。相信正有許多人同他們一樣,朝著同一個目的地,浩浩蕩蕩地走著。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