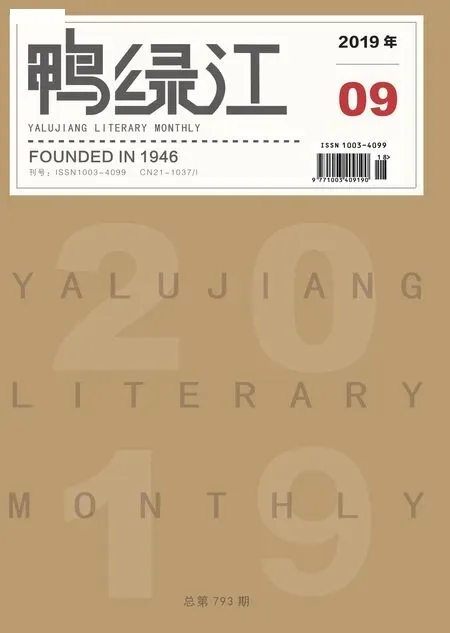如何塑造京劇《法場換子》中的徐策
蘇 超
一、《法場換子》劇目簡介
《法場換子》是京劇傳統戲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出戲,又被稱之為《換金斗》,故事出自于《薛家將反唐全傳》的第十六回。《法場換子》這部戲除了是京劇傳統戲的代表劇目外,在川劇、漢劇、河北梆子、秦腔以及徽劇等中國其他地方劇種中也有這一劇目的存在。
當年譚鑫培、賈麗川、陳彥衡、時慧寶、言菊朋、貫大元、以及富連成社的其他學員都擅長唱演此劇,而且戲路也基本一致。后來經過余叔巖對其唱腔進行了重新整理設計,最終成為了“余派”的代表劇目之一,被“余派”弟子所傳承下來。在《法場換子》的傳承上,“楊派”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楊寶森在繼承“余派”《法場換子》的同時加以創新,也成為了“楊派”代表劇目之一。故而對于《法場換子》的詮釋,“余派”和“楊派”最為經典,成為后世京劇演員及票友爭相模仿的典范。
二、劇中徐策情感分析
開場徐策的第一句念白是幕里的架子“回府”,這一句語氣一定要深切,他是帶著沉重的心情,與往日下朝大不相同。往日都是正常的“回府”叫起來也就是了,這回是朝里出了大事了,圣上要把薛家全家抄斬,徐策急速回府與夫人商量對策,他的上場,以及“回府”的架子,都是帶著沉重與憤怒的心情,所以這個上場與往日的下朝大不相同。“回”字出音要干脆利落,帶有急切的心情,“府”字揚起來念,然后再沉重的落下來。
徐策上場曲牌傳統用的是【小鑼六幺令】,穿帔上場,后來因為徐策上朝完畢以后直接回府,應改為穿蟒,改為穿蟒后再用【小鑼六幺令】就顯得輕浮了,不夠沉重,改成了感情色彩沉重的【大鑼六幺令】。大多“余派”演員演此戲時第一場都改為穿蟒,戴相貂,“楊派”還是穿帔,頭戴員外巾,盡管扮相有些許的不同,但曲牌用的都是【大鑼六幺令】。徐策下轎后,見夫人拱手見禮時,心情也是五味雜陳,一邊想著忠良薛家滿門被害,一邊想著怎么能保護薛家的后人。因此這里的見禮,也不同于一般的夫妻之間見禮。
三、劇中徐策身段分析
本劇中有兩個叫頭,一個是徐夫人的,一個是徐策的。徐夫人的叫頭要與第二場剛上場時徐策的叫頭相配合,后面徐夫人叫到“我那金!”時徐策甩髯口“噤聲!”這里鑼鼓【八大倉】,徐策托髯口攔著,落音落到“金”擋著徐夫人的口,別再往下說把“金斗”說出來,這個表演,阻擋的是徐夫人,惦記的是身后,怕夫人說漏嘴了,法場“換”子就換不了了。所以做“驚恐狀”抖髯口抖手,【撕邊】看身后,再【撕邊】看回來,雙【撕邊】的運用表達了徐策此時瞻前顧后的心情。
還有一個叫頭,第二場,徐策下場了,最后一句“待等那大炮響人頭落,再收你的尸骸”轉身,一想,還不能走。【叫頭】“薛猛,馬氏,我那金!”【八大倉】,雙【撕邊】,又是差點說漏,看一下周圍是不是沒有人聽到,確定沒人看到后兩抽泣“今生今世難得見的兒啊!”先往后退兩步,再邁著沉重的步伐下場,最后還是不忍。
《法場換子》這出戲是一出老生的唱功戲,身上身段動作并不復雜,但并不是說這出戲的身段非常簡單,幾乎所有身段都在唱念之內,所有身段動作必須隨著唱念的節奏,準確、協調、有節奏的合為一體。特別是二場的大段反調,因為節奏特別慢,如果這個動作做得不協調、準確、有節奏,動作特別多或太碎,就容易直接影響唱和表達的情感。應該把握什么原則呢?
我認為第一,不該有的身段不能亂加,多余的身段不能加;第二,一定要與唱跟念協調,不是只有唱腔有旋律性,身段一樣有旋律性,把握住一句話“唱與動的協調”,讓人看起來既協調,又有舞蹈性,這樣,表演、唱念就協調了,身段與唱配合上就有旋律性了,而且也有舞蹈性了。尤其在戲曲中,唱念舞是感情的表達,情感的抒發。加之京劇本身是集唱、念、做、舞為一身的藝術,演唱時,以身段動作來進行輔助,這是戲曲的程式化。身段動作來自生活,說話已經不能表達的足夠深切,就加以輔助與動作了,這是一種渲染。“語言不足舞蹈之”。這是老前輩給我們留下來的經驗。動作是更好地塑造人物的基礎,一定要有目的性及渲染力,當然,身段動作不是孤立的,也要有基礎,有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