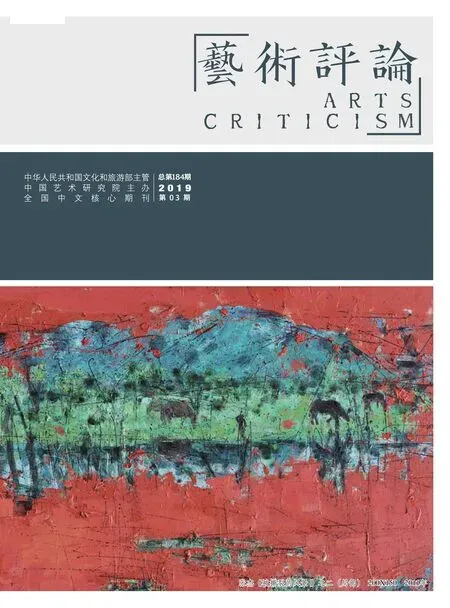說豫劇新崔派
——楊奇《新崔派藝術論——張寶英舞臺藝術論》序
廖 奔
安陽市藝術研究所楊奇先生寫了一本《新崔派藝術論》,論述豫劇名旦張寶英的舞臺藝術,邀我作序,并希望我談談對戲曲流派的見解。豫劇大師崔蘭田的崔派藝術我是熟悉的,她的女弟子張寶英在一生實踐中繼往開來、發揚光大,逐步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表演風格,楊奇稱之為“新崔派藝術”。“新崔派藝術”產生在安陽,讓我從安陽說起。
安陽是著名的七朝古都,今天以殷墟和甲骨文著稱于世,安陽殷墟遺址和中國文字博物館都是中華早期文明的象征物。但早期安陽和豫劇(河南梆子)卻一直沒有發生太多的聯系。我們知道,早年河南梆子唱腔有祥符調、豫東調、豫西調,是以黃河南岸一線的開封、商丘、洛陽為中心的。處于豫省北部的安陽卻和誰都挨不上,以往安陽是唱懷調、大平調為主的。而最早作為“豫西十八蘭”之一成名的崔蘭田,就是唱豫西調的,前半生多在洛陽、西安等地演出。但由于1951年的一個因緣際遇,崔蘭田來安陽巡演,引起轟動,隨后安陽市政府挽留住了崔蘭田。崔蘭田在安陽一扎就是五十多年,在這五十多年里,崔派藝術爐火純青。崔蘭田培養出一批徒弟,最有成就的就是張寶英。張寶英有幸成為崔蘭田的第一個徒弟,也是時代的因緣際遇。大躍進時期崔蘭田招徒,因出身貧苦收了張寶英。張寶英從此跟定崔蘭田,一跟幾十年。
張寶英早年多方打基礎,閨門旦、刀馬旦甚至彩旦都是常演的行當,國慶 30 年獻禮演出《對花槍》時她甚至扮演了帶頭盔的老旦姜桂枝。1979年香港金馬影業公司拍攝電影戲曲片《包青天》,她在競演者中脫穎而出擔綱主角秦香蓮,一炮打響,使“河南秦香蓮”飲譽了香港和東南亞,她也從此開始集中飾演青衣角色,塑造了眾多“青一色”的舞臺形象——陳三兩、竇氏、柳迎春、趙艷榮、尤二姐等,演出了《桃花庵》《賣苗郎》《秦香蓮后傳》《洪湖赤衛隊》《紅云崗》等代表性劇目,在崔派傳人中博得“第一青衣”之譽,后又在《尋兒記》里把老旦孫淑林演活了。張寶英嚴遵師訓,博采眾長,在保持崔派藝術精華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行腔特點,大膽吸收了秦腔、曲劇等姐妹劇種以及歌劇的發聲方法,形成獨特的演唱風格。她創造出的新腔真假聲運用自如,韻味濃郁、聲情并茂,既有崔派神韻,又有時代氣息。她把“塑造新人物,創立新風格,向觀眾奉獻自己的拿手好戲”作為座右銘,以在舞臺上塑造性格鮮活的人物為第一目的,幾十年來追求不息,創作了一批主題鮮明、風格獨特的代表劇目,培養了一大批追隨其演唱特色的傳人,逐漸形成一個新型的豫劇流派“新崔派”,產生極大影響。古都安陽,為孕育了豫劇新崔派藝術而驕傲。
崔派藝術的特長是哭戲,發揚光大了豫劇青衣唱腔悲戚激憤的特點。崔蘭田早年的艱難生活經歷使她同情孺弱,常常在唱腔中宣泄自己對底層民眾的一腔同情,也宣泄自己的一世悲憤。崔蘭田在舞臺上創造出一系列典型意義上的中原式悲劇,通過“以情動人”的手段把這種悲劇化入了真切感人的唱腔,感動了千千萬萬觀眾。張寶英繼承崔派藝術,首先就要在哭戲上下功夫。但她最初扮演秦香蓮時缺乏情感共鳴,導演楊蘭春諄諄啟發她:“文革”中,你是斗爭對象,愛人關進牛棚,你連孩子面都見不到。你就不想孩子?孩子就不想你?想到秦香蓮、自己以及普天下的苦命人,張寶英不禁悲從中來,感情閘門一下子打開,唱出了催人淚下的一腔幽怨和悲憤。經過長期的磨練,作為豫劇崔派藝術的優秀傳人,張寶英不但會唱、能哭,更善于融情入理、按情行腔。她的體會是:“用真摯的感情、真實的生活感受和傳統的表演手法融合在一起,才能抓住人物,通過唱把人物的心情表達出來。每用一個花腔、咬字、噴口、哭泣、換氣的部位都要考慮到人物。”能夠根據自己的條件進行繼承創新,張寶英促進了崔派藝術不斷向前發展并使其充滿活力。
我向來不認為流派僅僅體現在與大師唱腔的“相似”上,這是世俗的理解,是戲迷對大師留戀與眷顧所形成的特定社會需求,他們通過音聲甚至相貌舉止的“像”來懷念大師。雖然是人之常情,卻有害于藝術的發展。流派指價值觀、審美觀、美學風格的一致或接近,而不僅僅是指技法的相同度,如單純以后者為追求目標,就會走入死胡同。齊白石說:“學我者生,像我者死。”豫劇大師陳素真也說:“傳統的優勢恰在于她擁有不斷自我更新,可經歷百代而不衰的深根厚土和歷史淵源。”如果早期拜梅蘭芳為師的程硯秋跟著乃師亦步亦趨,何來京劇四大名旦和程派!如果早期拜過唱豫東調的陳素真為師、自己唱豫西調的崔蘭田也跟著乃師亦步亦趨,又何來豫劇五大名旦和崔派!
其實張寶英學藝崔派初期,也曾刻意模仿崔蘭田的演唱技巧和韻味,崔蘭田發現后,說出了另外的見解:“不要死板硬套地模仿我,在像不像我上瞎下功夫。你和我的嗓音條件不一樣,我是大嗓,你是小嗓,你沒那道腔。你要用我教你的方法,根據你自己的嗓音條件去演唱。怎么唱得舒服、唱得好聽悅耳,你就怎么唱。”這是大師從長期實踐中悟出來的深刻藝理。但不要徒弟像自己,而要根據先天條件去揣摩最適宜的演唱方法,怎樣體現流派呢?通過劇目和人物形象體現,通過對特定對象的獨特表現力體現,例如崔派的哭戲。大師們都有自己經受考驗和淘洗的看家劇目,并且研琢出了對這些劇目最恰當的表現方法。后學者要去精心研琢這些劇目和方法,形成自己的風格。這是對流派的最合適解釋。如果把“像不像”作為流派的首要也是必要條件,只能讓學生邯鄲學步、自我為牢,只會模仿不會創造,就壓抑了創造性。加上每個人的天然條件不同,外貌、形象、氣質、步態以及嗓寬、音高、氣息、聲量不同,個體差異會影響模仿的成色,影響學生的情緒和成績。甚至,天然條件優異的學生去孜孜模仿老師通過后天努力糾正先天不足缺陷的方法,就事倍功半、逆水行舟了。
流派亦須追蹤時代發展而變化,后來者不能只不越雷池一步地搬演前輩保留劇目,而應根據時代的需求創造自己新的作品和人物形象,有創造就會有突破。張寶英在繼承流派和不斷創新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先天條件對崔派演唱吐字、發音、行腔技巧實現了揚棄,使之既有鮮明的崔派特色,又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她因而既是崔派的忠實繼承者,又是崔派的變革發展者,實現了對崔派藝術的“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
張寶英大成了,創立了自己的“新崔派”風格,成為當代豫劇十大名旦之首、“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豫劇代表性傳承人”。我們則從中體會到了藝術傳承發展的歷史辯證法。
還在崔蘭田擔任安陽豫劇團團長的時候,團里來了一個文字秘書,他叫楊奇。楊奇長期在劇團工作,陪伴在崔蘭田和張寶英身邊,隨時留心記錄揣摩她們的劇目、唱腔、人物形象、表演藝術,幾十年不間斷地為之撰寫評介文章,把崔派藝術及其發展演變軌跡摸了個透。擔任安陽市藝術研究所所長之后,楊奇開始了對崔派藝術的系統研究,形成一部部成果。《新崔派藝術論》就是這些成果中新出的一部。這些歷史際遇,既是崔蘭田和張寶英之幸,也是楊奇之幸。我還想說,這難道不是安陽之幸、豫劇之幸?
于是我們就又有了這本談豫劇新崔派藝術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