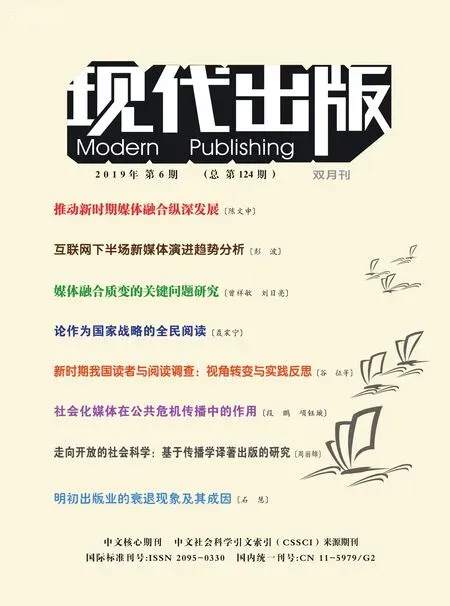推動新時期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
——基于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shè)
◎ 陳文申
當(dāng)前,我國媒體融合事業(yè)已經(jīng)到了從全面鋪開向縱深推進的關(guān)鍵時期,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的傳播環(huán)境已經(jīng)初步形成,與此同時,媒體融合發(fā)展也進入了深水區(qū),新型主流媒體打造進入攻堅期。值此關(guān)鍵之際,中國傳媒大學(xué)于2019年11月正式被批準(zhǔn)為“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建設(shè)的依托單位,既得以助業(yè)界以一臂,亦堪稱學(xué)界之首舉。在中宣部和科技部的大力推動下,學(xué)界當(dāng)響應(yīng)黨中央號召與國家戰(zhàn)略的需要,緊跟世界科技前沿,緊扣媒體融合與學(xué)科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新態(tài)勢,以中國傳媒大學(xué)國家重點實驗室為依托,開展前瞻性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以實現(xiàn)引領(lǐng)性原創(chuàng)成果的重大突破,這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與深遠影響,還是我國新聞傳播學(xué)界的緊迫課題和重大使命。本文擬簡述實驗室建立的時代意義并未來之研究方向,為我國新時期新聞傳播學(xué)研究打開新視野,引領(lǐng)新方向。
一、推進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的時代意義
如何理解媒介和傳播?人類從誕生起既要與物打交道,又要與人打交道—前者產(chǎn)生技術(shù),后者形成社會關(guān)系。一方面,人類自遠古便與技術(shù)伴生共存,沒有什么無技術(shù)的伊甸園,從發(fā)明衣服、篝火、語言、文字開始,技術(shù)就是人的外在身體,而不僅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另一方面,從原始部落到當(dāng)今社會,人在與他人的交流中產(chǎn)生和完善心智,得以成之為人;且人結(jié)群而居,彼此交互聯(lián)系而形成團體、組織、國家乃至全球世界。由此便可發(fā)現(xiàn):媒介與傳播依賴于特定物質(zhì)技術(shù),來聚集、轉(zhuǎn)換和生成各種關(guān)系,從而能夠塑造人類的社會形態(tài)。伊尼斯用媒介的透鏡來探視世界文明史,微小的紙張和石頭會與龐大帝國的命運興衰相連。媒介與傳播乃是塑造人類文明的一大動力,不可輕視。
如今,新媒介與新傳播興起,深刻改變了人的定義和社會的形態(tài)。當(dāng)5G技術(shù)使得醫(yī)生能夠遠程操作機械手臂進行手術(shù),我在此處而我的行為發(fā)生在彼處,預(yù)示著人類將可以實現(xiàn)其他時空的遠程數(shù)字在場(digital present);“我”不再是此時此刻的唯一肉身,還分裂為其他時空的數(shù)字分身。更甚者,隨著可穿戴設(shè)備的發(fā)展普及,芯片植入人體的賽博想象也并不再是科幻小說里的場景。如果技術(shù)與人融合而出現(xiàn)“后人類”,且數(shù)字信息與意識直接聯(lián)通,那么現(xiàn)有的物質(zhì)與精神、身體與心靈、傳播內(nèi)容與媒介載體的二元分立,都將被抹平和消解。就社會來說,如果媒介遍布到了各個生活場景,人或?qū)⒚繒r每刻都能進行具身傳播,萬物皆媒,萬物互聯(lián)。我們并非置身歷史之外,而是在波瀾壯闊的歷史之中;既處在歷史的風(fēng)口浪尖上,中國的新聞傳播學(xué)科與高校院系,當(dāng)有何作為?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有前瞻性的國家戰(zhàn)略,在傳媒領(lǐng)域處于全國頂尖行列的中國傳媒大學(xué),當(dāng)響應(yīng)黨中央號召,為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做出應(yīng)有之貢獻,實驗室之成立,就是要回答時代的命題。
1.建設(shè)全媒體布局與現(xiàn)代傳播體系是國家的戰(zhàn)略需求
媒體融合發(fā)展已上升至國家戰(zhàn)略層面,是黨中央著眼鞏固宣傳思想文化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以及維護意識形態(tài)安全與政治安全做出的重大戰(zhàn)略部署,對媒體融合與傳播領(lǐng)域的基礎(chǔ)理論研究,符合構(gòu)建新型主流媒體、全媒體傳播格局與現(xiàn)代傳播體系這一國家重大需求。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媒體融合發(fā)展。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來認識新聞輿論工作,推動媒體融合發(fā)展、建設(shè)全媒體已經(jīng)成為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fā)展。這些重要論述,不僅為推進媒體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也意味著媒體融合已成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議題,成為中央層面部署推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因此,對媒體融合與傳播的基礎(chǔ)性理論建構(gòu),有助于從長遠規(guī)劃上持續(xù)推動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建設(shè)媒體融合與傳播的基礎(chǔ)理論體系并開展相關(guān)應(yīng)用性基礎(chǔ)研究,是鞏固宣傳思想文化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關(guān)乎治國理政和定國安邦、關(guān)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戰(zhàn)略舉措。
2.建立完善的基于跨學(xué)科視野的新聞傳播學(xué)研究體系
構(gòu)建跨學(xué)科媒體融合與傳播基礎(chǔ)理論體系,是順應(yīng)世界科技前沿與信息傳播行業(yè)變革的需要,其中建設(shè)國家重點實驗室正是學(xué)界順應(yīng)這一潮流的關(guān)鍵性一步。近年來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ǎn)業(yè)變革蓄勢待發(fā),顛覆性技術(shù)和理論不斷涌現(xiàn),在以5G現(xiàn)代通信技術(shù)為核心的新一代移動網(wǎng)絡(luò)、大數(shù)據(jù)科學(xué)與技術(shù)、新一代人工智能與人機混合智能等新理論與新興科學(xué)技術(shù)的驅(qū)動下,媒體融合驅(qū)動傳播主體走向多元、下沉和智能化,曾經(jīng)單一而壟斷的專業(yè)化、組織化和建制化的傳播主體逐漸讓位于多元化、智能化的新傳播主體生態(tài),媒體融合與傳播相關(guān)領(lǐng)域正在不斷催生新技術(shù)、新產(chǎn)品、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并將強力驅(qū)動媒體形態(tài)、服務(wù)模式以及傳播模式變革。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要進一步研究相關(guān)理論和實踐問題,強化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形成學(xué)術(shù)研究體系,為媒體融合實踐提供理論保障。
3.創(chuàng)新公共服務(wù)模式是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從國家重點實驗室面向國民經(jīng)濟主戰(zhàn)場的關(guān)鍵定位出發(fā),開展媒體融合與傳播基礎(chǔ)理論研究是新時代提升公共服務(wù)和社會治理水平的緊要需求,更是滿足我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多樣化需求的基礎(chǔ)與重點。媒體深度融合發(fā)展是當(dāng)代信息技術(shù)變革和新時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推動社會信息化不斷升級,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介成為當(dāng)代社會發(fā)展的基礎(chǔ)性、結(jié)構(gòu)性支柱,是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引擎”和“基礎(chǔ)設(shè)施”。媒體深度融合是傳統(tǒng)媒體與新媒體、媒體與社會、媒體與人之間的高層次融合,全媒體的發(fā)展根植于當(dāng)代社會的信息化過程,滿足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因此,要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在新時代社會發(fā)展和治理的過程中把握媒體融合發(fā)展的基本定位和公共服務(wù)功能。
二、新時期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與傳播學(xué)基礎(chǔ)研究方向
新媒體環(huán)境下,“傳播”不再是受制于人的工具,其本身就悄無聲息地改變著社會與人類的發(fā)展,經(jīng)典傳播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理論成果都是在大眾傳播時代形成的,即使其中仍有不少理論經(jīng)久不衰,依然部分適用于當(dāng)今社會,但現(xiàn)有的依托傳統(tǒng)媒體時代建立的傳播學(xué)理論已是強弩之末,無法為今天的融媒體社會指引方向,發(fā)展新時期傳播學(xué)研究重點在于基礎(chǔ)研究的突破。實驗室是國家組織開展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聚集和培養(yǎng)優(yōu)秀科技人才、開展高水平學(xué)術(shù)交流、具備先進科研裝備的重要科技創(chuàng)新基地,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是提升媒體融合與傳播領(lǐng)域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的關(guān)鍵。當(dāng)今學(xué)界研究皆旨在解決媒體融合領(lǐng)域存在的關(guān)鍵基礎(chǔ)性問題,實現(xiàn)前瞻性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基礎(chǔ)研究、引領(lǐng)性原創(chuàng)成果的重大突破,進而加大科研成果應(yīng)用轉(zhuǎn)化力度,其總體目標(biāo)是創(chuàng)建媒體融合與傳播理論及服務(wù)模式。新時期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與傳播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具體思路和方向應(yīng)該包括如下幾個領(lǐng)域。
1.媒體融合和未來傳播形態(tài)
以媒介學(xué)的視野來看,所謂媒介,當(dāng)是物質(zhì)技術(shù)、文本符號和組織架構(gòu)的三位一體;延森也認為媒介應(yīng)理解為物質(zhì)、話語和機構(gòu)三個層面。“媒體融合”或“融媒體”也不單單停留在物質(zhì)技術(shù)層面。把新媒介當(dāng)作一種新的內(nèi)容生產(chǎn)工具,在組織上另立“新媒體”部門,是目前大部分傳統(tǒng)媒體的做法。問題在于:第一,媒介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物件,而是生生不息的傳播場景和事件。第二,占有和使用新技術(shù)易,但媒體融合不是新瓶裝舊酒,還涉及新技術(shù)下文本符號樣態(tài)的創(chuàng)造嘗試、組織內(nèi)部架構(gòu)的變革。近年來各種別開生面的新聞樣態(tài)和“新媒體”部門的設(shè)立,是值得肯定的開端。但深入的嘗試和變革即使不打破既有規(guī)則和秩序,也難免陣痛,可以說媒體融合無成規(guī)可循、無坦途可走—既定的規(guī)則是以往實踐的沉淀,已有的道路來自先行者的步步摸索。學(xué)界與業(yè)界,都是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中國傳媒大學(xué)作為中國廣播電視界的搖籃,與媒體業(yè)一向聯(lián)系緊密,實驗室當(dāng)在探索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與業(yè)界攜手砥礪共進,發(fā)揮在該領(lǐng)域研究的帶頭作用,真正實現(xiàn)新媒體、融媒體的發(fā)展,指引業(yè)界進行真正的探索實踐。
2.智媒體時代輿論發(fā)展規(guī)律與輿論引導(dǎo)能力建設(shè)
隨著用戶自制內(nèi)容(UGC)、機器自制內(nèi)容(MGC)以及算法推薦技術(shù)的興起和繁榮,媒體融合驅(qū)動傳播主體走向多元、下沉和智能化,曾經(jīng)單一而壟斷的專業(yè)化、組織化和建制化的傳播主體逐漸讓位于多元化、智能化的新傳播主體生態(tài)。多元主體的復(fù)雜互動成為媒體融合的新常態(tài),也影響著社會輿論格局的分化與重組。在傳播主體的多元化進程中,傳統(tǒng)的新聞傳播秩序和輿論格局也出現(xiàn)分化和重組,并呈現(xiàn)出兩個方面的鮮明特征:第一,多元主體導(dǎo)致的輿論高度不確定性和政府、企業(yè)危機應(yīng)對的常態(tài)化;第二,輿論場的分化,即傳統(tǒng)媒體權(quán)威性和把關(guān)力的下降,以及社交媒體驅(qū)動的多元表達生態(tài)的出現(xiàn)。媒體信息傳播智能處理研究主要解決國家媒體內(nèi)容生產(chǎn)的“四力”,即傳播力、引導(dǎo)力、影響力、公信力提升的問題。信息傳播已經(jīng)從文本、音頻、圖像、視頻等單一媒體形態(tài)過渡到相互融合的跨媒體形態(tài)。海量媒體數(shù)據(jù)的快速增長環(huán)境下,融媒體與傳播研究急需探索研究面向未來媒體的信息智能處理關(guān)鍵技術(shù),提高內(nèi)容生成速度和質(zhì)量,推動公信力的快速建立、輿論的正確引導(dǎo)、內(nèi)容的精準(zhǔn)傳播和影響力的迅速提升。新時代的新特征、新任務(wù)下,如何壯大主流媒體、有效有力地傳遞黨和政府的主流聲音,是媒體深度融合發(fā)展的重點和難點。而面對日趨復(fù)雜的社會輿論場域,傳播途徑和模式的創(chuàng)新應(yīng)用為主流媒體影響力建設(shè)提供了新的思路。更好地發(fā)揮出媒體融合傳播的潛力,強化主流融合媒體在社會輿論當(dāng)中的傳播力、引導(dǎo)力、影響力、公信力,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做大做強正面宣傳,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讓網(wǎng)絡(luò)空間的主旋律更響亮、正能量更強勁應(yīng)是新時期融媒體研究的落腳點。
3.媒介文化與數(shù)字技術(shù)
藝術(shù)創(chuàng)作離不開媒介和技術(shù)。中國商周時期的造型和文字依附于青銅器,古希臘的“藝術(shù)”一詞也屬于“技藝人”的領(lǐng)域。藝術(shù)和其他符號及知識,依憑特定媒介進行的傳播,便形成文化。因文化藝術(shù)與媒介傳播的密切關(guān)系,新媒介和傳播方式的出現(xiàn),每每衍生出新的文化藝術(shù)形態(tài),同時改變舊有的文化藝術(shù)。歐洲近代谷登堡印刷術(shù)帶來了報紙、期刊、圖書的印刷文化;19世紀(jì)攝影和電影的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改變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定義,標(biāo)志著現(xiàn)代視覺文化的開端。如今,我們又面臨一個虛擬現(xiàn)實的、邊界越發(fā)模糊的新時代:這不但指難以計數(shù)、無處不在的技術(shù)性影像深刻地構(gòu)建了現(xiàn)實,還指字面意義上VR、AR等技術(shù)直接讓我們體驗到了一種全新的現(xiàn)實。如果說,20世紀(jì)是電視、電影的百年,21世紀(jì)將有基于數(shù)字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的動畫、游戲等豐富和改變?nèi)祟愇幕囆g(shù)的生態(tài)。同時值得關(guān)注的是,上述這些領(lǐng)域都是中國傳媒大學(xué)的王牌專業(yè),依靠深厚的歷史積淀、雄厚的師資力量、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和先進的研究理念,國家重點實驗室也應(yīng)在媒介文化和數(shù)字藝術(shù)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旨在為業(yè)界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和學(xué)術(shù)支撐,開拓學(xué)界在該領(lǐng)域下一階段研究視野,共同引領(lǐng)研究,不斷積累,使該領(lǐng)域形成質(zhì)的突破。
4.社會治理與智慧城市建設(shè)
新時期媒體融合縱深發(fā)展與傳播學(xué)基礎(chǔ)研究的初衷之一就是助益社會治理。“社會”之概念具化到現(xiàn)實生活中,往往落實在“城市”場景。現(xiàn)代化進程除了市場化、工業(yè)化和民主化等,也包括城市化,尤其21世紀(jì)以來中國城市化速度迅猛,城市問題浮現(xiàn)。而城市從起源上就與傳播有關(guān),不論是古希臘城邦繁盛的交流,還是商周王朝的國都作為天人交流與四方匯聚的中心。早期社會學(xué)家強調(diào)現(xiàn)代城市是一種關(guān)系的形式或心理狀態(tài),城市不僅有實體的人和建筑,還有報紙等媒介凝聚起來的社會關(guān)系。近年來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又創(chuàng)造出數(shù)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當(dāng)今的中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個人移動終端與公共屏幕無處不在,無形的數(shù)字傳播實踐與有形的建筑實體,一起組成了中國當(dāng)代城市。此外,社會治理之不同于社會管理,在于政府和企業(yè)、公民等各方力量協(xié)商和溝通,這也關(guān)系到新聞傳播學(xué)。
5.人才培養(yǎng)模式與國際合作
媒體業(yè)日新月異,業(yè)界實踐與高校教育如何同步共進,是人才培養(yǎng)的當(dāng)務(wù)之急。中宣部和科技部創(chuàng)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就是依靠中國傳媒大學(xué)的國家一流學(xué)科,兼納新聞傳播學(xué)、信息與通信工程、戲劇與影視學(xué)、設(shè)計學(xué)、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等,以搭建融媒體“高、精、尖”人才培養(yǎng)體系。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diào),媒體競爭關(guān)鍵是人才競爭,媒體優(yōu)勢核心是人才優(yōu)勢。要提高業(yè)務(wù)能力,勤學(xué)習(xí)、多鍛煉,努力成為全媒型、專家型人才。媒體融合領(lǐng)域高精尖人才培養(yǎng)模式研究應(yīng)緊扣融媒體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情況和行業(yè)需求變化,注意動態(tài)調(diào)整學(xué)術(shù)方向,大力推動科教融合、產(chǎn)學(xué)結(jié)合。培養(yǎng)方案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機制,積極推進個性化培養(yǎng)和國內(nèi)外聯(lián)合培養(yǎng)模式,全面提升人才綜合素質(zhì)。
現(xiàn)階段傳播學(xué)研究更要力求以全球視野,聚天下英才,風(fēng)云際會,共襄盛事。作為陣前先鋒,國家級實驗室將與國際著名媒體機構(gòu)、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媒體教育研究機構(gòu)展開合作,并為國際學(xué)者和學(xué)生提供高端國際交流平臺,建立成熟的國際學(xué)者和學(xué)生駐校合作研究制度,并通過開放課題申請、合作研究和主辦系列國際學(xué)術(shù)活動等方式,吸引國內(nèi)外高水平研究人員來華開展合作研究,共同發(fā)表具有國際學(xué)術(shù)影響力和引領(lǐng)力的學(xué)術(shù)成果,為我國新聞傳播學(xué)研究與世界接軌,響應(yīng)國家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針,助力國際合作與人才培養(yǎng)。
三、結(jié)語
媒介之力與傳播之網(wǎng),將要或已經(jīng)改變?nèi)说亩x和人類社會形態(tài),關(guān)乎21世紀(jì)中國乃至人類世界的共同命運,當(dāng)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行業(yè)變革的實踐需求來看,我國的媒體融合正在全方位深入展開和持續(xù)創(chuàng)新變革,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亟需從更為廣闊的前瞻視角,進行媒體融合與傳播基礎(chǔ)理論的研究,為構(gòu)建強大的新型主流媒體、全媒體傳播格局與現(xiàn)代傳播體系提供關(guān)鍵理論指導(dǎo)和核心技術(shù)支撐;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biāo)、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將與學(xué)界勠力同心、秉燭先行、洞照未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注釋:
① 習(xí)近平.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fā)展 構(gòu)建全媒體傳播格局[J].求是,2019(6).
② 伊德.技術(shù)與生活世界:從伊甸園到塵世[M].韓連慶,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
③ CHARLES H C.Social Organization: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M].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3.
④ 藍江.5G、數(shù)字在場與萬物互聯(lián)—通信技術(shù)變革的哲學(xué)效應(yīng)[J].探索與爭鳴,2019(9).
⑤ 喻國明,耿曉夢.智能算法推薦: 工具理性與價值適切[J].全球傳媒學(xué)刊,2018(12).
⑥ 延森.媒介融合:網(wǎng)絡(luò)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M].劉君,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8.
⑦ 本雅明.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M].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
⑧ 庫蕾.古希臘的交流[M].鄧麗丹,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
⑨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
⑩ 帕克,等.城市社會學(xué)[M].宋俊嶺,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