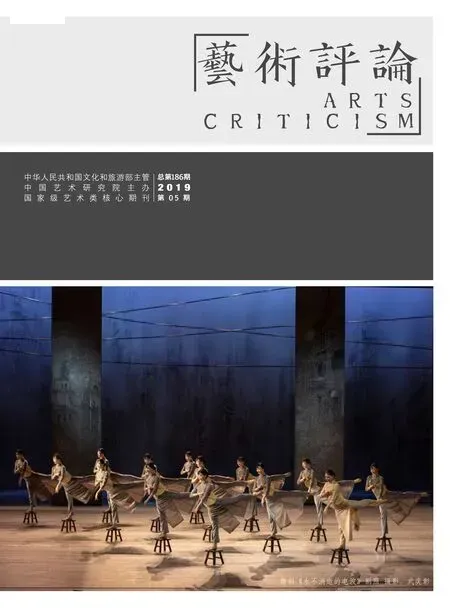關(guān)于藝術(shù)史觀念的書寫和建構(gòu)
——論高名潞的《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
一、藝術(shù)史觀念的種種路徑與高名潞的匣子、格子、框子說
研究藝術(shù)史一定會(huì)依據(jù)特定的觀念構(gòu)筑的路徑進(jìn)行藝術(shù)史的書寫。線性邏輯、并置描述、觀念為先、問題為綱等,必須得有一個(gè)“觀念”,然后才能去講“藝術(shù)史故事”。
黑格爾的《美學(xué)》是藝術(shù)史自身發(fā)展的目的性預(yù)設(shè)為觀念模型寫作的第一個(gè)范本,后世諸多寫作者和批評(píng)家便是以此書寫藝術(shù)史的“意志的行程”。李格爾以及他的學(xué)生們?yōu)榇淼木S也納學(xué)派便是這種寫作方式的代表。用施洛塞爾的說法:我們運(yùn)用“藝術(shù)意志”這個(gè)詞,主要是在談?wù)摽傮w的藝術(shù)現(xiàn)象,談?wù)撘粋€(gè)時(shí)期、一個(gè)種族或一個(gè)社會(huì)產(chǎn)生的藝術(shù)作品,而“藝術(shù)意志”這個(gè)詞一般用來概括個(gè)別藝術(shù)作品的特點(diǎn)。
潘諾夫斯基明確反對(duì)“藝術(shù)意志”說,認(rèn)為這是反映論的翻版。他據(jù)此提出了他的“圖像學(xué)”原則:其一,文獻(xiàn)的可證明性,其二,不僅文獻(xiàn)可證明而且其在形式要素中意義變化所改變的效果還要對(duì)今天產(chǎn)生影響,即從訓(xùn)詁的角度發(fā)揮糾正功能,最后,文獻(xiàn)的書面評(píng)論或圖畫復(fù)制為形式的提示,促使我們改變了對(duì)決定一件藝術(shù)作品外觀的實(shí)際數(shù)據(jù)的錯(cuò)誤看法。這是以圖證史、以史證圖的嚴(yán)格的波普爾式的可證實(shí)的書寫原則。
美國(guó)學(xué)者詹姆斯·埃爾金斯堅(jiān)持并非要用觀念和構(gòu)想剪裁藝術(shù)史,而是以對(duì)各個(gè)時(shí)期各個(gè)人為依據(jù)的藝術(shù)作品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和實(shí)例分析寫作藝術(shù)史。針對(duì)當(dāng)下的種種新藝術(shù)史觀念,曹意強(qiáng)提出理論的“有效性”問題,如德勒茲的激進(jìn)經(jīng)驗(yàn)主義的新藝術(shù)史原則,把問題和結(jié)論都設(shè)置成了一個(gè)預(yù)定的答案。這就是無效的藝術(shù)史觀念的原則。
這樣,我們就有了3個(gè)藝術(shù)史觀念的樣本:1.目的性,所謂藝術(shù)意志;2.史實(shí)的可確證;3.非目的性的經(jīng)驗(yàn)主義,追求陳述的精準(zhǔn)和清晰。對(duì)問題2一般都沒疑問,只不過達(dá)到潘諾夫斯基圖像學(xué)的絕對(duì)強(qiáng)度原則是困難的,但基本史實(shí)是藝術(shù)史觀念思考的基礎(chǔ)。問題3深入追究總是和問題1有深度牽連,即依據(jù)什么原則說是“非目的性的”?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來討論高名潞的專著《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再現(xiàn)與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的理論意義。
高名潞給我們建立的是這樣一個(gè)具有形象示義的演化系統(tǒng):以“再現(xiàn)”為軸線的匣子—格子—框子的藝術(shù)史觀念。
匣子指20世紀(jì)以前的古典寫實(shí)藝術(shù)及相關(guān)藝術(shù)史書寫模式,格子是指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上半葉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及理論觀念模式(這并非高氏首創(chuàng),據(jù)我閱讀所及,至少夏皮羅和克勞斯用過這個(gè)術(shù)語)。而框子則是指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的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實(shí)踐及觀念模式。
高著對(duì)這三者的關(guān)系表述如下:“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再現(xiàn)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是歷史發(fā)展的主要線索在兩個(gè)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展開:一個(gè)是媒介美學(xué),就是對(duì)媒體自身以及媒體擴(kuò)張的不斷論證,從格林伯格到弗雷德,再到克勞斯,他們勾畫了從現(xiàn)代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媒體擴(kuò)展史。另一個(gè)領(lǐng)域是政治的、文化的或者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語言學(xué),簡(jiǎn)單地講,就是把意識(shí)形態(tài)和社會(huì)文化不斷地符號(hào)邏輯化。比如德里達(dá)、福柯、新馬克思主義藝術(shù)史家克拉克、詹明信和歐文斯。”那就是從古典的“匣子”到現(xiàn)代主義的“格子”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框子”。匣子是自足的,以視覺深度介入歷史。平面格子是自由、不及物、有隱性深度的。后現(xiàn)代主義反對(duì)二者,強(qiáng)調(diào)上下文、內(nèi)部外部、藝術(shù)生產(chǎn)、藝術(shù)系統(tǒng)之間的整體關(guān)系,因此是一個(gè)什么都可以放進(jìn)去的“框子”。
概而言之:第一部分四個(gè)大章主要是形式—媒介的藝術(shù)史觀念的研究,他用“象征再現(xiàn)”表述他的西方藝術(shù)史觀的哲學(xué)轉(zhuǎn)向,從瓦薩里經(jīng)由康德、黑格爾而形成“藝術(shù)史的原形:理念的外形及其顯現(xiàn)秩序”的各類形式主義藝術(shù)史的理論坐標(biāo)基礎(chǔ)的建立。換句話說,高名潞預(yù)設(shè)的“藝術(shù)史原形”,不論是從形式自律、眼睛的凝視到阿恩海姆的形式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和貢布里希的視覺藝術(shù)以形式完形構(gòu)成獨(dú)特的知識(shí)樣本和美學(xué)樣本,都預(yù)設(shè)了這樣的藝術(shù)史觀念: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是一個(gè)“自足匣子”。而這個(gè)匣子即是理念的外形或顯現(xiàn)了秩序的理念。
第二部分也是四大章,稱為“符號(hào)再現(xiàn):語言轉(zhuǎn)向”。他把圖像學(xué)外部求證的圖像志的方法看成“還原圖像的語義邏輯”,并從伽達(dá)默爾、維特根斯坦、丹托及古德曼的詞語與圖像的對(duì)應(yīng)、衍義、釋讀的可能性和多義性的語言哲學(xué)等角度思考藝術(shù)史觀念。而海德格爾、夏皮羅、德里達(dá)關(guān)于梵高《鞋》的爭(zhēng)議便是這個(gè)“物的真理”的圖像如何在符號(hào)性的呈現(xiàn)中被再現(xiàn)出來的一個(gè)“語言轉(zhuǎn)向”的標(biāo)本。與此相對(duì),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史觀念也把這種再現(xiàn)看成是真理,但不是物的真理,而是思辨再現(xiàn)的世俗化:再現(xiàn)當(dāng)下時(shí)間與屬于個(gè)人“純藝術(shù)的內(nèi)部神秘本質(zhì)”的藝術(shù)自律。于是,由圖像的語言求證、作為圖像語言陳述的“物的真理”和藝術(shù)自律的本質(zhì),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主義:媒介烏托邦”,這便是格林伯格的平面性即“回到媒介自身”。由此,媒介被看成藝術(shù)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中的主角。弗雷德的物體的“劇場(chǎng)化”和克勞斯的“場(chǎng)域化”登場(chǎng)。進(jìn)一步推導(dǎo),那便是這擬人化的、主體化了的“秩序化”的物的劇場(chǎng)成為了阿多諾的烏托邦的表征物和克拉克的“景觀”資本的符號(hào)籌碼。這便是高名潞的“格子”的藝術(shù)史觀念。
第三部分有五大章,主題是“詞語再現(xiàn):上下文轉(zhuǎn)向”,即從“格子”走向“框子”:“后現(xiàn)代的政治再現(xiàn)語言學(xué)”。特征是:政治再現(xiàn)的話語邏輯,而藝術(shù)的“詞語和語境成為身份再現(xiàn)本身”。這取決于這樣一個(gè)根本的政治基礎(chǔ):“現(xiàn)代性是‘我們的’,而當(dāng)代性是‘每個(gè)人的’。”當(dāng)代前衛(wèi)藝術(shù)看起來越來越非社會(huì)性,而實(shí)質(zhì)是對(duì)資本體制的支離和矛盾的再現(xiàn)。特別是福柯對(duì)權(quán)力“視線”的鮮血淋漓的揭底推進(jìn)了新藝術(shù)史的“去原創(chuàng)性:把藝術(shù)還原為物”,用符號(hào)和詞語作為藝術(shù)自身,造成泛圖像和語詞化的形象的思想肉身化的后歷史主義的藝術(shù)敘事。于是乎,藝術(shù)與哲學(xué)成為一體,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的這一“再現(xiàn)”特征由演進(jìn)的三個(gè)階段而走向解體:藝術(shù)終結(jié)了。藝術(shù)史開始轉(zhuǎn)向了!
那么什么樣的藝術(shù)史觀能把這種種東西放到一起?答案是:框子。不論是“我們的”,還是“你的”“我的”“他的”,“框子”如同雜貨架,什么樣的東西都可以扔在里面。至此,我們明白了高名潞的理論意圖。
其一,他基本上是站在西方藝術(shù)史的史論之內(nèi)梳理這條線索,結(jié)論是藝術(shù)史終結(jié),而“轉(zhuǎn)向”則應(yīng)是高名潞的預(yù)設(shè)。其二,我更樂于把他的“匣子—格子—框子”看成是“形式—媒介”“符號(hào)再現(xiàn):語言轉(zhuǎn)向”“詞語再現(xiàn):上下文轉(zhuǎn)向”的形象比喻,而不是理論術(shù)語。其三,從高名潞的具體行文是容易區(qū)分這里的兩個(gè)轉(zhuǎn)向;但從概念內(nèi)涵上去細(xì)究,去界定“符號(hào)再現(xiàn)”與“詞語再現(xiàn)”就會(huì)麻煩重重。換句話說,高名潞可以不需要給自己找麻煩,一個(gè)個(gè)大問題列出來,從幾大方面呈現(xiàn)出一個(gè)整體的藝術(shù)史觀念的面貌即可,至于它們之間有什么樣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讀者可各自去找答案。許多藝術(shù)史及藝術(shù)史觀念類的著作就是這樣寫的。
當(dāng)然,找麻煩有找麻煩的快樂和意圖。這即是我們下文要討論的。
首先我認(rèn)為,在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的研究中,梳理出這樣一條清晰的邏輯脈絡(luò)是中國(guó)視覺藝術(shù)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項(xiàng)重大學(xué)術(shù)成果,非苦讀數(shù)年難成此書。這體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
(一)打通三個(gè)方面的知識(shí)和專業(yè)壁壘。從總體上說,不論有多少種觀點(diǎn)和看法,諸如道德學(xué)派的、社會(huì)學(xué)的、形式主義的、圖像學(xué)的、人文學(xué)以及科學(xué)的,但大致有三條路徑:第一條專注于過往美術(shù)史的書寫與研究,基本上不太會(huì)關(guān)注哲學(xué)家和批評(píng)家的工作,主要是以實(shí)證的美術(shù)文獻(xiàn)為依據(jù)而開展工作。第二條是當(dāng)代藝術(shù)批評(píng)的書寫,他們的工作比較復(fù)雜,與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美學(xué)等均發(fā)生關(guān)系,但核心工作是從歷史的橫坐標(biāo)和當(dāng)代社會(huì)的縱坐標(biāo)上確定當(dāng)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問題與走向,進(jìn)行藝術(shù)批評(píng)寫作。第三條是美學(xué)或哲學(xué)的藝術(shù)思想的寫作,他們是從某種預(yù)設(shè)的理論出發(fā),從史的或當(dāng)代的藝術(shù)事例中解釋某種藝術(shù)現(xiàn)象。在中國(guó),這三個(gè)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各不相關(guān)。因此,高名潞的這部《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特別難能可貴地將三者打通,以問題為導(dǎo)向,由各個(gè)學(xué)派第一層次的作家為論述主體,深入到第二乃至第三層次作家專項(xiàng)研究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的梳理,既可以作為總體藝術(shù)觀念史的研究導(dǎo)論,更可以作為深入研習(xí)的工具書。
(二)推進(jìn)當(dāng)代中國(guó)藝術(shù)批評(píng)的國(guó)際學(xué)術(shù)語境。高名潞該書論述的諸多重要學(xué)者的著作,有不少是有中譯本的。但他按照他讀英文的理解語境來書寫,特別是在論述過程中,對(duì)諸多關(guān)鍵概念和詞匯的譯法、漢語語境的理解差異的討論,非常有價(jià)值;對(duì)譯述和閱讀西方藝術(shù)理論原典,提供了更多的思考點(diǎn)。由某些流派主要人物的研究引申到附屬觀點(diǎn)和人物的討論,特別是20世紀(jì)60年代以后的研究,從整體上呈現(xiàn)出了當(dāng)代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研究的同態(tài)化的面貌,為比照當(dāng)下的中國(guó)藝術(shù)批評(píng)和史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書系索引。如他將“objecthood”譯為“物體化”而沒有譯為“物性”。他認(rèn)為“物性”的對(duì)應(yīng)詞是“thingness”。物體化更接近現(xiàn)代主義,特別是極少主義。中文的“物性”對(duì)應(yīng)英文“materialization”,非“objecthood”。再如關(guān)于“批判的”(critical)的中國(guó)習(xí)慣定義的校正,該詞在康德那兒是指理性尋求獨(dú)立于一切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的那種批判,而在英文指“不斷超越”和“創(chuàng)新”,因此為了避免漢語語義誤解,他譯為“觀念的”。關(guān)于“symbol”的傾向性說明以及“sign”和“mark”三者的區(qū)別,特別指出了它們?cè)谥形闹械幕煊谩?/p>
(三)著力建構(gòu)中國(guó)藝術(shù)觀念與西方藝術(shù)觀念不同的坐標(biāo)系統(tǒng)。高名潞寫在一個(gè)注里的關(guān)于圖像學(xué)與中國(guó)畫的非“自足匣子”的形象構(gòu)成的對(duì)比十分精彩:“筆者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繪畫更多地具有‘儀象’特點(diǎn),所謂‘儀象’,就是儀表、風(fēng)儀、儀仗等。所以,從漢代畫像石上的人物、動(dòng)物、場(chǎng)景和風(fēng)景到山水畫,再到宋代以來的畫院人物和花鳥繪畫等,都不注重視覺圖像的個(gè)別性、故事情節(jié)與細(xì)節(jié)的偶然性,而注重整體儀式的必然性特點(diǎn),不過于強(qiáng)調(diào)也不特別專注個(gè)別的表情和動(dòng)作的描繪,即便有所體現(xiàn),也要服從整體儀態(tài)。而且,很多時(shí)候這些儀態(tài)都是重復(fù)和規(guī)范化的,比如文人雅集、宮廷仕女、神仙儀仗禮佛圖等。但是,由于重儀象的中國(guó)古代人物畫抑制了語義的任意性,因此反而保持了視覺的外延性,它的視覺是自足聯(lián)想的,《女史箴圖》或者《任熊自畫像》無需追究語義,只需去感知書寫性形象的‘氣韻’如何生動(dòng)。但這個(gè)聯(lián)想自足不是那個(gè)和外在空間切斷的‘自足匣子’。當(dāng)然,我們不能否認(rèn),圖像學(xué)可能會(huì)讓中國(guó)畫領(lǐng)域的某些題材研究受益,然而,中國(guó)人物畫畢竟不像西方文藝復(fù)興乃至之前的宗教偶像(那些與“自足匣子”有關(guān)的古典繪畫和浮雕)那樣,是圖像學(xué)研究的天然對(duì)象。中國(guó)人物畫研究因此需要建構(gòu)一種更符合自身的方法論。再如還是說“匣子”,在該書第378—379頁把中國(guó)繪畫的“以小觀大”和西方透視法推動(dòng)的“匣子”作比較,由高遠(yuǎn)、深遠(yuǎn)、平遠(yuǎn)的模式?jīng)_破西方“匣子”和“框子”的取景模式。
(四)提出了扎根于國(guó)際文化多樣性的中國(guó)藝術(shù)觀念的“意派”模型。這個(gè)問題的設(shè)問,在于高名潞要為中國(guó)藝術(shù)找出路:即“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何方?
這里的第三點(diǎn)和第四點(diǎn)是我下一個(gè)論題的主要內(nèi)容。
二、“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向何處?
在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研究中,不論古代美術(shù)史研究還是當(dāng)代藝術(shù)批評(píng),言必西方,論必西論。因此,寥寥可數(shù)的幾位歐美諸國(guó)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者寫的中國(guó)畫史研究,似乎篇篇堪稱經(jīng)典。高名潞的《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雖是研究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但貫穿其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是同時(shí)要證明這種“套用”中國(guó)藝術(shù)的方法的不著邊際。因此,他的“藝術(shù)史觀念”的轉(zhuǎn)向,我更樂于說,是他提出自己的中國(guó)藝術(shù)史觀念的自身特征的理論預(yù)設(shè)。換句話說,他的目的正在于證明他的新理論的必然性和可實(shí)踐性。
1992年由洪再辛選編的《海外中國(guó)畫研究文選》收有多篇西方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家的經(jīng)典名作。羅樾本著沃爾夫林一路風(fēng)格史傳統(tǒng),認(rèn)為漢—宋由裝飾性、表現(xiàn)性和再現(xiàn)性風(fēng)格的演變,明確指出風(fēng)格史是一流畫家個(gè)人選擇的結(jié)果,而“時(shí)代精神”只是“一組作品所構(gòu)成的圖式的實(shí)質(zhì)”。而方聞則對(duì)此觀點(diǎn)提出嚴(yán)厲批評(píng),認(rèn)為李格爾—沃爾夫林一派的風(fēng)格史方法解決不了中國(guó)繪畫的斷代和真假問題,堅(jiān)持從作品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分析研究中國(guó)繪畫。這種“套用”西方理論方法研究中國(guó)繪畫史的紛爭(zhēng),在班宗華、高居翰、羅浩三人關(guān)于高居翰的《江岸送別》的討論中很具代表性;“外向觀”強(qiáng)調(diào)從作品產(chǎn)生時(shí)代、背景、生平“進(jìn)程加以理解”;“內(nèi)向觀”強(qiáng)調(diào)從作品出發(fā),按藝術(shù)自律形式展開探討。貢布里希的《西方人的眼光——評(píng)蘇立文的〈永恒的象征——中國(guó)山水畫藝術(shù)〉》的書評(píng)則對(duì)這種“套用”提出嚴(yán)厲批評(píng),認(rèn)為用拉斯金的理論解釋中國(guó)人的山水觀,把東方人的自然觀與愛因斯坦相對(duì)論并提,完全都是“似是而非”的說法。
但問題是我們自己沒有概念工具,除了“拿來主義”還有什么其他的招數(shù)!我想,這更是高名潞《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的破冰之旅中更具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地方。正因此,他在討論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的演進(jìn)過程之中,在關(guān)鍵概念上,試圖勾畫出中國(guó)藝術(shù)的觀念特征和核心概念,并指出它們完全是建立在不同于西方藝術(shù)史的觀念坐標(biāo)之上,比西方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者有更全面和縱深的學(xué)術(shù)視野。譬如,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根本問題,中國(guó)與西方走的是兩個(gè)完全不同的走向;西方自古至今的真、善、美和中國(guó)的氣韻、風(fēng)骨等根本不可比對(duì)。在阿奎那的三大超越中,首先“真”是上帝,上帝的形式是“善”,善當(dāng)與這個(gè)形式靜觀對(duì)象之時(shí)就是“美”。中國(guó)5世紀(jì)的謝赫提出“六法”,其第一便是“氣韻生動(dòng)”,是提升超逸的意思;而“風(fēng)骨“的概念是一種“境界”。這兩種不同的觀念決定了兩種根本不同的藝術(shù)世界。西方再現(xiàn),觀念在先、實(shí)證在后,觀念演出藝術(shù)觀念,用藝術(shù)實(shí)例證實(shí)觀念的再現(xiàn),核心是再現(xiàn)認(rèn)識(shí)論、反映論,呈現(xiàn)的是永遠(yuǎn)及物性。中國(guó)藝術(shù)觀是人生觀、生命觀,體現(xiàn)超逸、風(fēng)格、趣味、不可分析、不可測(cè)性、不及物性。
再如在對(duì)藝術(shù)的感知方式上,西方美術(shù)的感覺與超感覺、知覺與理性的二元合法性對(duì)抗與合法性互換的思維方式,成為西方形而上學(xué)哲學(xué)以及語言學(xué)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而中國(guó)的語言和象形文字系統(tǒng)完全不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無法找到感覺和非感覺的區(qū)分。再如中國(guó)藝術(shù)之由氣韻而筆墨而致“言不盡意”“言外之意”的美學(xué)觀念更是西方藝術(shù)觀念所沒有的。
因此,以西方這種再現(xiàn)論為主導(dǎo)的藝術(shù)史觀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是該到了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的時(shí)候了!
高名潞的《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把當(dāng)下的藝術(shù)史寫作、哲學(xué)背景的導(dǎo)入、符號(hào)學(xué)、文學(xué)批評(píng)、策展、當(dāng)下藝術(shù)現(xiàn)狀研究等各守一隅的狀況,以全景式的方式理出一條邏輯線索,并以“再現(xiàn)”的種種演變剖析出每一時(shí)段的“特殊”內(nèi)容,最終走到當(dāng)下的分崩離析的場(chǎng)景。
由此,他推導(dǎo)出了他的“在地性之上”的“世紀(jì)思維”:即以“差意性”之為基礎(chǔ)的中國(guó)“意派論”。為了表達(dá)他的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他造了一個(gè)詞:差意,由“差異”和“不似之是”二義合成,類似英文“deficits”。他給出的理由是:“再現(xiàn)理論執(zhí)著于藝術(shù)如何接近真理和現(xiàn)實(shí)真實(shí),努力讓藝術(shù)本身成為現(xiàn)實(shí)(特別是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現(xiàn)實(shí))的完美、絕對(duì)的合法性話語,從而將藝術(shù)批評(píng)和創(chuàng)作帶入了一種分裂性、替代性和征服性的主體性立場(chǎng)(一種人類中心論,同時(shí)也是非人性化的立場(chǎng)),并引入了一種永遠(yuǎn)無法進(jìn)入冥想的、永遠(yuǎn)躁動(dòng)焦慮和充滿危機(jī)的藝術(shù)觀。”
他的“差意性”模型是:“任何類型都沒有自足準(zhǔn)則,或者說準(zhǔn)則不是建立在‘理、識(shí)和形’各方的自足性和獨(dú)立性基礎(chǔ)之上,而是建立在‘理非理’‘識(shí)非識(shí)’和‘形非形’的缺失性關(guān)系之中,這個(gè)關(guān)系就是筆者所說的‘不是’,而‘不是’的關(guān)系總和就是‘不是之是’,也就是差意性。”所以,高名潞進(jìn)一步說:“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筆者參考了非西方傳統(tǒng)藝術(shù)理論中某些‘非再現(xiàn)論’的文化資源,提出了意派論,從差意性出發(fā),消除分離的邊界,尊重‘互有’‘互存’的包容性,尋找一種擺脫極端的線性替代和鐘擺的對(duì)稱性的另類道路,以此面對(duì)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的各種終結(jié)論危機(jī),從而嘗試建樹一種新的思維角度及其理論體系。”
好了!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有了兩個(gè)中國(guó)產(chǎn)的概念工具:差意和意派,并且提供了意義完整的解釋模型。這是個(gè)了不起的理論成就!
首先,我對(duì)高名潞的這一主張堅(jiān)決支持。這是近幾十年來中國(guó)藝術(shù)學(xué)術(shù)理論建構(gòu)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不論是民國(guó)初期蔡元培的“美育說”,還是“五四”時(shí)期陳獨(dú)秀的“美術(shù)革命”以及政治實(shí)用性的目的引入現(xiàn)實(shí)主義,我們都只是“引入”和“應(yīng)用”,只有引入的理論和應(yīng)用的理論,即使到了20世紀(jì)“85新潮”之后,也沒有獨(dú)立的理論建構(gòu)和思考,仍然還是西方理論在中國(guó)的“引入”和“應(yīng)用”寫作。近年來此風(fēng)更甚,從法國(guó)的巴特、福柯、德里達(dá)、德勒茲,美國(guó)的詹明信、丹托再到德國(guó)的哈貝馬斯以及最近的朗西埃、阿甘本、巴迪歐諸人,把“引入”當(dāng)成學(xué)術(shù)成就,把“應(yīng)用”于中國(guó)藝術(shù)評(píng)論當(dāng)成發(fā)展方向和標(biāo)準(zhǔn),于此可見高名潞的理論建構(gòu)的重要性。
其次,對(duì)高名潞提出的“轉(zhuǎn)向”及“差意性”的“意派”觀點(diǎn)可以有各種不同意見。這與這個(gè)論點(diǎn)提出的意義是兩個(gè)問題。哪個(gè)新理論沒有問題!但更關(guān)鍵的問題是,我們自己有沒有去嘗試這種理論的建構(gòu),走出理論思考史的空白?高名潞所邁出的正是這樣的關(guān)鍵步驟。
讀高名潞的《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所闡釋的主旨,讓我想到《全球轉(zhuǎn)向的覺醒中的藝術(shù)史》的一個(gè)國(guó)際會(huì)議論文結(jié)集,其提出的主題是“地圖重繪:空間丨時(shí)間丨地方丨主題”。藝術(shù)史已經(jīng)到了全球開放的時(shí)代,西方、非西方,中心、邊緣等不應(yīng)再成為問題。因此新的原則便是“全球化的內(nèi)容是機(jī)會(huì)的分配即不同地方在不同的時(shí)間說著不同話的人群。不存在一個(gè)地方的來源,更不存在一個(gè)時(shí)間來源”。
在我看來,高名潞為“全球轉(zhuǎn)向的覺醒中的藝術(shù)史”提出了“中國(guó)的”一個(gè)系統(tǒng)的具有理論深度和思想高度的學(xué)術(shù)樣本。期待這一示范會(huì)引出更多的后繼者!
坦率地說,我們太迷信西方人的觀點(diǎn)了,而對(duì)其觀點(diǎn)到底有多少實(shí)質(zhì)性意義的質(zhì)詢幾乎總是缺失的。比如說,藝術(shù)批評(píng)史上三篇關(guān)于梵高的著名文章即可見一斑,即夏皮羅的《關(guān)于個(gè)人物品的靜物畫》、海德格爾的《藝術(shù)作品的本源》、德里達(dá)的《定位中的真理的還原》。從夏皮羅對(duì)海德格爾的梵高的鞋的靜物畫的史實(shí)考證看,海氏的“農(nóng)鞋”的“天”“地”“歸鄉(xiāng)”云云的天馬行空的論述可謂是離題,原作中既非農(nóng)鞋而且兩只都是左腳的鞋子。海德格爾之論不攻自破,但是中國(guó)的評(píng)論家們卻樂此不疲地引述,仿佛夏皮羅的批評(píng)從不存在。實(shí)際上,海德格爾說的就是他的“在”與“在者”的繪畫圖像版,與梵高之畫沒有多少關(guān)系,按他的哲學(xué)敘述方式,隨便換上哪個(gè)人哪一張關(guān)于鞋的畫都可以如此陳述。這樣的畫論有“畫論”價(jià)值嗎?至于德里達(dá)的《定位中的真理的還原》,更是虛無主義的哲學(xué)追問的文字游戲,所以意大利哲學(xué)家艾柯說他是專門弄這一套出來浪費(fèi)時(shí)間的。追問梵高為何會(huì)如此畫,設(shè)問海德格爾又為何如此這般,最后又討論夏皮羅的史實(shí)對(duì)海德格爾和梵高的語境之不同的設(shè)定,結(jié)論是各話自話。如此廢話連篇卻成了美術(shù)經(jīng)典文獻(xiàn),也應(yīng)是這個(gè)時(shí)代出奇的原創(chuàng)景觀了。
與此相比,高名潞的“差意論”的“意派”之說,至少在漢語言文化語境要精彩得多。它是建構(gòu)中國(guó)藝術(shù)理論的自覺性和自意識(shí)性的示范性工作。
三、“再現(xiàn)說”評(píng)述
這里需要討論的是高名潞作為全書核心概念,并看作為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本體動(dòng)因的“再現(xiàn)論”問題。據(jù)我的淺見,有諸多理論難點(diǎn)請(qǐng)教高名潞先生。
高名潞是用“再現(xiàn)論”設(shè)定他的關(guān)于“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的轉(zhuǎn)向。他劃分的三個(gè)部分的“再現(xiàn)論”:每一種都有一個(gè)相應(yīng)的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支撐。如作為“象征再現(xiàn)”的哲學(xué)轉(zhuǎn)向:正是啟蒙的哲學(xué)奠定了西方以再現(xiàn)為基礎(chǔ)的西方藝術(shù)史理論的全面基礎(chǔ)。美學(xué)的獨(dú)立和系統(tǒng)藝術(shù)史(或者批判藝術(shù)史)敘事的出現(xiàn),是這個(gè)再現(xiàn)論的直接結(jié)果。第二階段的“符號(hào)再現(xiàn)”的“語言轉(zhuǎn)向”:就是研究概念化的形式“如何超越模仿復(fù)制,從而更有效地、更真實(shí)地再現(xiàn)外部世界的學(xué)問”。因此,這里的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便是對(duì)圖像語言、象征語義的探討,如去圖像、超圖像、泛圖像等“再現(xiàn)”的概括。
對(duì)此,高名潞說:“如果用一句話去概括藝術(shù)再現(xiàn)論,那就是,藝術(shù)的本質(zhì)就是復(fù)制大腦意識(shí)和外部對(duì)象之間相互對(duì)應(yīng)的大腦形象模式。檢驗(yàn)這個(gè)模式合理性與否的理論就是再現(xiàn)認(rèn)識(shí)理論,它既可以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法論,也可以是藝術(shù)史敘事的方法論。”“這里的關(guān)鍵詞是‘對(duì)應(yīng)’。換言之,如果說藝術(shù)再現(xiàn)了什么,那就是再現(xiàn)了意識(shí)給外部世界規(guī)定的某種秩序。所以在藝術(shù)作品中,以及藝術(shù)史的敘事中,藝術(shù)作品的構(gòu)造要完整、完美地替代那個(gè)它所表達(dá)的意識(shí)秩序。”而“符合”“對(duì)應(yīng)”和“替代”等概念說的都是一回事,“即再現(xiàn)意味著完全對(duì)等”。
那么問題來了。第一個(gè)問題,按他的推論,“再現(xiàn)論”是不可避免的:視覺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不論是什么類似的,必然要以一個(gè)中介物“再現(xiàn)”精神理念、政治語境、女性權(quán)力、寫實(shí)理想、至上主義、概念主義等,乃至詞語與身份都是圍繞著“再現(xiàn)”某種思想、情感、理念等。“相似也是一種再現(xiàn),相似更是轉(zhuǎn)向再現(xiàn),再現(xiàn)之所以是再現(xiàn),在于和詞語的再現(xiàn)發(fā)生關(guān)系,而詞語的再現(xiàn),讓圖像的陳述自由空前地解除了限制,無限地?cái)U(kuò)展了。”那么,賦、比、興、“六法”“六書”是“再現(xiàn)”嗎?還是“再現(xiàn)”與“再現(xiàn)論”沒有關(guān)系?再如現(xiàn)代藝術(shù),沒有再現(xiàn)摹本,有的學(xué)者把它們與羅巴契夫斯基、鮑耶、黎曼的非歐幾何一樣的“人類性靈最富于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懷德海語)相比,它們依靠的是人類的純粹直覺和主觀想象的“依靠理性、而不是情感”。那么我們是不是據(jù)此也可以把非歐幾何或者非歐幾何式的繪畫當(dāng)成“再現(xiàn)”?當(dāng)然可以這樣稱謂,只不過沒有實(shí)際的意義。
不僅如此,從解構(gòu)主義的角度說,不僅不是再現(xiàn),而是堅(jiān)決反對(duì)再現(xiàn),走到“零度”狀態(tài)。羅蘭·巴特的說法很有代表性:古典作品中用詞語是為了“突然達(dá)到一個(gè)事先料想不到的高度而再現(xiàn)出某種經(jīng)歷的深度和差異性;它們按照優(yōu)雅的、修飾性的結(jié)構(gòu)要求,都排列在作品的表面。人們感到高興的是把這些詞語組合在一起的程式,而不是它們自身的力量和美”。“詞語從此僅僅是一張垂直的設(shè)計(jì)圖,它就像一塊石頭或一根柱子一樣插入由意義、想法和暫留形象組成的整體之中;它是站立著的符號(hào)”,被“引導(dǎo)到一種零的狀態(tài)”。現(xiàn)代藝術(shù)亦可作如是觀。硬把它們說成是“詞語再現(xiàn)”是沒有實(shí)質(zhì)意義的。
第二個(gè)問題,再現(xiàn)論成了哲學(xué)反映論的翻版,如同羅蒂的《哲學(xué)與自然之鏡》所說,維特根斯坦的前期《邏輯哲學(xué)論》試圖給“再現(xiàn)”式的反映論建構(gòu)一套語言邏輯模型,后期《哲學(xué)研究》則完全回到語言自身用法的哲學(xué)思考,論述不是“照鏡子”的語言性質(zhì)。語言至少有三部分,一部分對(duì)應(yīng)對(duì)象,一部分對(duì)應(yīng)情感及精神世界,還有一部分什么都不對(duì)應(yīng)的語詞自身;假如把這種創(chuàng)作和思考也說成是“再現(xiàn)”,那么結(jié)論就是,這個(gè)世界也就沒有不是這種“再現(xiàn)”的表達(dá)物品了。于是,“再現(xiàn)論”便成為無所不在的上帝;而作為一個(gè)學(xué)術(shù)的特稱判斷的“再現(xiàn)論”命題,便成為了全稱判斷;猶如說,地球上的物品是關(guān)于地球的再現(xiàn),然后劃分為物理的、化學(xué)的、歷史的,等等;如此的話,這個(gè)命題便沒有任何實(shí)質(zhì)意義了。
第三個(gè)問題,高名潞的“再現(xiàn)論”的物理的支撐理由是“中介”“媒介”,也就是說,所有的藝術(shù)觀念必須借助媒體、中介。這當(dāng)然也是自明的問題。但問題是,既然借助媒體、中介呈現(xiàn)的藝術(shù)觀念是“再現(xiàn)”,那么為什么西方的“再現(xiàn)論”到了中國(guó)藝術(shù)領(lǐng)域就失效了?這兒需要的理論解釋是:其一,中國(guó)藝術(shù)當(dāng)然也要媒介、中介,那么它是“再現(xiàn)論”的論域嗎?如不是,為什么?其二,推及高名潞的“藝術(shù)史轉(zhuǎn)向”的“差意性”之“意派”說,它是否也是“再現(xiàn)論”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如若是,它與中國(guó)藝術(shù)的一以貫之的“再現(xiàn)論”論域之外的學(xué)術(shù)邏輯是什么?
第四個(gè)問題,非要把任何一種思考方式都當(dāng)成反映論的“再現(xiàn)”,不論從方法上還是認(rèn)識(shí)上,都是無助于問題的聚焦的。比如下述表述方式,我認(rèn)為更有助于學(xué)術(shù)研究的具體思考和問題深入:“圖像學(xué)方法關(guān)注內(nèi)容,而形式主義凸現(xiàn)構(gòu)圖要素。藝術(shù)史尋求秩序,而社會(huì)學(xué)是要打破這個(gè)秩序。符號(hào)學(xué)過于結(jié)構(gòu)化的是把意義作為‘科學(xué)事實(shí)’來發(fā)現(xiàn),而解釋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們可能發(fā)現(xiàn)的、闡釋的、臨時(shí)的本質(zhì)。”美國(guó)的卡達(dá)爾.L.沃爾頓寫有一本《扮假作真的模仿》,討論各種藝術(shù)形式的模仿特征的“再現(xiàn)”,而這個(gè)“再現(xiàn)”不是反映論的,而是針對(duì)某種對(duì)象的,是各種藝術(shù)摸仿的“虛擬性”呈現(xiàn)出來的物質(zhì)特征。“Mimesis as make-believe”即如何“信以為真”的“再現(xiàn)”問題的探討,如小說是有文字情節(jié)的一本書,音樂展演和凝聚樂音光盤的聆聽,視覺藝術(shù)是一件可視物等;而“扮假作真”是實(shí)現(xiàn)“再現(xiàn)”的結(jié)果的根本法則。因此,他消解了席勒賦予“游戲沖動(dòng)”的本體論意義,把“扮假”看成是虛構(gòu),作為“專注于扮假作真”的一套理論模式。而藝術(shù)作品是有種種“描繪再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再現(xiàn)”,如“跨形態(tài)描繪再現(xiàn)”、言語“故事型敘述者”再現(xiàn)、非言語敘述再現(xiàn)等“扮假作真”類別。這里的“再現(xiàn)”,顯然迥異于高名潞的“再現(xiàn)論”,它是聚焦于“扮假作真”的具體方式上實(shí)現(xiàn)的效果的“信以為真”的目的。它不是關(guān)于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論和方法論,而是“信以為真”的一種“再現(xiàn)”手段,是一種單稱判斷命題。當(dāng)然還可以有“扮假即假”“扮假無真假”等的方法探討。尼爾森·古德曼的《藝術(shù)語言》把“再現(xiàn)”作為“再造的現(xiàn)實(shí)”一章中9個(gè)方法中的一種,即指謂、摹仿、透視、雕塑、虛構(gòu)、再現(xiàn)、創(chuàng)造寫實(shí)、描繪與描述。
再如奧爾巴赫的《摹仿論》中關(guān)于摹仿論的“再現(xiàn)”問題的研究也可與此對(duì)照。如他說“19世紀(jì)初在法國(guó)形成的現(xiàn)代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一種美學(xué)現(xiàn)象”,“對(duì)于后來文學(xué)摹仿生活的真實(shí)”比“當(dāng)時(shí)浪漫派所宣稱的高雅風(fēng)格與怪誕滑稽的混合更完美、更重要”;“司湯達(dá)和巴爾扎克將日常生活中的隨意性人物限制在當(dāng)時(shí)的環(huán)境之中,把他們作為嚴(yán)肅的、問題型的、甚至是悲劇性描述對(duì)象”,自此之后,“現(xiàn)代寫實(shí)主義順應(yīng)了我們不斷變化和更加寬廣的生活現(xiàn)實(shí),拓展了越來越多的表現(xiàn)形式”。該著便是用這一原則,以個(gè)案的方式,綜合歷史文獻(xiàn)、民間文學(xué)、宗教生活、語文學(xué)等,探討自古希臘荷馬以來的寫實(shí)主義的發(fā)展和不同時(shí)代的文學(xué)“摹仿”的“再現(xiàn)”樣本。
如關(guān)于《羅蘭之歌》這部法國(guó)最早的民族史詩,作者通過歷史文獻(xiàn)梳理、民間俗世理想、基督教精神的社會(huì)生成,把羅蘭塑造成“半宗教、半傳說式的想象”的人物,“這種想象總是將偉大帝王的出現(xiàn)與受苦受難的精神和力不從心的性格聯(lián)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說,在他的身上也有耶穌的影子”。再如宮廷小說,“愛情往往成為英雄創(chuàng)造業(yè)績(jī)的直接原因;當(dāng)行為完全沒有政治歷史方面的實(shí)際動(dòng)機(jī)之時(shí),就很接近虛構(gòu)了”,但卻因此使“愛情作為詩歌題材在文學(xué)中提高了地位”。
另外還有關(guān)于塞萬提斯的論述:“堂吉訶德的愚蠢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揭示;整部書是一部戲劇,在劇中,愚蠢在基礎(chǔ)良好的現(xiàn)實(shí)的映襯下變得十分可笑。”“他喜歡這個(gè)畫面,既因?yàn)樗世_紛,也因?yàn)槭汞偵导八龅降囊磺械哪欠N中立歡快。這是一種英雄的理想化的瘋傻,它為智慧和人性讓出了空間,他肯定也喜歡這些。但我覺得,若認(rèn)為這瘋傻具有象征性和悲劇性就牽強(qiáng)了。”關(guān)于席勒的《陰謀與愛情》中描寫米勒家庭的悲劇性、真實(shí)性和時(shí)代感的論述:“觸及到那個(gè)時(shí)代政治社會(huì)的深層,這似乎是通過個(gè)人命運(yùn)反映整個(gè)時(shí)代現(xiàn)實(shí)的首次嘗試。”這里的篇篇分析都精彩絕倫,我忍不住地多引了一些與大家分享。
在此,我們看到,作者要告訴我們的是:其一,是置于日常生活之基礎(chǔ)的“再現(xiàn)”的“摹仿”。應(yīng)該說,他的《摹仿論》全書都是按照這一原則,由一個(gè)個(gè)單項(xiàng)研究的內(nèi)容組織起來的。其二,這些作品是有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的,為什么會(huì)是這樣的對(duì)象而非其他,然后說,是怎樣讓這個(gè)被摹仿的對(duì)象加入了“主觀愿望”,最后回答這個(gè)主觀愿望的真實(shí)性、歷史性意義。其三,他的“摹仿論”,不是針對(duì)歐洲的所有文學(xué)的概括和評(píng)論,也就是說,不是說所有文學(xué)的摹仿的再現(xiàn),或者再現(xiàn)的摹仿,而僅只是針對(duì)“越來越小、越來越細(xì)”的遵循生活特征的理想主義或悲劇主義或者中立主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這一類別的摹仿。因此,這是一個(gè)由眾多個(gè)單稱判斷命題組成的“特稱判斷命題”。
注釋:
[1]施洛塞爾等著.維也納美術(shù)史學(xué)派[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113、119、126.
[2]潘諾夫斯基《圖像學(xué)研究: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藝術(shù)的人文主題》的“導(dǎo)言”中,有一個(gè)簡(jiǎn)明、清晰的表格,是他這一理論的基本公式。見潘諾夫斯基.圖像學(xué)研究: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藝術(shù)的人文主題[M].戚印平、范景中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1.
[3]曹意強(qiáng)主編.藝術(shù)史的視野[M].杭州: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7:391—400.
[4][6][8][9][10][13][14][15][16]高名潞.西方藝術(shù)史觀念[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556、300、304,320、206、70、217,68、142—143,123、567,569,92、64—65,129、203、206,6,395.
[5]〔美〕夏皮羅.現(xiàn)代藝術(shù):19世紀(jì)與20世紀(jì)[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256.
[7]洪再辛選編.海外中國(guó)畫研究文選[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2:93、371.
[11]Art History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Turn,Edited by Jill H.Casid and Aruba D'Souza,Yale,2014,pxii.
[12]關(guān)于德里達(dá)的這篇文章,沈語冰在夏皮羅《藝術(shù)的理論與哲學(xué)》的“譯后記”一文中有精辟論述。見〔美〕夏皮羅.藝術(shù)的理論與哲學(xué)[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6.
[17]〔美〕莫里斯·克萊因.西方文化中的數(shù)學(xué)[M].張祖貴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585.
[18]朱立元主編.二十世紀(jì)美學(xué)名著選(下冊(cè))[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88:402、403、404.
[19]〔英〕理查德·豪厄爾斯.視覺文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110.
[20]〔美〕卡達(dá)爾.L.沃爾頓.扮假作真的模仿[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495.
[21]〔美〕尼爾森·古德曼.藝術(shù)語言[M].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90.
[22][23][24]〔德〕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M].吳麟綬、周新建、高艷婷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653、654,117、166—167,411、426、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