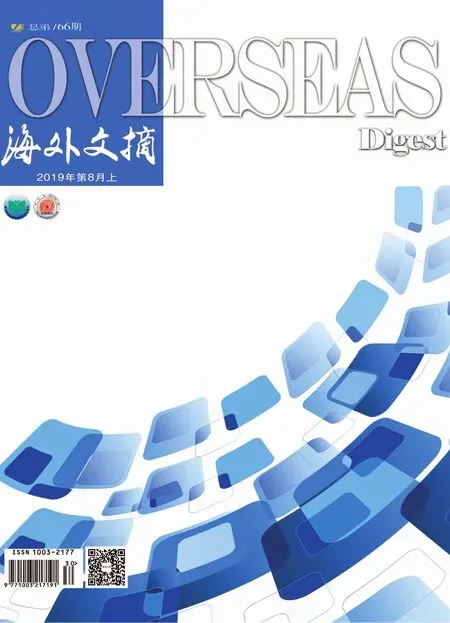追逐“漢江夢”
劉松
(漢江水利水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樞紐管理局),湖北武漢 430048)
1 我的夢想
我“至于學”后之于丹江口水庫調度,轉瞬已過知非之年。多少次言及經歷,唯我簡單而單一,即水庫調度單位,唯一之變化乃隨業務單位名稱而變化。其實,很早就有幾次改行的機會,因我“固執”而一直堅持至今,為的是圓一個夢想——親歷漢江流域變成中國式的“田納西”。
小時候,受我大伯的影響較大。大伯,一名鄉中學語文教師,經常給我講一些非常新奇的故事。小時候的我,這些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大伯最大的愛好就是愛看一份用自己微薄工資訂買的《參考消息》。每次到大伯家里,這份《參考消息》也成為我的最愛,以至于后來我無論走到哪里,也總喜歡買一份來看看。大伯講得最多就是“美國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先進,如何的發達、富裕”,經常鼓勵我“好好學習,長大后一定要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之人”。這些話至今在我的腦海里記憶猶新,以至于從學校畢業到丹江口水庫管理單位工作后,就經常與美國比較,特別是后來了解到美國的田納西河流開發利用情況后,就有了“漢江夢”。入職漢江集團公司(丹江口樞紐管理局),與丹江口工程、與漢江相伴,與“漢江人”同行,我想這個夢想也是“漢江人”的夢想。近年,我隨總部搬入武漢東西湖,常佇立漢口,聯想頗多。愿“漢江安瀾,經濟繁榮,水潤天下”,這就是我追逐的“漢江夢”。
“漢江夢”起于丹江口,落于漢江流域,甚或華北平原。“漢江夢”的實現,靠什么?主要靠“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當然還有相關工程及其流域水資源!歷史已經證明,還將繼續證明,丹江口樞紐工程一定會為實現“漢江夢”發揮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2 漢江之重要地位
談及“漢江夢”,就不能不提及漢江的重要地位。
漢江乃長江的最大支流,而丹江口樞紐則是漢江的骨干樞紐,既是重要的防洪工程,也是國家重要的供水與跨流域的調水工程,初期工程還發揮了重要的電力組網功能和能源基地作用。工程建設至今,帶動了漢江流域經濟多方面的發展,后期還將在供水和生態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漢江干流全長1577公里,發源于秦嶺南麓,干流流經陜西和湖北兩省,在武漢市注入長江;漢江流域面積15.9萬平方公里,覆蓋了陜西、湖北、河南、甘肅、四川和重慶等五省一市。漢江之于長江,僅為支流,然而其在歷史上占居重要地位,常與七大江河之長江、淮河、黃河并列,合稱“江淮河漢”。
漢江所處之位置獨特,北邊與黃河交界,東偏北與淮河相接,西邊與長江的另一支流嘉陵江為鄰,南邊為長江干流,乃漢江之目的地。漢江處于南北氣候過渡帶,具有多種氣候特征,有時與黃河之渭河支流具有相同的旱澇氣候特性;有時又有淮河的暴雨洪水特征;間或具有嘉陵江之天氣成因;當然其處于長江的中游,又常常呈現長江上中游或中下游的氣候與雨洪特點。
漢江與除長江外的其它六大水系好有一比。漢江之水量與黃河不相上下;流域面積,介于太湖和遼河流域之間;論及干流長度和水能理論蘊藏量,都高于淮河、海河、遼河、太湖流域。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漢江流域水利與經濟地位也極其重要。2017年湖北省25強縣市經濟,漢江流域范圍即占15個席位;同年湖北省有4個縣市進入全國百強行列,其中就有2個漢江流域內縣市入列;國家為解決中國日益復雜的水資源問題,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而漢江則成為全國唯一的流域性水資源管理試點,并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由國務院部署,水利部、國土資源部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水流產權確權試點方案》亦選擇了丹江口水庫作水流產權確權試點,并于2016年11月4日起施行。
可見,漢江地位之重要。
3 丹江口乃“防洪工程”
“漢江夢”起于丹江口,而丹江口工程則因防洪而建。因此,“防洪第一”是前提,不管是初期工程還是后期工程。歷史上,漢江是一條洪災多發、頻發的河流,干流河堤幾乎達到三年兩潰的程度,“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是對漢江下游的仙桃沔陽農村的真實寫照。
特別是漢江1935年洪水,是有記載以來的最大洪水,洪峰流量約50000立方米每秒,直接淹死8.7萬人;歷史調查洪水更是超過60000立方米每秒,達到61000立方米/秒(1583年6月),盡管其可靠性有待進一步考證。
為徹底根除漢江洪災,國家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仍決定修建丹江口水利樞紐。在長江水利委員會主持編制的《漢江干流綜合規劃報告》(以下簡稱“《漢流規》”)中稱丹江口水利樞紐為漢江的骨干防洪工程,即丹江口是一個重要的防洪工程。
雖然我國水利工程眾多,然而稱得上重要的防洪工程的卻不多。三峽是長江干流的主要防洪工程,其防洪庫容約221.5億立方米;其次就要數長江支流漢江丹江口工程了,其防洪庫容約為110.2億立方米,約為三峽水庫防洪庫容的一半;其它流域較大的防洪工程還有黃河小浪底水庫,其防洪庫容約38億立方米;松花江流域的尼爾基水庫,其防洪庫容23.68億立方米,等等。可見,長江支流漢江的丹江口水庫是全國不可多得的防洪工程,僅從防洪庫容的大小來講,僅次于三峽工程了,不可小覷。
“《漢流規》”明確,丹江口樞紐工程主要為解決漢江的洪水災害而興建。因此,漢江集團(丹江口管理局)等幾代管理領導人,都始終不忘初心,“堅持防洪第一,綜合利用為上”。據統計分析,截至2018年7月底,丹江口水利樞紐共攔蓄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92次,避免了12次下游民垸分蓄洪和34次杜家臺滯洪區分洪,減免損失達620億元,“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丹江口大壩加高工程完工后,丹江口水庫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至170米,庫容從174.5億立方米增加到290.5億立方米,增幅超過60%,漢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由20年一遇提高至百年一遇,工程必將發揮出更大的防洪減災效益。
4 初期工程丹江口電站歷史地位凸顯
“漢江夢”最初即靠丹江口樞紐巨大的發電效益得以實現的。防洪是樞紐的首要任務,是“漢江安瀾”的前提,而發電則是初期工程最大的興利效益,對漢江經濟繁榮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國家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仍決定修建丹江口水利樞紐,既看重其不可替代的防洪工程效益,同時看重了其巨大的發電效益。丹江口電站的建成,不僅發揮了其巨大的電力效益,促進了華中電網的形成,還帶動了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
4.1 促進華中電網形成
縱觀湖北電力工業發展歷程,丹江口電廠的建成,形成了220千伏跨省的華中電網,也是湖北省境內的第一個跨省的高壓電網。丹江口水電廠的建設奏響了湖北大型水電工程建設的凱歌,也鍛煉與造就了一大批水電工程建設的精英人才,為后來的黃龍灘、葛洲壩、隔河巖乃至三峽水電工程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2 發揮了重要的骨干電廠作用
1968年10月1日,丹江口水電廠首臺機組投產發電,1973年9月第六臺機組并網運行,完成了90萬千瓦的總裝機。這在70年代初期的中國已算為數不多的大型電站。對于當時缺電十分嚴重的湖北省來說,丹江口水電廠更是湖北省電網起支撐作用的骨干電廠。
由于當時“三陽”(襄陽、鄖陽、南陽)地區經濟不發達,丹江口水利樞紐管理局自身的工業還沒有起步,區域用電不多,因此,丹江口水電廠所發電量的80%以上遠距離、重負荷輸送至鄂東南的武漢地區和豫中的鄭州地區,極大地緩解了兩省(尤其是湖北省)用電緊張的矛盾,特別是直接向當時兩省重工業項目(武鋼一米七軋機和鄭州鋁廠)供電,為兩省的工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977年,湖北省電力局局長趙墨軒同志在沙市召開的全省電力工作會議上曾說:“我們要特別感謝丹江口,因為丹江口機組一開,全省就大放光明。”
由于丹江口庫容大、單機容量大、調節性能好,加之當時丹江口裝機容量在華中電網占比較大,因此丹江口水電廠就成為華中電網的主力調頻、調峰、事故備用的骨干電廠。丹江口水電廠在極其困難的運行條件下,顧全大局、服從調度,對電網的安全、穩定和優質供電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據統計,從1981年華中電網成立至1995年的15年時間里,丹江口水電廠累計發電594.18億千瓦時,其中調峰電量為259.57億千瓦時,調峰率為43.69%;又如1993年,機組開停1342次,平均每天開停3.68次,大大增加了機組的損耗和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丹江口電站還以相當多數量的旋轉備用容量或發出一定的無功功率支撐電網電壓等等,這些都是電廠為電網、為社會所做出的巨大的無私的貢獻。
因此,作為主力骨干電廠的地位,對電網的貢獻和所做出的犧牲在華中電網史上是不可磨滅的。
4.3 促進了丹江口直供區的形成及其經濟發展
1973年,在丹江口水電廠最后一臺機組投產發電、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全面建成之際,作為對庫區三縣(市)為丹江口工程建設所作貢獻和犧牲的補償,同時也作為開發性移民的嘗試,國家利用移民經費建設了專門的供電線路,直接向鄖縣、淅川和丹江口市等“直供區”供給廉價的電力、電量。據統計,庫區三縣(市)由丹江口水電廠獲得的總電量遠超過290億千瓦時,并從長期的低電價中獲得大量收益。若每千瓦時電量與電網綜合電價差僅按0.10元計算,三縣(市)將少支付電費29億元以上,這對三縣(市)經濟發展和庫區移民脫貧致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隨著直供區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直供區需求電量也快速增長,給予優惠電量不斷增長。1987年,向直供區供電6.5億千瓦時,而1996年則增加至14.24億千瓦時,2017年更增加至25.5億千瓦時,是30年前的4倍,其中2012年直供區用電量為歷年最大值36.85億千瓦時。
對于漢江集團來說,依托丹江口水利樞紐運行管理,堅持多種經營發展,規模不斷壯大,實力不斷提升,逐步形成了以水電、鋁業、電化、地產四個板塊為主的多元發展格局,成長為一個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集團,是國家首批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百戶試點企業之一。
從電站運行情況來看,華中電力系統形成后,也扭轉了丹江口水庫長期低水頭運行的不利局面,還通過與高校院所合作研究丹江口水庫的經濟運行規律,使得水庫運行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電站多年平均發電量達到了40億kW·h,超過了設計目標38.3億kW·h,充分發揮了丹江口的發電效能。應該說,2014年12月12日之前,是丹江口樞紐最好的發電時期,即“大發電”時期。
可見,初期工程丹江口電站歷史地位凸顯。
5 丹江口亦為供水工程
實際上,丹江口水庫一直以來,就是一個供水工程。
根據《漢流規》,丹江口樞紐作為開發漢江水資源的第一期工程,即丹江口初期工程,其首要任務是防洪,其次為發電、灌溉和航運;初期工程建成了陶岔和清泉溝兩座引水渠首,分別向河南引丹灌區和湖北引丹灌區提供灌溉用水,設計年均供水量15億立方米,設計灌溉面積360萬畝(河南灌區150萬畝、湖北灌區210萬畝)。初期的丹江口樞紐工程一直發揮著向鄂、豫兩省的供水任務;同時,由于丹江口水庫的建成與運用,給漢江沿江兩岸提供了一個穩定、豐沛的水量,極大地支持和促進了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多年來,湖北省的經濟總量分布中,漢江縣市占有較大比重即得到佐證。
為了徹底解決北方缺水的不利局面,毛澤東主席半個多世紀前就提出偉大構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為實現這個偉大構想,1959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編制的《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要點報告》中,即提出南水北調總體布局,中線工程從丹江口水庫引水,遠景從長江干流調水。2002年國務院批復并確定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體規劃調水方案,丹江口水庫作為中線一期工程的水源地,供水范圍主要是唐白河平原和黃淮海平原的中西部,供水區總面積約15.5萬平方千米,工程重點解決河南、河北、天津、北京4個省市,沿線20多座大中城市提供生活和生產用水,并兼顧沿線地區的生態環境和農業用水。
丹江口大壩加高后,供水即變為僅次于防洪的第二大水利任務,可實現向北方調水95億立方米的目標,即為中線南水北調一期工程。若能適時實現引江補漢工程,擴大向北方的調水量至130億立方米,即實現中線南水北調二期工程目標。
丹江口初期工程建成至今,已累計向湖北、河南兩省灌區供水超過396億立方米,灌溉面積4580萬多畝次。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陶岔渠首自通水以來,截至2018年10月底,已累計向北方供水182.008億立方米,工程惠及北京、天津、石家莊、鄭州等沿線19座大中城市,5310多萬人,北京市、河北省等地的地下水開采量逐步減少,水位均大幅回升,供水效益逐步顯現;2018年4~6月丹江口水庫還向中線受水區實施生態補水8.68億立方米,生態補水效益顯著。
可見,水庫供水效益巨大,而跨流域調水和生態補水效益也初步顯現。隨著北方供水規模的擴大,若實施引江補漢工程,北調水量即可達到130億,丹江口樞紐的供水效益將進一步增強。
6 丹江口樞紐功能正經歷調整
縱觀西方國家水利工程的發展脈絡和歷史發展趨勢,丹江口工程的運行管理將經歷三個重要時期,即“大發電、大供水及生態利用等三個時期”。
“大發電”時期:丹江口工程為“防洪工程”,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了巨大的發電效益,是丹江口樞紐所經歷的第一個階段,即大發電時期。具體來說,就是工程建成發電至2014年12月12日(中線南水北調通水之日),經歷時間最長,即46年有余。截至2014年12月12日,已累計發電約1700億千瓦時,這也是“《漢流規》”看重的最大興利效益之所在。巨大的發電效益支撐了華中電網的安全運行,富裕了庫區百姓,也帶來了顯著的環境與生態效益。
“大供水”時期:從丹江口最終規模工程蓄水驗收、正式通水之時,丹江口樞紐已真正具備了“供水與調水”的功能,即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亦即“大供水”時期。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南水北調工程的興建,丹江口樞紐工程已被推上風口浪尖之上,大有超過三峽工程的關注度。盡管工程建成后遇到來水五年(2012至2016年)連枯,但其供水量仍然穩步提升。壩址徑流量是一個水文事件,也是隨機事件,具有周期性變化,其多年平均值是很難改變的;唯一的變化就是人類活動的影響,但這方面的影響較小,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來減緩其影響的。因此,也許三、五年內,北調水量就將實現設計95億立方米的目標。到那時,樞紐的主要興利功能將得到全面調整,即進入第二個階段——“供水為主”的黃金時段。我想“大供水時期”至少持續20年,也許30年,這與國家總體經濟發展規劃安排及經濟實際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另外,我們應該清楚的是,不是某一年的供水量達到95億立方米就認為達到了設計目標,而應該是某一個連續年份里,如連續五年,或十年的多年平均北調水量達到95億立方米,才算是真正達到了設計目標。因此,根據設計,不同來水年份設計供水量的多少是不一樣的。根據設計,其供水系列年份中,調水最大年份的年調水量超過110億立方米;調水最小年份的調水量不低于40億立方米。
“生態利用”時期:“大供水”后,水庫運用將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生態利用階段。當然,“大供水”與“生態利用”可能還難以準確劃分,特別是“大供水”的后期,這主要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需求,也許很快,值得進一步觀察。
當前漢江集團具有前瞻性的提出“生態優先”的口號,將為水庫逐步向第三階段過渡打下良好的基礎。相信到了那時,生態的發展將把丹江口水庫的運行管理推向一個更高的地位,即一個全新的鼎盛發展時代。到那時,滿足生態的要求將擺在一個重要的地位,水庫將以滿足生態為前提,其水利任務將會變成:防洪、生態、供水、航運與發電。五者的關系將是:防洪仍然是首要任務,這是其所處的的地位所決定的,沒有防洪的安全,就無法言及其它效益的發揮;生態將上升到第二位,當前國家機構調整后新設生態環境部就是明確的信號;供水任務將退居第三位,但作用仍不可小覷;航運的地位將可能提到發電之前,而發電的地位將再次下降,這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因此,丹江口水利樞紐將“因防洪而建、因發電而興、因供水而旺、因生態而盛”。丹江口一定會因生態需求的調度運用而達到鼎盛。我們應該順勢而為,積極促進工程功能得到順利調整,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7 續寫新輝煌,追逐“漢江夢”
丹江口樞紐自1958年開工至今已有60年,自1973年建成至今已有45年了。應該說,歷經幾代人的建設和管理,樞紐已較好的發揮了其巨大的綜合利用效益。那么,在后續的時期里如何發揮樞紐更大的效益,這是擺在我們“漢江人”面前的重要任務。但經過40多年的運行管理,我們有理由、有信心、有能力續寫新的輝煌。
7.1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走進漢江集團武漢總部,迎面大屏上顯示著“防洪第一、供水為主、生態優先”的12個大字。這是“漢江人”的大局觀、“漢江人”的使命,也是“漢江人”的驕傲,更是“漢江人”續寫樞紐新輝煌的路線圖。
“防洪第一”不是口號,應長期遵循。我國水庫垮壩事件中,“75.8”事件令人記憶猶新。1975年8月8日,一場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在內的兩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和兩個滯洪區在短短數小時內相繼垮壩潰決,使河南駐馬店地區猝然間溝壑橫溢、頓成澤國,數以萬計的人失去了生命。洪水過后,一位長期居住板橋水庫附近農民接受采訪說到,“當時我心里有這么一個概念,水庫庫容這么滿,一旦汛期來了如何辦?”當記者追問為何滿庫運行時,這位農民道出了原因,即前一年滿庫發電養魚收益不錯。可見侵占防洪庫容,會釀成大災。
丹江口大壩建成46年來,丹江口樞紐管理局(漢江集團)精心管理維護著丹江口水利樞紐,認真履行防汛職責,真正做到“防洪第一”,經受住了歷次大洪水考驗,使得漢江中下游居民長年安居樂業,一片欣欣向榮,特別是下游的仙桃市由過去“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變成了如今湖北省25強縣市經濟的前列。
“供水為主”是權衡樞紐的供水、發電與航運任務的必然。在興利中,供水、發電、航運三者之間,應以供水為主,發電退居次要地位。應該說,現在的供水是一個大的“供水”概念,不僅要滿足北方調水的要求,更要滿足漢江中下游和清泉溝的供水要求,特別是不能以犧牲漢江中下游和清泉溝引水要求來滿足北調用水的要求。對此,《丹江口水利樞紐調度規程》有了明確規定:“在確保樞紐工程安全的前提下,以滿足漢江中下游、清泉溝和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供水為目標”、“供水調度應統籌協調水源區、受水區和漢江中下游用水,不損害水源區原有的用水利益”。因此,“供水為主”就是要在設計標準內滿足水庫三大口門的供水要求,而且漢江中下游和清泉溝原有的用水利益必須得到優先滿足。
“生態優先”是新時代的新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系統治水提出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治水思路,對推進中華民族治水興水大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總的來講,一是要發揮好水資源的最大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二是要堅持量水而行、因水制宜,強化水資源環境剛性約束;三是要統籌自然生態各種要素,協調解決水資源問題;四是要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協同作用。
因此,漢江水資源的綜合利用是國家在“空間均衡、系統治理”的具體體現。從這個方面來講,丹江口水庫從“大供水”到“生態利用”的過度也許更快。
7.2 著眼當下,探索樞紐科學控制運用之路
當前水利部對治水的主要矛盾變化做出準確判斷:“從人民除水害興水利的需求與水利工程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對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的需求與水利行業監管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因此,丹江口水利樞紐的運行管理的主要任務或重點工作也許會有所改變,我認為關鍵在“安全”二字。這里的“安全”不只是工程安全,是一個廣義的安全,是“大安全觀”,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維護電網運行安全、航運及生態安全等整體協調平衡的安全觀。
“防洪安全”是丹江口大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丹江口立壩之基,而且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傾國力來建設這座工程。因此,防洪安全始終擺在第一位。當然工程本身的安全是所有水利任務的基礎和前提。
“供水安全”是丹江口加高大壩的根本考慮,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是治水方針中解決“空間均衡”的必然要求。因此,供水安全是重中之重。
電站和電網是一個整體,是相輔相成的,“維護電網安全運行”是國家電網的根本要求。盡管發電擺在第三的位置,但作為電網大容量的水電站,應該創造條件維護好電網的安全運行。只有電網安全運行,電站才有發電效益。反之,電站的安全運行又是電網安全穩定運行的基礎。因此,應在保障“防洪、供水安全的前提下”維護電網安全穩定運行。
“生態安全”,現在已越來越被重視,將來還有可能上升至僅次于防洪的重要地位;而“航運安全”,則要求漢江中下游必須維持一定的水位流量,這又與漢江水電站梯級聯調關系重大。
上述“安全”目標,實際上彼此是存在矛盾的。如過分追求防洪安全,有可能出現較多棄水而不能保證供水安全;反過來,為保證供水安全,采取高庫水位運行,又會侵占水庫防洪庫容而置防洪于不安全的境地;供水安全與維護電網安全,生態安全要求與其他方面安全要求也不盡一致。因此,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滿足各方需求、多目標均衡的安全觀。
那么如何達到“安全”的目標呢?
一要再認識。防洪與興利有矛盾,但不能把防洪與興利的矛盾尖銳對立起來,應追求合理的平衡;供水與發電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應有機協調統一;航運和生態與供水也可達到協調與平衡等。這幾對矛盾,不同時期的有不同的要求,可力求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要加強協調。保證防洪、供水、發電及生態安全都是通過丹江口樞紐工程與其關聯工程和有關的單位、部門來實現的。因此,盡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三要繼續加強研究。盡管以前已投入了大量研究資金,但仍要繼續加強有關方面的研究,如水庫流域來水規律的研究,調度控制運用方面的研究,管理機制和法規方面的研究,人們對水需求變化以及信息化需求等方面的研究等等;特別是應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對漢江流域水庫聯合調度研究、水庫汛期運行水位控制運用研究、各水利任務之間風險控制與轉換方面的研究、水生態保護等方面的進行深入研究。
四要繼續加強信息化建設。丹江口樞紐是國家重點水利工程,國之重器,涉及面廣,責任重大,應做好樞紐管理方面信息化的建設,即應建設一套集雨情、水情、工情于一體的綜合調度管理信息化系統。當然,這套系統,既包含監測漢江的水量信息,也包含其水質信息;工情信息系統既包含丹江口工程的工情,也包含陶岔和清泉溝渠首工程信息等。
因此,追求一個滿足各方需求、多目標均衡的安全,上述幾個方面缺一不可。
7.3 著眼未來,做好其它調水工程的相關工作
“引江補漢”、“引漢濟渭”、“鄂北水資源配置工程”等都是與漢江緊密關聯的調水工程。其中,“引江補漢”工程是優化全國南北水資源配置、保障漢江中下游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舉措,長江委正在著手“引江補漢”的前期研究工作。由于引水路線的不同,從小范圍來說,對漢江集團的長期發展影響巨大;從高站位來講,將是漢江“水潤天下”大展宏圖的好機會。
從長江引水到漢江按引水到丹江口大壩以上干支流和大壩以下河段分為兩類,分別簡稱為“壩上方案”和“壩下方案”。從取水點和引水路線來講,有大寧河調水、神農溪引江、小江調水、香溪河引江長隧洞換水、龍潭溪調水、引江濟漢提水至王甫洲、引嘉補漢方案等多條路線、多類方案。但都可簡單歸結為壩上方案和壩下方案。
推薦“壩下方案”的,多認為丹江口水庫原有水量盡可能的實現北調,水質有保證,且工程后期運行維護費用較低。但仍然存在三個較大的不利因素:一是調水量依賴于天然徑流;二是不能充分發揮丹江口多年調節的性能;三是特枯年份僅能北調30至40億立方米水量。
當然,壩下方案的不利方面就是壩上方案的優勢。就當前國家對環境保護重視程度而言,壩上方案更具優勢,應該正確引導,做好前期工作,以期充分發揮水庫的多年調節性能。
7.4 憧憬未來,水潤天下
中線南水北調、鄂北調水(包括清泉溝引水)、引江濟漢、引漢濟渭、引江補漢等一串串重大的調(引)水工程,都與漢江緊密相聯,足見漢江之重要。正因為這么多工程的綜合運用,才使得漢江流域的水資源潤澤的地區越來越廣,惠及的人口越來越多。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自2014年12月12日正式向北方調水,至2018年10月底,已完成調水182.008億立方米,惠及沿線19座大中城市,供水覆蓋面達到15.5萬平方千米,5300多萬居民喝上了南水北調的水。
引漢濟渭工程總調水規模的15億立方米,預計2019年通水,將惠及總計2348萬人的生活及工業用水,同時將歸還原被大量擠占的300至500萬畝耕地的農用水。此外,可有效改變關中超采地下水、擠占生態水的狀況,實現地下水采補平衡,防止城市環境地質災害等。
引江濟漢工程于2014年9月建成通水以來,截至2018年11月19日8時,累計調水141.13億立方米,其中向漢江補水117.39億立方米,向長湖、東荊河補水19.39億立方米,相當于置換了約130多億的漢江水量調往北方。
鄂北調水工程自丹江口水庫清泉溝取水,自西北向東南橫穿鄂北崗地,沿途經過襄陽市的老河口市、襄州區和棗陽市,及隨州市和孝感市部分地區,是從根本上解決鄂北地區干旱缺水問題的重大戰略民生工程,設計供水人口482萬人,灌溉面積363.5萬畝。
考慮到漢江流域內以及調水惠及的漢水流域外區域,漢江流域水資源將惠及全國1.2至1.3億人口,即漢水流域不到2%的國土面積,而其水資源惠及的人口則占到近10%,分布于甘肅、陜西、四川、重慶、湖北、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共六省三市,真正實現了“水潤天下”。
8 結語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這是唐代詩人王維的《漢江臨泛》。如果王維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登上丹江口大壩遠眺,行走于當今的漢水流域及水流惠及之地,不知有何感慨!
漢江丹江口樞紐自1958年開工至今已六十載,各方面的效益已經盡顯。再過十年、二十年甚或更長時間,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景!成為“漢江人”,是我們的幸運!生活在新時代,是我們的幸福!“漢江夢”始終是我們“漢江人”永遠不變的追求:愿“漢江安瀾,經濟繁榮,水潤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