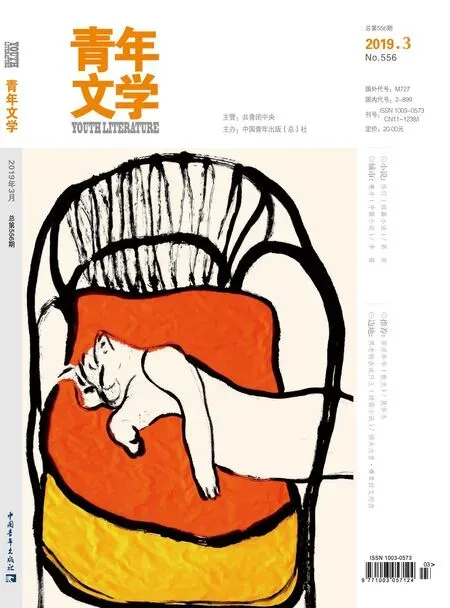走向晴明和開闊?
——評蔡東的《伶仃》
2019-11-13 14:59:30
青年文學
2019年3期
關鍵詞:小說
這些年身陷俗務,疏于寫文章,閱讀習慣雖一直保持著,但很少遇見引發情感共振的文字,也沒有提筆應和的愿望。這次讀到蔡東的短篇小說《伶仃》,一時心里卻有很多話想表達出來。“黃昏的時候,衛巧蓉走進一片水杉林。通往樹林深處的小路逐漸變細,青苔從樹下蔓延到路邊。”靈秀的文字,靜謐的氣息,悄悄地把讀者從塵俗的空間帶進小說的情境。工作一天后讀到這樣的文字讓我覺得很享受,心很快靜了下來。
先不細談小說迷人的氣息,首先從故事層面上說,我的猜測落空了,這落空卻很美妙。我對徐季有諸多猜想,讀完了再回過頭來思考作者的寫法,發現自己的猜想難免落俗,無論出軌者、藝術男的猜測,還是為他離群索居找到的各種現實理由,都不如小說現在的處理方式好。不僅是技法的模糊虛寫,技法什么的并不稀奇,我讀出來的,是作者對人和人世的寬宥與理解。她理解某個平凡男人決意從世界上消失的行為,甚至她認為沒有理由也可以,這個理解當然不容易,想到這一層,為作者捏了一把汗,但她的身姿實在輕靈,悄然無聲,群山已過。
最想說的是衛巧蓉這個飽含新質的人物,也因此,我愿意把《伶仃》當作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女性主義文本。從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到杰羅姆·魏德曼的《父親坐在黑暗中》再到霍桑的《威克菲爾德》,我們已見過太多黑暗里枯坐或干脆逃走的父親,而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更用較長的篇幅去呈現男性藝術家奇異精彩的后半生。……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