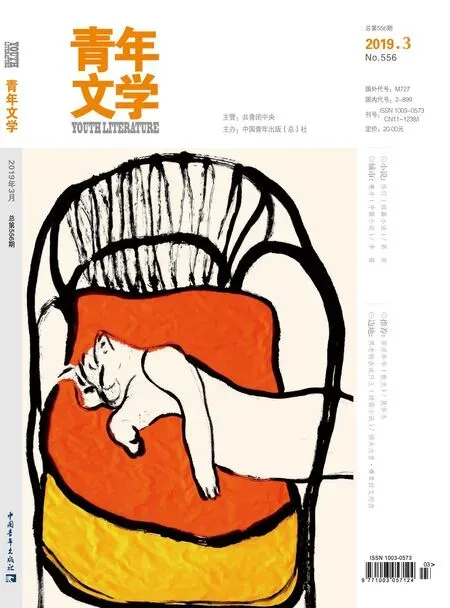西北偏北
2019-11-13 14:59:30
青年文學
2019年3期
一
上星期在祁連山旅行時接到湖南詩人譚克修的電話,從定西地震扯到匈奴、回紇與月氏國,最后準備掛電話時,他提起一件舊事,說我答應的一篇文章老沒有交稿,我們又從六月的兩湖詩會說起,岳麓山、吹香亭、湘江水以及詩歌的地方性等等話題,不知不覺陽光已經從祁連山南邊轉到了北邊。冷龍嶺的主峰冰川矗立,夕陽映照下閃著金粉般的色彩。我有點恍惚,此刻身在塞外,冷風吹過山谷,白云在山腰緩緩移動,還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野花在腳下瘋狂地生長著。可是關于詩歌,我還能說些什么呢?
我每每遇到這樣的問題時就有些遲疑。詩到底是怎么樣的,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巨大的難題。這難題極具誘惑力,讓我在每一首詩歌的開始和結尾都徘徊不定。說實話,我不是一個在藝術追求上堅定不移的人,也不是一個對自己的寫作信心滿滿的人。或者說,我喜歡的那種詩歌狀態,是模糊的,散發的,有著隨時變幻的可能性。這或許是我的人生觀。人事無常,人世無常,我們走在路上,哪里有什么目標和終點。
一九八九年冬天,我來過一次西北。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從武漢去甘肅沒有直抵的火車,我和幾個朋友先坐上去西安的火車,然后再轉乘從西安到蘭州的火車,一行四人的目的是陪著其中一個郭姓朋友去蘭州談戀愛。
上火車的前夜,幾個人在漢口吉慶街后的泰珍火鍋吃飯,張濤的家就在黃石路榮寶齋的樓上,他父親請客,席間叮囑我們說,去西北要注意安全,不要和回族人發生爭斗,不要在回族餐廳隨意喝酒,特別是,不能提到豬肉這個字眼。……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