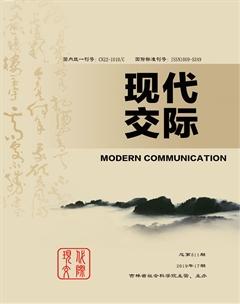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探析
夏恒霞
摘要: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勵下,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工作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其外宣翻譯卻存在不足之處。通過闡述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重要性,描述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不足的現狀,探討不足的原因、探究其翻譯策略,并提出在政府主導下使整個西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宣傳統一、規范、合理的具體建議。
關鍵詞: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17—0094—0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10月17日頒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簡稱《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給予了明確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
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最具代表性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國辦發〔2005〕18號)。《意見》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間”。[2]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統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以及禮儀和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其文字介紹涉及民俗、建筑、宗教、手工技藝、文學、歷史等。
自2005年國務院頒布《意見》,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上日程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并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當中。作為文化之都,西安市政府比較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在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業績。比如,2008年,“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在西安市群眾藝術館掛牌成立。中心建立了1000多平方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廳,收集展品4000多件,常年對群眾免費開放。2014年,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建立,并命名38名第二批“市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其中6人入選省級名錄。自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以來,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申報“非遺”的熱潮。截至2017年年底,陜西省已獲批74項國家級與520項省級非遺項目,其中,西安鼓樂、陜西剪紙、華縣皮影戲3個項目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名錄”。[3]
毋庸置疑,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開發、利用取得了一定成績。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經典文化廣為流傳,讓更多的人了解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傳統文化。在我國提倡“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要想讓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世人所熟知,必須加強其對外翻譯宣傳。
對于西安這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來說,在創建國際化大都市的背景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翻譯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環節。如何做好我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宣傳,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探討的問題。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重要性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精髓,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宣傳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譯介能夠讓更多外國人進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一些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甚至能夠在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第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譯介對保護和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有著重要意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特點鮮明,因此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譯介能夠促進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借鑒,使世界各民族文化百花齊放。
第三,西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極其豐富,是西安本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中,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的背景下,準確無誤地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翻譯宣傳不僅能促進其自身的傳承與發展,更將有益于西安市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有益于提升西安市的國際知名度,對于西安市旅游、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現狀分析
在“一帶一路”大背景下,西安市正大力提倡對外文化交流,然而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翻譯不足,沒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無論是從譯文質量還是傳播效果來看,尚不盡如人意。筆者專門選擇西安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極具代表性的民間剪紙藝術進行了研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剪紙藝術是一種文化形式,它所展現出來的民間藝人們高超的手工技藝令人嘆為觀止;另一方面,剪紙也是一種文化的載體,剪紙的內容包羅萬象,承載著博大精深的中華特色文化。再加上剪紙這種工藝品攜帶方便,易于對外傳播。包裝精美的剪紙,往往是饋贈外國友人的不二選擇。然而,筆者所接觸的民間藝術剪紙的英文譯文可讀性較差,誤譯、錯譯現象嚴重,遠不能達到預期的翻譯傳播效力。剪紙藝術的外宣尚且如此,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同樣堪憂。
總的來說,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目前西安市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翻譯還沒有形成規模,還沒有統一、規范的管理
多數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翻譯活動屬于個人行為,因此,市面上能看到的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稱、術語的翻譯不統一。另外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缺少官方權威的英文介紹,雖然部分旅游網站和旅游宣傳手冊上有一些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英文介紹,但是其譯文質量不高。筆者仔細閱讀了英漢對照版的《中國西安》,這是一本由西安市政府研究室和西安市規劃局聯合推出的全面介紹西安這座世界歷史文化名城的書。筆者發現書里對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簡單的介紹,但是其英文譯文質量有待提高,且有些術語的翻譯與其他出處的翻譯不一致。據西安市規劃局的工作人員透露,一般英文宣傳資料都是由翻譯公司來翻譯,然后找專家校對。即使這樣,仍差強人意。
2.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英文翻譯的幾個突出問題
筆者仔細研究了現有的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英文譯文,發現譯文里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突出問題:有些譯文沒有譯出原文隱含信息,造成翻譯信息不對等;有些譯文對于文化專有項處理不當,常見錯譯、漏譯等現象;有些譯者欠缺對中英思維差異的了解,忽視目的語讀者對源語文化的接受程度,大量使用音譯法,造成譯文可讀性差,外宣效果不佳。
三、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現狀的原因分析
經過調研,筆者發現造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由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特點決定的
從《公約》和《意見》的定義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我們慣稱的民間文化基本一致。我們慣稱的民間文化,既包括《公約》中所指稱的‘非物質這層含義,又強調其‘民間的性質,亦即在民眾中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世代相傳,歷史上通常不被官方或上層文化所承認或重視的文化”。[4]臧學運劉錦豫(2017)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內容豐富,歷史悠久,群眾基礎深厚,但是因為它的“民間屬性”,往往被看成“下里巴人”,低等、卑賤甚至可有可無,自生自滅。因此,它最容易被人忽視,被人歧視,甚至遭到破壞。
2.政府重視不夠,資金扶持不足
雖然西安市政府比較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但是,目前政府的主要資金扶持放在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開發,以及對現有資料的收集整理上,在對外宣傳這方面還沒有專項資金的投入。
3.缺乏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專業人員
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要從事這項工作,不僅對譯者的中英文語言水平和翻譯技巧有嚴格的要求,而且譯者必須把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并把文化信息準確地傳達給目的語群體。然而目前,真正能夠勝任文化翻譯工作的人員很有限。
4.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研究不夠
筆者在中國知網主題欄輸入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進行模糊搜索,獲取的相關論文只有二十幾篇。而且,這些研究都屬于個人行為,沒有形成規模,對改變某個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狀況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四、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策略探析
在譯者具備了一定的語言水平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的前提下,想要充分再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精確地傳達其文化內涵,還需要一定的翻譯策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策略這個方面,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比如有的學者認為,在外宣翻譯中應首先考慮受眾或目標讀者的感受,建議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筆者認為,在翻譯時應盡可能地采用異化的翻譯方法,這樣才能體現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性和唯一性。而且,具有異化特質的譯文更能激起西方讀者的好奇心。
此外,在解決實際翻譯問題時,翻譯策略的選擇應該是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源語特征,有針對性地解決主要難題。陳芳蓉(2011)歸納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翻譯難點有以下三個:民族特色鮮明的非遺名稱翻譯;文化專有項的翻譯;漢語意合到英語形合的轉換。
針對這三大難題,以下是可供參考的翻譯策略:
一是本著文化交流又不失源語文化本真的目的,民族特色鮮明的非遺名稱英譯可采用以下三種方法:直譯/直譯加音譯、音譯加解釋、音譯加類別詞(陳芳蓉,2011)。
二是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文化專有項的翻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音譯加文內解釋。或者選用譯文讀者較為熟悉的另一文化專有項來進行翻譯,再或者也可選用非文化專有項來翻譯文化專有項。
三是對于漢語意合到英語形合的轉換,重點在于理解英漢兩種語言的不同表達習慣,以及在句法上的不同體現。漢語重意合,不注重句法結構形式,而英語注重邏輯關系及句法結構,譯者在翻譯的時候就要準確理解源語的內在邏輯關系,用符合英語習慣的表達形式再現源語的信息。
五、改善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現狀的建議
1.發揮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工作的主導作用
通過查閱相關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資料,筆者發現,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比較成功的國家,盡管各國的國情、文化背景不一樣,所采取的保護措施也不盡一致,但無論是日本、韓國的亞洲模式,還是意大利、法國、英國的歐洲模式,無一不都是采取政府主導的模式(周志勇,2007)。
事實上,我國政府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在歷史上,各朝各代的政府都曾擔當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重任。近代,在各個發展階段,我國政府都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舉措,并卓有成效(鄢秀娟,2017)。事實證明,政府發揮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導作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政府部門應發揮主導作用,負責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工作的統籌規劃,從政策、資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給予相關部門大力支持;加大宣傳力度,培養市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的意識;鼓勵專家、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深入研究,利用各種資源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翻譯研討活動,探討并最終建立一套適合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統一標準。
2.成立專門的翻譯機構
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材料實質上是一種文化載體,其英譯的質量直接影響到文化輸出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因此,應該由政府主導,成立專門的翻譯機構,進行分工合作,部分人員負責修訂現有的英文翻譯資料,部分人員從事具體翻譯工作以及譯文的審校,在此基礎上,組織專門人員進行資料的編寫、出版,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準確無誤、有效地進行對外傳播。
3.提高專業翻譯人員的素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外宣翻譯中的譯者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是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的關鍵因素。翻譯人員的專業素質直接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的質量和效果,因此,專門翻譯機構應嚴格把關,吸納高水平的翻譯人才。可以從各高校的翻譯專業畢業生中擇優錄用,進行專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學習,進行專業的翻譯技巧培訓,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質量。
4.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翻譯語料庫的建設
解決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使整個西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宣傳統一、規范、合理,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規范的翻譯語料庫。據筆者了解,西安市已于2014年建立了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這為翻譯語料庫的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政府應支持專門翻譯機構,組織專業翻譯人員在數據庫基礎上進行翻譯整理,建立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翻譯語料庫。
六、結語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我國“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下,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有意之舉,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翻譯是特色文化對外輸出的關鍵環節。鑒于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的現狀,本文主要探究了其外宣翻譯不足的原因、探討了其翻譯策略,并提出了在政府主導下使整個西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宣傳統一、規范、合理的具體建議。做好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主要在于觀念的轉變和政府的政策支持。重視和解決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不足的問題,將有望帶動整個陜西省甚至全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工作邁上一個新的臺階。我們應該努力在對外文化交流傳播中發揮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優勢,將西安推向更廣闊的世界舞臺。
參考文獻:
[1]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56.
[2]王鶴云.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機制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3]第五批省級非遺秦腔代表性傳承人獲授牌[EB/OL].陜西省人民政府,2017-06-11.http://www.Shaanxi.gov.cn.
[4]劉錫誠.關于民間信仰和神秘思維的問題——兼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問題[C]//民間信仰與民俗生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5]臧學運,劉錦豫.外宣資料譯介策略視域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J].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17,32(3):128—132.
[6]陳芳蓉.文化多樣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譯介[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8(3):64—69.
[7]陳芳蓉.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英譯的難點與對策[J].中國科技翻譯,2011,24(2):41—44.
[8]周志勇.論政府主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D].湖南大學,2015.
[9]鄢秀娟.政府主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對策[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8(5):77—80.
[10]高昂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宣翻譯與國際傳播現狀與策略[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2019,(42):42—47.
[11]田亞亞.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文本中文化專有項英譯探析[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8(7):120—123.
[12]翁敏雅.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調查與對策研究[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8,38(2):66—68.
[13]王金輝.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現狀及策略研究[J].河北企業,2016(4):86—87.
[14]王愛支.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調查研究[J].鄂州大學學報,2017,24(3):68—69.
責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