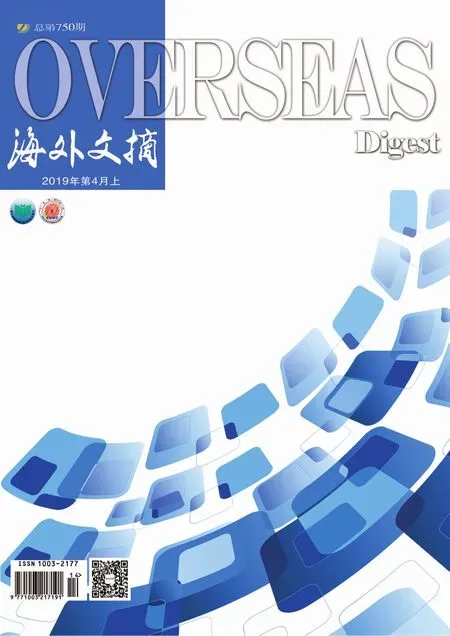淺析1985年“彩虹勇士號”事件
——以環保理念與國家利益的視角
郭家書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1)
1 事件背景與過程
1985年,法國秘密安全局在水下布置的兩枚炸彈炸沉了綠色和平組織的“彩虹勇士號”輪并造成了一名荷蘭籍攝影師死亡。這一事件使得法國在南太平洋的核試驗又一次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自1966年起,法國有報道的在南太平洋領地穆魯羅瓦島進行的核試驗就有近100起。70年代起,反核運動在這一地區盛行,法國政府也因其堅持進行核試驗的立場而與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處于緊張關系之中。此外,法國政府與綠色和平的矛盾也由來已久。早在1972年,綠色和平就曾經派出過船只在穆魯羅瓦島水域進行抗議活動,并遭到法國海軍的阻撓。在法國穆魯羅瓦島核試驗地帶,綠色和平的維加斯號甚至被法軍突擊隊登船,船長麥克塔加特被打入院,一只眼睛險些失明。在綠色和平的頻繁抗議和國際輿論壓力下,法國政府最終讓步,于1974年宣布停止在南太平洋的大氣核試驗。
1985年,綠色和平又準備派出“彩虹勇士號”前往這一海域,抗議法國預定于秋季進行的核試驗。彩虹勇士號于7月3日到達新西蘭的奧克蘭港,三日后便被法國特工炸毀,此事在當時并未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但兩天后,新西蘭警方拘捕了持瑞士假護照的一對“夫婦”。7月26日,新西蘭警方又發出了對與此案有關的“盧維亞芬”號帆船上的三名船員的逮捕令。迫于新西蘭與國內輿論壓力,密特朗總統于8月8日要求法比尤斯總理對這一件事進行調查,27日法總理宣布要求國防部長糾正國外安全總局工作中的嚴重失職情況。但事情遠未能平息,多家報紙披露此事系法國國外安全局特工受上級指使所為。有關負責人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也使得政府日漸陷于被動。反對派利用媒體煽動民意,要求查清真相并公之于眾,執政黨人也覺得事情拖下去帶來的政治后果不堪設想。
在此背景下,密特朗于9月19日下令更換外國外安全總局局長,次日國防部長埃爾尼提出辭職。22日,法比尤斯總理正式承認“彩虹勇士號”是國外安全總局的人所炸。最終,法國和新西蘭就奧克蘭爆炸案達成協議,由法國總統向綠色和平組織正式道歉并支付了700萬美金的賠款,新西蘭將兩名法國特工押送到法國南太平洋軍事基地服役。
縱觀1966年到1985年,南太平洋反核呼聲不斷,綠色和平抗議頻繁、步步緊逼,法國政府的傾向也從一開始的部分讓步到最后態度堅決,并最終制造出炸船事件。不可否認,1985年的“彩虹勇士號”事件對法國政府造成了巨大影響,有的反對派人士甚至將其稱為“法國的水門事件”。它使得法國政府十分被動,不僅法國的形象和聲譽在全世界遭到了損害,其與新西蘭等太平洋國家的關系也進一步惡化,南太平洋的反核浪潮也隨之日趨高漲。這不禁使人疑惑,在南太平洋的緊張形勢下,明知道可能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又有悖于西方價值觀甚至違背了法律,法國政府為什么還要默許情報部門使用炸船這樣強硬的手段?1985年的“彩虹勇士號事件”又緣何發生?筆者希望從環保理念與國家利益兩大要素的沖突角度來分析。
2 環保潮流的興起
進入20世紀,環境問題已經在事實上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現實威脅了。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戰爭、核試驗、核軍備競賽不僅浪費資源,更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1962年,《寂靜的春天》一書的發表,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20世紀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首次提出了全球人口、工業的快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生態學的普及、民眾環境意識的提高,以及波瀾壯闊的環境保護運動都對國家執政者產生了很大的壓力。為了緩解這種壓力,順應時代潮流,西方國家首先出現了一股環保浪潮,不管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先后被迫高舉環保旗幟。1970年的第一個“地球日”標志著世界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開始。同時,環保主義和核軍控運動的關系也日益密切起來,核試驗以及核軍備競賽作為威脅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與譴責。
綠色和平組織正是在西方社會這種環境運動、行動主義、反主流文化運動交織的背景下出現并壯大的。從其名稱中不難看出,“和平主義”是其主要意識形態之一。綠色和平致力于追求一個無核世界,它主張裁減軍備,強烈反對核試驗、核軍備競賽和核戰爭,從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站在反核反戰的第一戰線。從其許多次反核示威活動中也可看出,綠色和平一直深信“行動比說話更具有影響力”的理念,相比于語言上的抗議,其更愿意通過積極策劃各種“非暴力的直接行動”來揭露環境問題。
3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
從國際環境看,當時正處于冷戰中的“新冷戰”階段,兩極格局下美蘇競爭激烈,但多極化的趨勢已經凸顯。戰后受到削弱而不得不依附于美國陣營下的西歐經濟、軍事實力上升顯著,要求保障自身安全和維持大國地位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法國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獨立防務一直是法國全球戰略的基礎,1958年戴高樂總統執政時,就強調要奉行獨立自主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防務政策,核心是發展獨立的核威懾力量。戴高樂在1960年10月甚至毫不避諱地說:“我們也應該有自己的核威懾手段,否則我們就不是一個歐洲的強國,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只是一個被納入一體化的衛星國。如果不打破美、蘇的核壟斷,世界將永遠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天下。”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也不斷強調,法國必須保證自己獨立的核防務力量并“保證自己支配這種力量的權力,這是法國獨立地做出自己決定的保證。”現實政治使法國政府認識到,核力量是本國防務的“最終依靠”,法國正是依靠著自己獨立的核力量才阻止了蘇聯的核威脅和避免過分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在兩極世界中保持相對獨立和特殊的地位。這也說明在核時代,一國擁有核力量的政治作用遠超過了軍事作用。正是鑒于獨立的核力量在法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即使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法國政府也從未動搖過繼續在穆島進行核試驗的決心。
4 事件發生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是國際社會波瀾壯闊的環境保護運動和主張停止核試驗的強烈呼聲,另一方面是主權國家維護本國安全,絕不放棄核試驗的堅定態度,這種截然的對立和結構性矛盾必然會引發激烈沖突,1985年的“彩虹勇士號”沉船事件也由此發生。縱觀整個事件及其背景,我們可以將沖突發生的原因歸納為表層、中層和深層三部分。
首先從表層看,綠色和平作為一個相對激進的環保組織,其“非暴力的直接行動”這一行動綱領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攻擊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綠色和平與法國政府的矛盾由來已久。1972年綠色和平在穆魯羅瓦島進行的抗議就曾遭到了法軍的阻撓,但在綠色和平頻繁的抗議和被調動的輿論壓力下,法國政府還是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于1974年宣布停止在南太平洋的大氣核試驗。1985年,綠色和平準備繼續在穆島抗議示威,要法國取消在那里的包括地下核試驗在內的全部核試驗的要求顯然進一步觸及了法國政府不可讓步的核心利益。此外,非政府組織和國家政府所代表的利益覆蓋面顯然是不同的。非政府組織既不以整個社會或者國家民族的代言人自居,又不依從許多世俗慣例,有的非政府組織更天然是政府的對立面和批評者,他們只以社會部分成員的要求作為存在根據。而政府通常以全民族的利益和要求作為合法性的基礎,反映的是正統習俗的觀念,在國際外交上,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所以它本能地拒絕他認為的少數成員的“偏好”、批評或是呼吁。法國政府和綠色和平組織的這種沖突也就自然會出現。
更進一步分析,雙方實力的懸殊是法國政府沒有采取妥協或者繼續協商而是決定使用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的重要原因。盡管20世紀70年代后,環境問題已經演變成國際社會所不能忽視的政治問題,加上生態學的普及和民眾環境意識的提高,不斷壯大的環境運動給了政府很大的壓力,但它們畢竟還是少數派,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地位。正如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暴力機器,國家壟斷了在國內合法使用暴力的手段。雙方實力差距過于懸殊,代表整個國家力量的法國政府對這些少數派做出進一步示弱或者妥協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而整件事發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反映出的現實告訴我們,在當時,環境保護理念并未凌駕于主權和國家利益之上,人類中心主義仍占據著主導地位。這里的“人類中心主義”指的是人類活動所追求的全部和唯一的利益,歸根到底是人類自身的好處和需要,人類不會為了任何非人類的動物、植物或生態體系去做任何事情,除非它們適合了人類的某種需要。這一點在主權國家上體現的尤為明顯。當環境保護僅僅涉及到一些比較有技術、工藝層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時,政府顯得比較慷慨大度。而一旦環境保護涉及到了比較敏感的國家安全、軍事政治利益等時,主權國家的行動就變得謹慎而有敵意了。換句話說,當主權國家面臨國家利益與生態保護的抉擇時,前者必然會被放在首要考慮位置。可以肯定,法國的防務政策和繼續在南太平洋進行核試驗的基本方針是不會改變的。不僅僅是法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對法國核試驗的強烈譴責從根本上看也是因為法國的核試驗損害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而少有出于保護自然權利的視角。這件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雖然環境主義、環境運動有了很大發展,但人類中心主義仍然的主流地位依然難以動搖。
盡管如此,從結果看來,1985年彩虹勇士號事件使得法國政府受到了巨大損失,在其國際聲譽、地位甚至是外交上都造成了不小的打擊,而對綠色和平來說卻是它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綠色和平因此而轟動一時,大大增加了其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也為它贏得了公眾的同情,并極大地鼓舞了環保人士的斗志。其后幾年,綠色和平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階段。其實,環境保護運動和環保主義思潮也在這種不斷斗爭中廣泛傳播并進一步發展壯大。
5 結語
總之,“彩虹勇士號”的沉沒是環保主義和國家利益相沖突的結果,通過對當時生態思潮和政治背景的層層分析,我們可以初探事件背后紛繁復雜的利益、觀念與力量的博弈。20世紀70、80年代的環境主義運動的浪潮以橫掃西方的速度發展,卻也面臨來自各方面利益相關體的阻礙,包括環境運動自身也有許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如何在生態理念與國家利益中尋找平衡點,始終是一個困難的命題,我們既需要對傳統國家主權觀進行修正,也不能忽視對環境主義運動的開展進行規范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