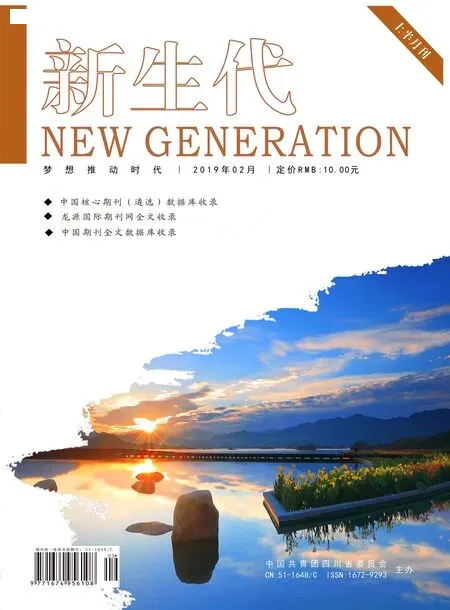陳寅恪:“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李升學 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
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涌現。陳寅恪先生就是民國時期涌現出的璀璨巨星。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遠流長影響著后人,佛房一盞明燈,照亮史學前進的道路。
一、初聞陳先生
第一次初聞先生那是在無知的大二第一學期,記得某師老師講課時說“做學問就要做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讀書寫文章就要做到直掏心臟,立意拔高。”上萬老師的課總是能把迷失的自我拉回到現實的人生中,去思考,去感悟。還記得第一次讀的是陸鍵東老師著作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剛開始讀時心里只是帶著老師給的任務去讀,當慢慢深入了解到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人生經歷,我已由不情愿讀轉變為心向往之。對陳先生充滿了尊敬崇拜之情。
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終于讀完《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而始終縈繞在我心頭的是那份沉重,除卻陳寅恪晚年不得安寧的生活,還有那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的凄涼。字里行間,猶可清晰的的找尋到作者翻著泛黃的檔案,動容而又感傷的印下上個世紀的學人風骨。整本書刻畫出了一個學者文人身不由己的畫面。我想,作者是極敬重陳寅恪的,那就難怪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一絲絲的偏愛,一絲絲的懷念。
此書,與其說是在向我們展示陳寅恪的晚年光景,莫不如說是以陳為核心的一眾知識分子在大環境中的沉浮錄,一個群體有著難以自持以及身不由己的悲涼。梁曉聲先生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在談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現狀時,曾這樣寫道,“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視他為官員。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有幾分不痛快起來。如果他是他所從事的知識領域內的官,他將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區別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認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這在中國絕對有著根深蒂固的思想起源,只不過是當今社會的現狀加劇了此類現象。知識分子原本應該安于學術樂園,只可惜政治化的浪潮仍將他們掀得此起彼伏。陳寅恪從十幾歲起就一路飄泊,偶有幾年靜心休學也終被這混亂的年代打亂。也唯有在那時的年代中大學的獨立才格外顯著。大學,莫不是文人的聚居地而已。可就是有那么多的文人,為了迎頭趕上社會浪潮的大風向,前赴后繼,才越發顯得像陳寅恪的“落后與腐朽”。讀這本書,讓我的心跟著沉痛了一段時間,并沒有完全理解其究竟忍受了多少苦難,可那種哀慟的氛圍卻像一根針,時不時的在戳傷著我的心。現代人速度太快,太浮躁,燈紅酒綠的世界里充盈著太多的誘惑,利欲熏心,談自我這種形而上的東西似乎只是躲在象牙塔校園里的人們的專利。于我而言,我所能確定的僅僅是陳寅恪的那種執著會一直支撐著我,是在今后的路上偶有松懈時的鞭笞,我還是會把最本質的東西深深地壓在心底。 陳寅恪,是學人風骨,是純粹,更是前行的明燈。
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幽靜的清華園,矗立著王國維的紀念碑,學子們每經此地總會懷著對一代國學大師的崇敬與惋惜的心情,而又總會為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陳寅恪所寫的碑銘所感動與激勵。碑銘中稱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練的語言總結表達了近世啟蒙思想運動以來中國學者要求學術獨立與自由的理想,成為正直學者的追求與人格的象征。
1925年初,清華學校欲設立國學研究院,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由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出面,先后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這就是后來名動天下、流傳久遠的“四大導師”
陳先生在清華園講課的時候說到“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不講”,陳寅恪也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于是陳寅恪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令師生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先生響亮的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都能感覺到。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為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留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看不起。但不管是那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三、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
陳先生說過,在解釋古書的時候,要“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但他有時候故意“不改原有之字,轉用新出之義”。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不古不今之學”就是這樣的。他在1933年曾經說過短短一句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這是他寫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里面的。歷來對這個話的解釋不一。馮友蘭認為這是陳先生實述自己具體的學術、工作和思想情況。可是當過陳先生學生的鄧廣銘根本否定這種說法。他們都是在八十年代末說的這些話。但直到現在,我們對這話的理解基本上還沒有共識。不過,我們可以通過解釋或了解其他人怎么看這句話,來探索陳先生自己的思想、學說及處世方式。
逯耀東很早就說這話跟今古文經學有關,但又說也可以作為專治史學中的魏晉隋唐史來講。這話有一些問題,因為前面的“平生”很重要。平生當然指以前,可陳先生做魏晉隋唐史是在1933年以后。汪榮祖說:“不古不今之學就是指中古史”,他的說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后來就有一些不同意見了。桑兵就說這話跟馮的著作的審查有關。桑老師比較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是中國大陸首個支持逯耀東說法的人,認為“不古不今之學”就是跟經學的今古文有關。李錦繡的理解更加具體,她把陳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學跟另外一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聯系起來,認為那句話是解釋這個的,具體的“古”指的是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和顧頡剛他們的疑古,“今”指的是胡適他們的整理國故。程千帆說這些人全都在胡說,尤其提到汪榮祖的說法與事實不合。程先生的貢獻是指出了這個話出自《太玄經》,并特別點明和此話相配的是“童牛角馬”。最近又有劉墨提出與逯氏相似的詮釋。牟發松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他在比較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與陳寅恪的“六朝隋唐論”時說:“陳氏論著常以中古一詞指代所研究的六朝隋唐時代,對于熟諳世界文明史的陳氏,所謂中古、不今不古,不可能僅僅是一個描述時間距離的辭藻,應當含有時代性質的內容。”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黃清漣也注意到這一點,認為理解這個話最關鍵的是“童牛角馬”,可惜他沒有具體說為什么。黃先生說它的意思是兼涉的、調和的、不古不今、不舊不新、不中不西、亦古亦今、亦舊亦新、亦中亦西。我想這個說法大致接近陳先生的意思。
按照陳寅恪先生自己的做法,解釋詞句,首先要認識作者的直接動機。陳先生在講到用典的時候,提出了幾點:第一,這個典故必須發生在要考證的這個作者做文之前;第二,要考慮用典的人對這個典故有聽說和見到的可能。我今天就嘗試用陳先生的方法來考察他到底用的是哪一個。晚清提得很多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跟陳先生這句話的后半句“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有直接的聯系。近代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葛兆光老師特別強調的甲午。在甲午以前和以后,同樣的說法表述的是非常不同的意思。張之洞的《勸學篇》被認為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表征。這當然是代表甲午或者以后的事。
大部分人在引用這段話的時候就說陳先生要區隔時流。他想要劃清界限的一些人不僅有胡適,也包括梁啟超,包括章士釗、梁漱溟、張君勱這些被列為東方文化派的人,也包括很多人直接把陳先生算進去的學衡派。所有這些人,他們的見解都有一部分是和陳先生相通的,可是也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所以 “不古不今”就是要跟所有這些人都不一樣。他在《四聲三問》里很明確地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成是同光的思想,而不說成是咸同的思想,這里面應該是很有分寸的。我想,這個話是有它的直接含義的,就是他對張之洞有認可的一面,也有不認可的一面,所以他要回到張之洞之前。
他為什么要回到曾國藩呢?張之洞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基本指的是一個以儒學為中心的學說,而且他是主張“損之又損”的,這是《老子》里的話,下面就是“以至于無”。如果損之又損是可以以至于無的話,那“中學為體”基本就是一個象征了。而曾國藩是把當年的考據、辭章、義理、經世和孔門四科連起來的。簡單說來就是,曾國藩時代的“中學”比張之洞時代的范圍要大得多。陳先生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保存中國的某種東西,但是要接受另外的東西,讓它發生轉變。我猜,他之所以要回到張之洞和曾國藩之間,是希望有一個更寬的以維護中國的東西。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跟陳先生經常使用的另外一個詞“非驢非馬”要放在一起理解。他始終指出“非驢非馬”有一個意思,就是要融合胡漢為一體。這個跟他后來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直接的關系。他曾經明確地說,李唐一族之所以能夠崛起,就是取了“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我想這基本上就是“不古不今之學”想要做到的,但關鍵是要別創空前局面。這是“童牛角馬”的一個含義, “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要相反而適相成”。
陳先生講“不古不今之學”不一定講他做中古史,他說的“平生”是1933年說的,此前他基本上沒有做多少中古史。陳先生和章太炎都曾經反對民國新史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國新史學比較偏重研究上古史。章太炎曾明確說,上古的歷史對于中國的當時沒有借鑒作用,不能致用。唐代這個時候是一個中外接觸頻繁的、各種文化碰撞的時代,比較切近近代。所以陳先生寫《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本著作,他有一種經世致用的理想在里面,就是要報國。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里兩次說到童牛角馬,都是要特別強調中古的這段歷史對中國的意義。我們不能說陳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學就是要做中古史,因為那是后來的事,但是他往中古史轉移,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一個讀書人總要以某種方式來為國效力,若不上前線打敵人,也應該有某種表述。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創造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同時,亦積淀了過于厚重的歷史文化沉疴,而專制思想便是其最為顯著的表征。封建社會的專制政體及其文化傳統留給人類最大的災難,就是扼殺人的個性思想和獨立不羈的人格,通過政治強權和道德教化培養人的奴性意識,使人喪失自我。對于此,陳寅恪有著最為清醒、最為徹底、最為深刻的認識。此時,在王國維的紀念碑銘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覽無余。
可以說,陳寅恪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中國數不清的風浪,但他從不為形勢所左右,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盤西化”論獨尊一時,而他卻以自己的勇氣堅稱“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面對喧囂一時的政治思潮,陳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雖然他有時迫于時勢,噤不得發,但卻無所畏懼,依然“論學論治,迥異時流”。
作為一代大師,陳寅恪為海內外學人樹立了一個高峻的標格,使人們覺悟一種嚴肅的學術追求,一種理性的文化心態。陳一生守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的是憑自己的睿智和膽識,實踐一條現代知識分子終將會走通的“續命河汾”之路,意欲建構自成一體的知識分子價值體系。雖然歷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邁的胸襟和戛戛獨造的膽識在現代文化史上鑄造了一個鮮活的靈魂,先生的風骨為后世學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也必將為后世學者所宏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