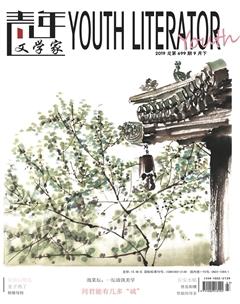淺析張愛玲與波伏娃作品中的女性主義
王越
基金項目:吉林外國語大學2018年學生科研項目“中法女性主義比較研究——以張愛玲、西蒙娜·德·波伏娃為例”JW2018XK117。
摘? 要:張愛玲與波伏娃同為中西方文壇上重要的女性作家,她們都塑造了很多血肉豐滿的女性形象,作品中充滿犀利的批判和精準的審視。本文對兩位偉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解讀,探討二者作品中女性形象以及寫作風格的異同,觀察不同時代與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義思想。
關鍵詞:張愛玲;波伏娃;女性主義;對比分析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7-0-03
1789年7月14日,旨在推翻波旁王朝君主專制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吶喊中拉開序幕。這場偉大革命不僅對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開創了世界婦女運動的先河。這次法國歷史上第一次婦女大規模行動標志著法國婦女運動的興起和法國女性主義思想的萌芽。在一百多年后的大陸另一端,中國的女性意識也開始慢慢覺醒。隨著五四運動的開展,婦女運動綱領與領導思想逐漸成熟,中國的女性主義不斷茁壯成長并發展出了獨特的中國特色。而在這歷史的浪潮中,誕生了許多杰出的女性主義思想家,她們都為女性的權利、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中,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與中國現代女作家張愛玲都在她們的作品中對女性主義做出了獨特的詮釋。兩位作家的創作巔峰都處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但由于時代背景、國家文化的不同,兩位作家對女性意識的表達也有所不同。本文通過分析波伏娃與張愛玲文學作品中的經典女性形象,對兩位作家傳達的女性主義思想進行平行比較,深刻探討女性主義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一、張愛玲女性主義思想
張愛玲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傳奇,她獨特的語言特色與寫作風格使其藝術作品成為傳世經典。她的作品塑造了很多血肉豐滿的具有中國特質的女性形象,具有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征。通過深入描寫女性的精神世界,她對女性自身的弱點進行思考,開拓出了女性批判的方向。
(一)“紅玫瑰與朱砂痣”——王嬌蕊女性形象
《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張愛玲經典之作,小說從男性視角出發,揭露了女性在男性統治的社會下的生存困境。王嬌蕊作為文中唯一的一朵紅玫瑰,無論在言談舉止還是處事風格上,都有別于傳統中國女性溫順恭良、三從四德的形象。
在華僑家庭背景與倫敦豐富的交際經歷的影響下,王嬌蕊的思想已在西方先進思潮的影響下變得開放。出場時便先聲奪人,身穿浴衣迎接客人,待人接物時也沒有絲毫的拘束。她沒有逃避掩飾自己與佟振保的愛情,并選擇直接寫信向她的丈夫坦白,而這樣一個勇敢的選擇,卻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背景下顯得辛酸與悲哀。盡管受過五四運動與西方思想的浸染,王嬌蕊仍無法憑一己之力掙脫傳統封建思想的禁錮。因為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提供的物質條件,她的一切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在意識到佟振保不可能拋下世俗的偏見與她遠走高飛時,她沒有再進行徒勞的哀求與勸說,干脆果斷的離開。王嬌蕊的結局是重新成為一個傳統的女性,仍以婚姻謀生。她明白了在愛情中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事情,例如倫理,世俗,規矩。女性的獨立意識最終還是被封建思想扼殺,她那熱烈鮮明的性格只得在女子需三從四德的大環境下被拋棄。回歸家庭,放棄自我是王嬌蕊無法抵抗的命運。
(二)“月有陰晴圓缺”——曹七巧女性形象
女性角色悲劇的命運在中篇小說《金鎖記》中愈加突顯。原本活潑開朗的鄉下姑娘曹七巧被賣入大戶人家姜公館,成為了 殘廢的姜二公子的正房。由于卑微的出身,她受盡姜公館里每一個人的嘲諷與羞辱,加之與姜二公子名存實亡的婚姻,她的性格日益扭曲,甚至親手葬送了一雙兒女的幸福。讀罷全文,只覺她的一生充滿刺骨的悲涼。
腐朽的傳統封建思想則是促成這場悲劇的主要推手。在那個封建思想殘存的混亂年代,人們對金錢的追求超過了思想道德底線,吸鴉片,逛窯子都是生活常態。婚姻是用來牟利的工具,女性則是其中的犧牲品。社會對女性嚴苛的道德要求像沉重的鐐銬,鎖住了無數女性的自由與希望,如果做不到賢淑、孝順、溫婉,就活該遭受千夫所指。在感受到人情涼薄的現實后,曹七巧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更牢靠”的金錢上,久而久之,由她親手打造的黃金鎖不僅永遠困住了她,還葬送了周圍人的生命。這是一個女性的悲涼結局,也是一整個社會的殘酷寫照。
從《紅玫瑰與白玫瑰》和《金鎖記》的主要兩個女性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愛玲遠離了四十年代戰爭的主流話題,將目光深入到男權社會下的女性生活。她不僅從外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對女性的摧殘,刻畫了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悲慘命運,還從女性意識的原罪出發,揭示出女性自身的性格弱點與奴性意識,將作品主題上升至對人性、命運、歷史的思考。
二、波伏娃女性主義思想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國極具影響力的女性存在主義作家,她的女性主義哲學思想影響了不同時期的女性。在哲學領域保持獨立的思考外,波伏娃在文學創作上也獲得過巨大成就。她的小說傳達出了“現代女性應掙脫傳統世俗的禁錮,獨立思考,與時俱進”的思想。
(一)從“依附”到“獨立”——弗朗索瓦絲女性形象
波伏娃的處女作《女賓》以弗朗索瓦絲單視角出發,她是一名獨立自由的職業女性,一直自認為與皮埃爾保持著不受世俗、婚姻約束的理想感情關系,他們二人并歸于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而在第三者介入這段感情時,她發現自己只是依附于皮埃爾的存在。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曾提出了“他者”的概念,認為女性受到“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不得不受制于男性的支配。在文中,作者對弗朗索瓦絲的心理活動有過這樣的描述:“她所想的一切都是與他一同想和為他想的。”她為皮埃爾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根本不會思考發自于自身、與皮埃爾無關的行為,很顯然,弗朗索瓦絲已經在這段看似穩定、情投意合的關系中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主體意識。在“三人組”的關系中,弗朗索瓦絲發覺“皮埃爾總是只顧自己走路,甚至不回首望她,然后,他卻確信她緊隨著他。”毫無疑問,皮埃爾才是這段關系的主導者,另外兩位女性被動接受了這一切。面對格扎維埃爾的闖入,弗朗索瓦絲并沒有反抗,反而選擇遷就與自己性格大相徑庭的格扎維埃爾,討好皮埃爾的想法,一味地容忍與退讓。最終,佛朗索瓦絲選擇反抗,爭取自由,打開煤氣與格扎維埃爾自盡,留下了一個悲壯、令人扼腕嘆息的結局。
(二)理智中的勝利——安娜女性形象
《名士風流》是波伏娃創作巔峰時期的代表之作,描繪了戰后法國知識分子處于迷茫彷徨的精神困境。安娜是一名經濟獨立且受教育水平高的知識女性,她對政治、哲學、人生都有著自己獨立的見解。她和作家羅貝爾的婚姻始于愛情,雙方在這一關系中都處于尊重、平等的地位。
這部作品對兩性關系的描述不帶有任何社會偏見與世俗歧視,把男女間對欲望的追求以一種直接純粹的手法描繪了出來。其中,安娜在美國遇見令她一見傾心的美國作家劉易斯,瘋狂投入到了這一段她極度渴望的愛情中,但她并不以此為恥,周圍人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作者著重于挖掘女性在面對人生抉擇時的精神世界與思想狀態。盡管如此,社會中還是天然存在著對女性追尋自由的阻力。通過安娜心理活動的描寫能感受到,在同時承擔工作壓力時,女性還需比男性肩負更多的家庭責任,例如安娜在決定是否去美國參加會議時,她不得不時時考慮女兒與丈夫的狀況。在經歷了與劉易斯有始無終的感情后,安娜不堪精神上的壓迫與抑郁,險些自殺。然而最終理智戰勝了一切,她意識到生者近在眼前,讓別人經受自己的死亡是愚蠢且無意義的,既然心臟仍在跳動,那必須要讓這生命充滿活著的意義。安娜這一人物形象,不僅代表了當時法國上流社會獨立堅強的女性知識分子形象,還體現了波伏娃對兩性關系、女性追尋自身自由的獨到見解。
作者通過這兩位同為知識分子,但命運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強調盡管經濟事業等物質方面的獨立能一定程度上幫助女性獲得生活上的自由,但并不能從根源上打破思想上的枷鎖。徹底鏟除男尊女卑觀念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波伏娃寄希望于塑造不同的女性角色,鼓勵女性勇敢追尋出路,獲得真正的獨立與自由。
三、張愛玲與波伏娃女性主義的比較
(一)張愛玲與波伏娃女性主義比較的相似之處
首先,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制社會都是波伏娃和張愛玲作品中遏制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阻礙。不管是處于封建思想殘余的中國近代還是平等思想已得到廣泛認可的法國,女性的自由道路上仍是障礙重重。根深蒂固于大眾內心的偏見不僅在時刻打壓著女性,且讓很多人自出生起就將這一思想根植于大腦,形成思維定式。張愛玲的作品中大多是成長于中國封建與新式思想交匯時期的女性,由于社會變革不徹底,她們從小接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育,之后便終生膽戰心驚地活在綱常倫理的陰影下,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她們狹隘的目光阻礙她們發現自己身處的悲哀處境,將一切生活的不如意歸咎于天命、世道,或轉化為怨恨惱怒撒向旁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理論也同樣表達了她的觀點: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傳統的父權制度將女性限制在了家庭、婚姻中,使其別無選擇,只能走向成為男性附屬品的道路。
其次,婚姻生育也是禁錮女性思想的另一枷鎖。女性承擔著人類繁衍的責任,而這一點卻被用做囚禁女性的鐵柵欄。十月懷胎與家務瑣事將女性牢牢地拴在屋內,迫使女性放棄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業中去。在封建時期的中國,與有錢男子結婚是最好的出路。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婚姻成為人們謀利的工具。貧窮人家在盤算嫁一個女兒能賺多少錢,女性在謀劃攀上一戶好人家,男性則在時刻提防保護自己的家產。女性身上的有利條件被劃分為籌碼,赤裸裸地被擺在桌上,等待著有意之人來討價還價。如此循環導致了女性地位的逐漸下降與女性特征被物化的結果。波伏娃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便選擇與薩特始終保持自由的交往關系,她認為婚姻會使女性喪失自我,造成兩性關系的不平衡,因此可以看出她對婚姻持否定的態度。
(二)張愛玲與波伏娃女性主義比較的不同之處
與波伏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不同的是,張愛玲創作的人物大多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無論是王嬌蕊還是曹七巧,她們最終的命運都是屈服于殘酷的現實。來自生活的重壓是一切悲劇的源頭,沒有人能在這樣一個大熔爐里幸存下來。作者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冷眼觀看著一幕幕的慘劇,通過冷峻凝練的表達手法,揭露了人性的丑惡、貪婪、自私,意于瞄準當時社會封閉壓抑的痛點,以此來喚醒女性心中的主體意識。由于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波伏娃筆下的女性形象相對來說更加“幸運”。她們都有獨立穩定的工作,以愛情為基礎與另一半建立了相互尊重理解的理性關系,她們的掙扎與彷徨更多來自于精神世界。社會上對于女性的偏見不露于表面,但也如影隨形。女性在追尋自由時更容易被精神上的羈絆壓垮,有的能像安娜理性自救,而有的如弗朗索瓦絲,付出死亡的代價。可以說,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掙扎于生存,而波伏娃創作的人物糾纏于生活。
此外,兩位作家對女性意識的描寫以及個人的女性主義觀點的表達方式截然不同。波伏娃側重于從內部探尋女性意識,對外部環境的描述是理智且客觀的,通過大量的心理活動描寫女性在不同階段的變化與思考,用更為直觀的方式敘述女性意識覺醒、迷茫、反抗的過程,鼓勵女性自由地探尋自我意識。反之,張愛玲多從外部角度闡述女性問題,即父權體系的禁錮與封建思想的迫害對女性奴性意識的影響,她善于用比喻、意象等暗示女性的悲慘命運,例如《金鎖記》中的月光,《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白月光與朱砂痣。通過大篇幅的環境、景物、動作描寫,塑造出特定環境下的氛圍,激發讀者探尋作者寫作目的的興趣,間接傳遞出中心思想。
四、結語
通過比較這兩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可以從中能觀察到中法兩國的思想文化差異,這對語言學者來說是一個寶貴的學習經歷。而在女性問題的探索上,兩位作家都用自己獨特敏銳的目光洞察了女性的歷史,向社會傳遞了自己的聲音,并為著同一個目標——女性主義前行。她們筆下的人物,無論悲喜與否,命運是否坎坷,都為文學界留下了深刻的時代烙印,當她們審視千百年來困于男權社會壓迫的女性時,新時代的女性主義正在翻開新的篇章。
參考文獻:
[1][中]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2]張愛玲.《金鎖記》[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女賓》[M].周以光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
[4]西蒙娜·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5]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士風流》[M].許均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6]姜珊.伍爾芙與波伏娃女性主義比較研究[D].遼寧:遼寧大學,2013.
[7]宋虎.論蕭紅與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劇意識[J].大學教育,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