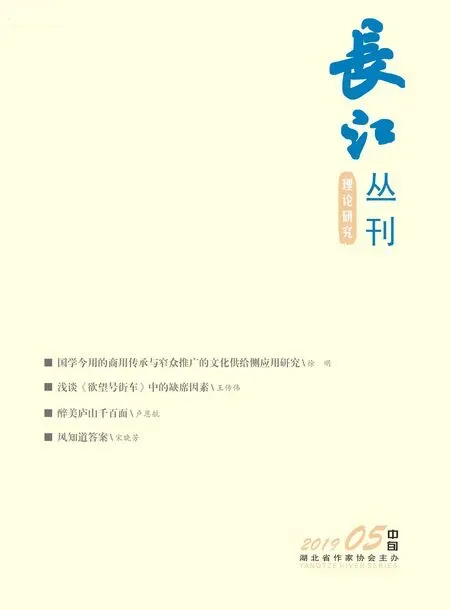存在的困惑與意義
——論加繆作品思想的雙重性
■張智韻/太原理工大學現(xiàn)代科技學院
法國作家羅歇·格勒尼埃將“陽光與陰影”作為加繆傳記的題目,這一對既相反卻又不可分離的詞組正代表了加繆思想的雙重性。生長在阿爾及爾貧民區(qū)的加繆一生與陽光、大海和生活的熱情相伴,但同時伴著他的還有另一面:陰影、孤獨、貧窮和失望。他一生都在努力尋求著兩極的平衡與和諧,這種雙重性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印證:反與正、孤獨與團結(jié)、生與死、幸福與痛苦、光明與黑暗、有罪與無罪、流亡與王國等等。在加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巨大的虛無感和內(nèi)心的熱情同時存在,這使得他的存在主義思想既有認識論的深刻,又有價值論的崇高,試圖給在荒誕世界中苦苦掙扎的人們指出一條出路。吸取了地中海陽光的加繆也同時吸取到了這種陽光孕育出的古老文化——古希臘貼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文化。加繆用這種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尊重來平衡存在的正反兩種極端,形成了他作品思想中特有的雙重性。加繆作品中的雙重主題具體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反與正
1937年加繆出版了他第一部散文集《反與正》,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反與正》再版,在《再版前言》中,加繆寫到:“每個藝術家都在心靈深處保留著一種獨一無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養(yǎng)著他的言行……就我來說,我知道自己創(chuàng)作的源泉就在《反與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過的貧窮和光明的天地里。”散文集《反與正》是一部反映了加繆內(nèi)心真實的作品,從中可以窺視到加繆的成長環(huán)境和生活經(jīng)歷,也預示著他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形式和主題。
在《若有若無之間》中描寫了一位被戰(zhàn)爭奪去丈夫的母親形象。她從不愛撫孩子,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略為微妙,甚至有一種淡漠,但內(nèi)心里她是很愛自己的孩子的;兒子對終日操勞的母親懷有深深的憐憫,可同樣不善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愛。這一母子關系正是加繆與他母親之間的關系的寫照。一邊是沉默、孤獨、死亡圍繞著的貧困,一邊是陽光、大海、生活的熱情,加繆美學觀的基本原則就是在這兩極之間尋找平衡。《反與正》中通過一個老婦人用全部的積蓄修筑自己的墳墓的故事來表明加繆自己的生活哲學,即生活中存在的荒誕如同生活本身一樣,是同陽光、空氣一起存在的,是無法否定的現(xiàn)實,世界的正反面無法分開,就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無法割離。
二、幸福與痛苦
在加繆眼中,“沒有生存的痛苦,就不會熱愛生活”,生活的幸福和痛苦也是相伴相生的。《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爾索的一生伴隨著生活的痛苦,而他卻自認為是幸福的。但一個除了絞刑架別無選擇的人,談何幸福?在加繆看來,默爾索是誠實的,他絲毫不肯用文明社會的習俗來掩飾自己、檢討自己,面對著強大的社會法則他也不肯屈從。默爾索渴望真實地活著,而社會為人們規(guī)定的法則是虛偽地活著。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任何一個連母親下葬時都不哭泣的人都會被認為是喪失道德,甚至有可能被判處死刑。默爾索最終發(fā)現(xiàn)了真實的自我和虛偽的社會之間的不可溝通、不可共存,發(fā)現(xiàn)了“文明社會”的荒誕。于是,在做社會的孝子和棄兒兩者之間,他選擇了后者。人無法把控自己的命運,因此,生命本身就是荒誕的、偶然的,真實的生活和虛偽的生活一樣毫無意義,擺在人類面前的永生之路只有一條遲早無法躲避的死亡。對于這一點的深信不疑,才是默爾索執(zhí)著而深厚的激情之所在。
既然默爾索明確地意識到無法對人生賦予任何永恒的、有價值的形態(tài),他自然就放棄了這種努力,只專注于短暫的幸福和滿足中:海濱的炎熱、夏季傍晚的氣息、溫暖的海水、瑪麗豐滿的胸部等等,這些成了他的敏感細膩的心靈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實和幸福的全部。默爾索發(fā)現(xiàn)了荒誕,就找到了幸福。加繆在認清世界的荒謬和人生的痛苦的同時,也不忘告訴人們什么是幸福,就如同他筆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因此,加繆的哲學就轉(zhuǎn)化為這樣一個問題,其本質(zhì)已不再是活著是否有意義,而是帶著命中注定的那份痛苦和折磨,如何去生活。
三、流亡與王國
加繆在小說集《流亡與獨立王國》中深刻地刻畫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狀態(tài)。所謂“流亡”與“王國”是對立的世界,加繆把人的日常生存說成是流亡,人生在世的各種狀態(tài)在他看來都是荒謬的現(xiàn)實,都是一種意義的流亡,而王國則存在于彼岸,存在于人內(nèi)心的理想之中。人類本質(zhì)的存在于獨立王國之中,人只是偶爾超越日常生活的限制才能獲得這樣的境界,并且它是難以捉摸而又轉(zhuǎn)瞬即逝的。在某種意義上,流亡以特有的方式又標示著走向獨立王國的道路,為了尋找到這條道路,人們又必須懂得拒絕屈從于流亡。
《不忠的女人》中的妻子雅尼娜陪伴丈夫進行一趟生意旅行。她被阿爾及利亞南部當?shù)赜文敛柯涞娜藗兯@群人貧窮卻自由,他們是一個古怪王國的主人。這吸引雅尼娜反思自己結(jié)婚二十五年來蒼白、貧弱的婚姻和生活,將游牧人的王國認同為她自己的王國,在一個夜晚離開了她的婚姻之床,將身體與自然力量熱烈地相交合。雅尼娜的“不忠”在于她對丈夫靈魂上的背叛,是對自己生存處境的一種覺醒,但在短暫地忘卻現(xiàn)實婚姻的單調(diào)、苦悶之后,雅尼娜又回到她的丈夫身邊,再次返回流放狀態(tài)當中。加繆筆下的王國是愛和理解的王國,正是現(xiàn)實中的各種“流亡”,使人們從此岸憧憬著彼岸的美好,才使得內(nèi)心的王國有了巨大的意義。
四、孤獨與團結(jié)
每個人作為個體都是孤獨的存在,但同時加繆非常強調(diào)人性的普遍性,而反抗證明了這種人性的普遍存在,也只有反抗才能肯定它的存在。這樣,團結(jié)也應運而生,在反抗的過程中,人走出孤獨,走入集體,反抗成為了集體的斗爭。在人性這個共有的價值之上,人們建立起團結(jié)一致的價值。反抗超越于個人主義之上,在面臨人類共同的命運時,人們團結(jié)起來抗擊惡與死亡,擺脫了孤獨的斗爭。
加繆在《鼠疫》中充分地表現(xiàn)了孤獨與團結(jié)這一主題。加繆不再像《西西弗神話》中那樣只是一味強調(diào)個人的命運,在阿赫蘭城遭到鼠疫肆虐的情況下,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是對生活的希望、對生命的留戀卻是共同的,因此,才有了一群以里厄醫(yī)生為首的反抗者。他們采取了與默尓索不同的態(tài)度,放棄了個人的絕對自由,不再以孤獨和冷漠對抗世界的荒誕。瘟疫的出現(xiàn)使麻木活著的人們變成了有愛憎和血肉的人,他們在經(jīng)歷痛苦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愛。鼠疫中團結(jié)一致的愛引起了對上帝建立的人間秩序的反叛和對死亡的抗拒,個人面對死亡的反抗也是人類對生存境遇的反抗。面對鼠疫中不可忍受的荒誕,人類必須持有的抗爭漸漸地由一種個人的經(jīng)驗變成了集體的共識。
在加繆作品這種雙重性的主題之下,我們不難看出他思想內(nèi)在的矛盾與掙扎。早年的加繆是貧窮的,窮到?jīng)]有一張寫作業(yè)的桌子,然而他又是驕傲的,因為他能在阿爾及爾的陽光下暢游在地中海的懷抱,他始終看到的都是一個陽光與陰影交織著的世界。這種影響使得在加繆的思想中,每當一個概念出現(xiàn)時,另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就會隨之出現(xiàn),從而限制了極端概念的發(fā)展,構(gòu)成兩極世界的相互平衡和制約。認識到了世界的荒誕,反抗的概念隨之出現(xiàn),在反抗的過程中從痛苦走向幸福。但當革命這一反抗的過度發(fā)展完全否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時,對反抗的限制也有了必要,加繆用和諧的人道主義呼喚了一種承認局限的反抗。在理論上,加繆從古希臘思想這一精神家園中尋找到了一種有節(jié)制的均衡,在肯定生命的基礎上給反抗規(guī)定一個適度的界限。“希臘思想始終固守節(jié)制的觀念,它從不把任何事物推向極端,無論神性還是理性,因為他不否定任何東西,既不否定神性,也不否定理性。希臘思想顧及萬物,以光明來平衡黑暗。”在加繆看來,這種節(jié)制并不等于妥協(xié),荒謬的人從冰冷的反抗中重新找回了熱愛生命的理由,他在這種節(jié)制中尋找的是生活的真實和人類的尊嚴。在這一意義之上,加繆通過對藝術的美和生活的真的追求,找到了兩極世界的平衡點。
注釋:
①(法)加繆,著.柳鳴九,主編.加繆全集 散文卷1[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4.
②(法)加繆,著.柳鳴九,主編.加繆全集 散文卷1[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8.
③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 加繆思想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