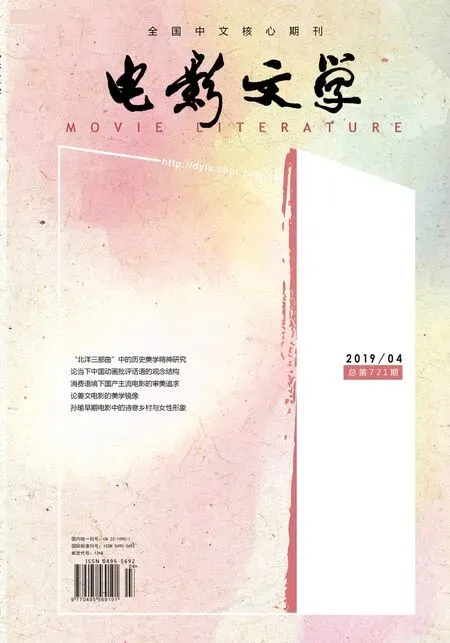論姜文電影的美學鏡像
董慧敏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姜文是當代中國影壇的一個獨特存在,他的幾部電影,都采取了獨樹一幟的表達方式,完成了電影表達上的多次創新,具有高度的審美價值。姜文電影的表現形式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顛覆性的美學意義。
一、姜文電影美學的表現形式
姜文在美學上的追求不僅僅停留在電影的畫面色彩及視聽語言等表面層面,更力圖將這些元素和電影深層的思想內核緊緊結合起來。同時,姜文也試圖在視覺和聽覺上對電影的鏡頭語言進行創新性的表達,對細節的完美追求更是體現了他作為一個導演的用心之處。姜文的鏡頭語言既細膩精致,又頗具富有主觀想象色彩的夸張、浪漫和狂放,體現了他在藝術上獨特的審美追求和審美超越。
(一)姜文電影的視覺因素
1.光線的處理
姜文電影中光線的處理有其獨到之處。姜文對光線的追求更多是與時代特征及人物性格緊密相連的。光線的利用力圖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一個大的舞臺和背景,同時,每一縷光線的投射也是人物內心的寫照。《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打光十分講究,利用人造光代替自然光,使得光線比較柔和,能夠體現出一種溫暖和諧的氛圍,這有利于展現一個處在青春期的男孩對愛情的美好幻想以及在社會失序狀態下人性解放的張力。《太陽照常升起》中光線在四個情節中游刃有余地轉換:第一個故事整體色調偏暗,室內光和室外光的偏差較大,有利于展現瘋媽分裂的性格;第二個故事整體色調偏于中性,以暗淡的光線為主,符合“文革”時期整體的時代色彩;第三個故事又回到了第一個故事的環境光線,大自然絢爛的陽光體現著主人公需要宣泄的欲望,室內光線的暗淡體現著人物在那個時代的壓抑郁悶以及人物之間的矛盾與緊張關系;第四個故事中大自然絢爛的光線展現了自然的廣博和宏大,更有利于展現人物面對廣袤的大自然油然而生的渺小和崇敬之感。最后一個鏡頭利用了逆光時的剪影,轟鳴的火車幻化成一個模糊的背影。太陽蓬勃的光線更展現出人物勃發向上的生命力和冥冥之中注定的輪回。
2.色調的處理
《陽光燦爛的日子》用了鮮明的色調對比展現了影片的主題。“其中觀眾看到的那種絢爛的金色,真如陽光般燦爛,使人溫暖而恬然。暖色調的強烈突出,抒發了那個特殊時代人們的生活激情,也可以反映出導演姜文年少時代的精神狀態,他所要反映的就是那樣的無拘無束,那種激蕩的少年情緒。……該片最后的顏色處理使用黑白的色調,也同時反映出了成人后的顏色,與年少時的暖色相對比,展示了年少時光的消逝而去,對于青春過往的無奈。”[1]借此展現了一種關于童年美好的想象以及現實的平淡煩瑣之間的深刻關系。這不僅僅是簡單地借鑒西方電影藝術后的精湛模仿,更是包含了深層思考后的情感噴發。《太陽照常升起》中,影片的色調豐富而不單調。電影中色調的運用如同油畫般富有詩意和美感。影片中的色調時而發黃偏綠,展現了一種歷史的質感,代表了一段時代的記憶;時而清冷而暗淡,展現了人物被壓抑的欲望和扭曲的人性;時而絢爛而輝煌,讓天地萬物和個體之人水乳交融,從而產生天馬行空的不羈想象。
3.道具的安排
影片中許多細節的處理和安排體現了導演的良苦用心,對表現人物的性格有莫大的幫助,這在道具的安排上體現得非常充分。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幾個細節頗富韻味。長筒望遠鏡的使用表現了一個男孩萌動的荷爾蒙和窺視欲,體現一種對愛情的向往和性的沖動。米蘭腳上的鑰匙體現了一種不合于時代而又富有象征色彩的神秘之感。余北蓓身上不同于那個時代的紅裙子展現了一個少年對于青春的美好憧憬和想象。此外,還有各種富有“文革”色彩的道具也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比如大標語、毛主席像、樣板戲、綠軍裝、紅肩章等。
(二)姜文電影的聽覺因素
1.人物的語言對話
(1)人物語言對話富有時代特征。姜文善于將人物語言設置在時代的方程式之中,從而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活生動。《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各種富有時代特征的語言隨處可見。“喜歡冬妮婭嗎?我喜歡保爾。冬妮婭也喜歡,可惜后來她變了,變成資產階級了”“姥爺竟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這種戰備觀念,要是帝國主義發動突然襲擊,還不全他媽的完蛋”……這些臺詞都體現著鮮明的時代色彩。
(2)人物語言對話富有地方特色。姜文電影中主人公的對話都帶有鮮明的地方色彩,這不僅讓觀眾覺得親切自然、平易近人,而且增加了影片的幽默感。《太陽照常升起》中瘋媽的溫州方言以及林大夫的上海嗲氣、唐嫂的南洋語調都可以讓觀眾揣測人物的身份背景,而這又和影片的主題密切相關。《讓子彈飛》中的四川口音更是極大地制造了人物語言的幽默感,展現了環境背景獨特的地域特色。
(3)語言的視聽感強,人物對話富有幽默感。姜文善于讓觀眾在歡笑聲中感悟嚴肅的歷史。這些幽默并沒有浮在表面,而是有深刻的象征和隱喻意味。相比那些帶給觀眾沉重觀影感受的影片,姜文的電影用一種創新式的激情顛覆了以往凡是關于深刻的歷史就要有嚴肅表達的論斷,帶給觀眾的感受必定是更加深刻的。《讓子彈飛》中的臺詞,就演繹著令人難忘的黑色幽默。“我以為,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路要一步一步走,步子邁得太大,會扯著蛋”“這他媽的稅收都收到2010年啦”“誰是窮人?誰窮,誰就是窮人”等。姜文電影中的這些幽默臺詞絕不僅僅流于表面,更是和影片的表現主題有一種一脈相承的關聯性。
2.電影配樂的合理使用
姜文對電影的配樂十分講究,其影片中的配樂往往是自然、人性和歷史的融合,時而靜謐婉約,帶領觀眾徜徉在想象的波瀾之中;時而野性豪放,展現著男人的雄性荷爾蒙和陽剛之美;時而自然舒展,讓觀眾感悟大自然的奇崛與瑰麗;時而悲涼沉重,讓觀眾體悟歷史的深邃和人性的復雜。音樂在姜文的電影中,不僅起到了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更是一種時代的符號和象征。《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毛主席,革命戰士祝您萬壽無疆》很好地展現了“文革”時代的歷史特色。而這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首配樂就是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每當女主角米蘭出現,這首配樂就會應聲響起,展現了女主人公的高貴典雅以及那種無法揣測的神秘感,還有成年馬小軍對這一段往事的懷念之情。《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幾首配樂展現了自然的廣博、生命的張力、人性的萌動以及不同的情感宣泄。其中,《太陽照常升起》展現了生命的輪回中勃發向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黑眼睛的姑娘》刻畫了瘋媽對李不空癡情的等待和守望;《前奏曲:瘋狂之開始》體現了瘋媽的種種瘋狂。而其新作《邪不壓正》,能“使人清晰感受到古典音樂在《邪不壓正》中對于電影空間拓展所起到的多重作用。姜文選用大量古典音樂與這部武俠電影題材結合,使這部電影變得與眾不同”。[2]比如《第二圓舞曲》輔助呈現了別樣的京城舊貌,《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則暗示了正邪之宿命。
二、姜文電影美學的表達方法
姜文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法無疑是多元的,且永遠是那樣的個性鮮明而又獨樹一幟。往往既帶有個人經歷的傳記色彩,又帶有逝去時代的普世價值,從而構成了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共同回憶。姜文電影的表達手法剝離了傳統的敘事手段和中國電影程式化的僵化表達,既具有高度的藝術特征,又帶有創新性的顛覆和對電影美學的重新建構。姜文的風格不同于一般性的寫實,亦不流于耽于幻想的不合理想象,而是力圖在藝術和現實之間尋找一個有效的平衡點,用最與眾不同的藝術手法去還原最深刻的真實。
(一)對隱蔽文化的重新建構和解讀
姜文的電影敢于突破傳統電影的敘述手法,敢于突破意識形態的宣教色彩去對中國最隱蔽的文化做出別具一格的解讀。《陽光燦爛的日子》和《太陽照常升起》反映的是“文革”題材,而這兩部電影讓觀眾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文革”色彩。不同于傳統電影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避,或者展示這段歲月的沉重與悲傷,姜文用一種“不嚴肅性”將自己的作品和他人進行區分。《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反常態,將“文革”這段灰暗的時光稱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以一個少年懵懂而又青澀的愛情為切入點去還原一個真實的時代。影片突破了桎梏化模式的藩籬,以個人的視角、平凡的小事,用與最嚴肅的歷史相反相離的愛情去生動地展現一個時代,可見姜文獨特的藝術構思。而影片通過這一個個生動情節的再現,從歷史的暗角處無聲但又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的另外一個側面。《陽光燦爛的日子》對“文革”歷史的顛覆性解讀,氤氳的是濃厚的政治氣息,讓觀眾體悟到的是最真實的“文革”歲月。《太陽照常升起》中,姜文破除了傳統意義上關于“文革”壓抑窒息的時代氣息而實現了人性的大狂歡和大解放,影片中充斥著性、愛、欲望和瘋狂,生命在這個不合適的年代中有了最大的張力。姜文從歷史的對立面去解讀和看待這一段歷史,其標新立異的程度讓人嘆為觀止。歷史的深刻性以及對時代的反思在姜文的這兩部電影中得到了別樣的重構和解讀。
(二)浪漫主義、英雄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多重想象
姜文的電影中充滿了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情結。《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少年馬小軍始終懷有一種虛無而又不切實際的英雄主義夢想,他渴望像大人一樣參加戰斗,希望世界發生戰爭而能夠成為一名戰爭英雄。他渴望一段美好的愛情而盡情暢想,又體現了“文革”中的浪漫主義色彩。《讓子彈飛》中,張麻子這個江湖英雄的完美性格也體現著姜文的博大胸懷和英雄主義情結。《太陽照常升起》則集中展現了姜文富有激情的浪漫主義想象。水面上浮起的草坪、彼岸富有神秘色彩的白宮、荒涼的原野、茫茫的大漠、激情的狂歡、火紅的太陽……影片中瑰麗的鏡頭語言展示了姜文無邊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此外,影片中夸張而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情節更是浪漫主義的體現。瘋媽死又未死、小隊長的亂倫、生命交錯時的錯愕、冥冥之中注定的輪回讓整個故事充滿魔幻色彩。但是,無論是英雄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影片都以悲劇結束。《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少年馬小軍因脫離了集體意識后的迷茫與混沌而被朋友孤立了起來;《太陽照常升起》中,前三段故事都結束于一種莫名的死亡;《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得到了勝利也走向了孤獨。在姜文的敘事語言中,他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背后,透露的都是極度感傷的悲觀主義情結。正面與負面、積極和消極、表面和深層的組合,讓影片的思想層級和思想境界都更加立體深刻,從而超越了表面化、片面化和單一化的簡單表達。
(三)影片敘事結構的大膽突破
姜文電影的敘事結構可謂各有千秋,打破了單一化的按照時間或者空間進發的敘事模式,借鑒了西方現代化電影手段而讓影片的敘事結構更加新穎、更加豐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姜文運用一段意識流的敘事方式,展開了成年馬小軍對少年時代的回憶。影片中人物對話和旁白穿插運用,旁白不僅及時點題,而且在一些關鍵情節上更是揭示了影片的主題和思想內涵。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姜文大膽運用了圓形敘事結構和倒敘結構的雙重疊加。姜文借用了曼徹夫斯基《暴雨將至》的敘事模式,從而串聯起了四個獨立而又內在緊密相關的故事。觀眾看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來影片獨立的四個故事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循環。影片以倒敘的方式開始,影片的結尾亦是故事的開始,四個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也有內在的關聯性。這種敘事手法解構了傳統的單線條的敘事模式,一種時空錯亂的安排顯示了姜文的用心和思考,從而展現了深刻的哲學意味:結束即是開始,開始即是結束,一切仿佛沒有終點;一代人來,一代人走;生命生生不息,太陽照常升起;生活中一切的循環往復,早就冥冥注定。時間在三個片段化的故事之間穿越而過,最終影片又神秘地回到片頭,整個敘事結構就像一個圓圈。在這種循環往復中,時間和空間的疊加和纏繞,讓觀眾感受到一種現代主義電影的敘事之美。
(四)從道德文化語境剖析人性
姜文電影中許多人物的行為都不符合特定年代的道德文化語境,而姜文也正是試圖用這一種歷史的滑稽和文化道德的不嚴肅性去深刻剖析人性,展現影片的主題。姜文擅長將電影中的人物置于輿論和道德的風口浪尖,讓嚴肅的歷史變得滑稽幽默起來,以最不符合文化語境的觀念和行為去展現最真實的歷史。這種戲謔化的解讀在標新立異的同時,也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其不同于單一的宣教式的批判和否定,從而完成了另一種層面的真實。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主人公是一群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小混混。影片是以這群小混混的視角來看待“文革”這一段歷史的。影片還對傳統高、大、全的軍人形象做了顛覆化的解讀,完全不符合“文革”時期的道德文化語境。但就是這樣的逆向行進,反而以另一種側面的視角,用最隱蔽和邊緣化的眼光,給了觀眾一種更加真實的感受。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志愿軍戰士李不空對妻兒的背叛、醫生林大夫張狂的性欲以及小隊長和唐嫂之間的亂倫,都明顯不符合當時的時代語境,并與主流價值的描述背道而馳。姜文用這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完成了歡笑背后的嚴肅、荒誕背后的真實深刻。
(五)“置身其中而又不在其中”的高妙
除了主觀視角和客觀視角,姜文的電影更擅長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這種獨立于主觀和客觀之外的第三種視角,才代表了姜文的真正立場,也往往和影片的思想主題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姜文的影片中,充當這“第三只眼睛”的,通常是一些瘋癲和癡傻的人物。但是,姜文更力圖傳達的是——大智若愚。這看似瘋癲和癡傻的背后,蘊藏了深刻的智慧。姜文通過這些獨立于影片主人公之外的人物,傳遞著自己的聲音,表達著自己的觀點。《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有一個呼喊著“古倫木、歐巴”的傻子,這個人物的設置看似多余,但實際上傻子的一舉一動都暗示著故事的走向。傻子始終是馬小軍這個集團內的成員,他沒有被孤立起來。當傻子開心的時候,也暗示著馬小軍和米蘭關系的進一步進展;當傻子哭泣時,象征著馬小軍和米蘭關系的進一步疏離。姜文用一種獨特的視角,在看似不經意間傳遞著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在電影敘事中演繹著哲學式的辯證,是對“愚”和“智”的反思。它脫離了主人公敘述的單一視角,并以此來給予觀眾深刻的啟示。
(六)時代命運和個人命運的交錯感
在姜文的影片中,時代通常充當了一個框架,而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在這個框架下活動的要素。這種時代和個人命運交疊的方式,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命運與時代的必然性有了一種內在的邏輯性和聯系性。個人命運是時代命運的產物,時代命運是個人命運的升華。在姜文電影的人物身上,總能看到時代的印記;而結合影片的時代背景,又不難發現人物的命運更是時代的造化。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馬小軍的童年生活集中代表了當時許多青年人的集體記憶,紅肩章、毛主席徽章、革命歌曲、綠軍裝……富有時代色彩的情節設置濃縮了一個時代的特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梁老師的自殺、唐老師的下放、瘋媽的孤獨更是與大躍進和“文革”時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姜文影片中交織的時代感,令影片本身有著一種高屋建瓴般的卓越和深切的人文關懷,使影片的高度和質感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和飛躍。影片不局限于家長里短的平凡生活,而是從歷史和時代的大視角來參悟人物的命運,使得影片的表達更加宏大、更加深刻。
三、結語
姜文在電影上的美學追求開辟了中國電影的一個新時代。其作品不是簡單的寫實主義,而是用看似荒誕幽默的手法去演繹歷史和現實的平衡;不是簡單追隨西方電影的進程,而是以深厚的民族責任給予家國最深切的人文關懷;其作品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宣教,對隱蔽文化的重新建構和解讀讓他的電影更加深邃而又真實。姜文電影的美學鏡像,不只是技術環節上的精雕細琢,而更多體現在表達方式上的創新以及思想內涵上的深刻。姜文用自己個性化而又充滿激情的想象,不僅在鏡頭語言上展現了自己的理解和創意,更在歷史、政治和道德、文化的荒漠地帶,勇敢地開掘出了一片肥沃的綠洲,使其電影永遠流淌著新鮮的血液,為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動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