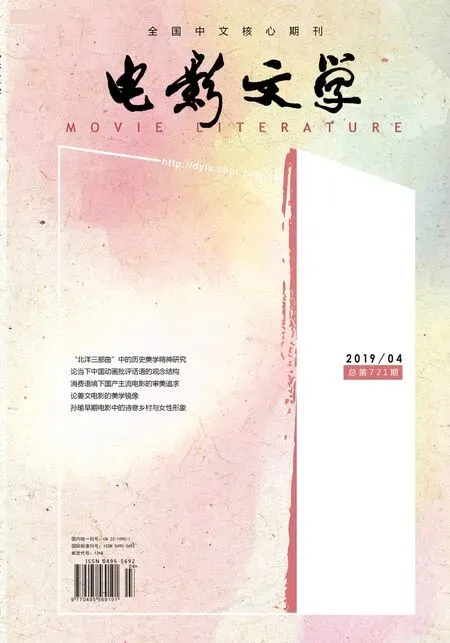文明對話與文化圖騰
——《瘋狂動物城》敘事話語解析
吉俊虎 (山西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電影《瘋狂動物城》講述了在一個虛構的動物世界,兔子朱迪通過努力實現了自己的警察夢想,并破獲了試圖顛覆既有秩序的重大案件。這種傳統的迪士尼主流意識形態影片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它精深的隱喻意義、精細的細節刻畫以及一直延續的“美國夢”小人物勵志之外,其敘事演繹也是值得探討的,故事、敘事視角、敘述者和閱讀諸要素合力推動了影片主題的呈現與深入。
一、故事:“烏托邦”式的反諷世界
英國文藝批評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說面面觀》中提出著名的“故事”命題——“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與“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傷心而死”,前者是故事,后者是有情節的故事,“二者是對同一事件的描述,但后一描述則提供了作者對于材料的詮釋”[1]。電影作為典型的敘事藝術,最本質的功能就是用影像的方式藝術地講故事,“當電影由一種記錄性‘寫實’呈現,演進為以某種‘特定敘述方式’展示故事,從而引起人們的推想、懸念和驚奇時,電影成為嚴格意義上的藝術”[2]26。影像強調的是電影講故事的技術手段,而藝術性強調的是電影講故事的審美價值和精神關照。
首先,電影講的故事具有故事的共性。故事是受一定情感和觀念支配而講述出來的事件,它與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密切相關,而又是“被講述”出來的故事,具有一定的虛擬性。“瘋狂動物城”英文原單詞是“Zootopia”,即“動物園”的“zoo”和“烏托邦”的“utopia”的混合體,“動物烏托邦”本身就具有符號性的隱喻,是對美國社會的虛擬展現。
《瘋狂動物城》講述的故事很多情節、事件都是人類社會的虛擬展示,兔子朱迪的個人奮斗歷程所折射出來的是“食草動物”——社會弱勢群體在主流社會的努力情景,它所隱喻的是亞非拉裔群體在美國主流社會生存的艱辛與面臨的種種不公正及不被認可。影片具有笑點的幾個片段,如樹懶作為車管所辦事員的極低的工作效率是對美國政府工作狀態的一種反諷;獅子市長為了競選而隱瞞動物失蹤是對美國選舉機制的反諷。可以說整個動物城就是美國社會的縮影,“烏托邦”就是美國文明的虛擬,不同動物的生存狀態就是美國社會不同群體的生存狀態。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根深蒂固的防范意識以及偏見是美國種族歧視的縮影,朱迪與尼克的奮斗故事則是典型的“美國夢”的實現過程。整部影片講述的故事就是對崇尚自由的美國社會的一種理想化藝術虛構。
其次,電影講述故事的圖像性決定了故事講述的時間和空間局限,這也讓電影對故事講述的時間流程和空間布局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撥和抗拒,這就需要電影在講故事時運用鏡頭的切換和組合。“電影敘事由于其媒介語言的機械性質帶來的與生活的近親性所導致的非故事性,又由于其媒介語言的機械性質所具有的靈活轉換能力和自由分切組合能力而得到補償。”[2]55《瘋狂動物城》的敘事語言是3D影像技術,它呈現給觀眾更多的現場感。以卡通角色來講故事,這種“幼稚化”的圖像突破了故事講述的原則性限制,可以讓動物形象“天馬行空”。所以在這部影片中,成年人看到政治諷刺和階級偏見,青年人看到追求夢想,兒童看到的則是可愛的動物。
二、視角:文明與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電影講故事就是給觀眾提供一個可觀看的文本,但是文本由誰來構建,是電影講故事的前提。“今天的電影往往是‘從電影到電影’,而以往的電影經常是預先‘扣住的’一個情節的事后的、二次元的圖解,這是顯而易見的。”[3]一般理解,電影講故事是導演按照一定的意圖來表述的,但是觀眾從影片文本中聽到的卻是諸如人物角色、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聲音,這就涉及敘事視角問題。視角是電影講故事的切入點,敘述者是聯系作者與人物的中介,是溝通故事與觀眾的橋梁,對電影敘事視角的定位,可以更好認知作者的意圖與風格。
首先,電影敘事視角主要有兩種,即全知視角與限制性視角。全知視角是指敘述者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他對整部影片故事具有統籌能力,操縱著故事的走向。這種視角敘述自由度大,對于接受者來說也可以對整個故事有較完整的把握,減少理解的難度。限制性視角是敘述者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或無人稱敘述,受敘述者身份、角色的影響,這種敘事是有限制的,贏得的卻是敘事的當下感與真實感。《瘋狂動物城》中的全知視角是影片的作者,他建構了整個故事基本的思維方向。朱迪限制視角,以角色的身份敘述,行動、思考更具真實感。
其次,《瘋狂動物城》的視角折射出的是一種文明、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影片所構建的動物烏托邦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所折射的是美國社會的種種現實。影片在展現動物城的時候,站在一定的視角進行審視與反思,是對美國社會民主和權利的一種思考。個體在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中需要面臨種種偏見,民主之路充滿了艱辛,而個體發展的權利則必須構建在話語權的實現上。正如福柯所說,個體如果無權定義自己,那么就只能活在他人對自己的定義之下,權利與權力不可分割。影片的魅力在于沒有停留在對問題的揭示上,而是試圖對理想社會進行構建。“烏托邦”式的和諧關系能夠維系,個人的夢想能夠實現,正義得以伸張,罪惡得以懲處,這些都說明不同文明和文化在不斷的沖突融合中走向和諧,這也是對理想世界秩序的一種期許。
三、隱性敘述者:意識形態的“正確”與文化霸權
敘述者是敘事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敘述者的聲音決定整個敘事文本的意義生成,這里涉及敘述者與真實作者的關系。
真實作者與敘述者是錯綜復雜的兩個敘述主體。真實作者是創作敘事作品的人,是作者,是編劇,是導演,他是現實中的生命;敘述者指的是講故事的人,他是文本中的具體存在,是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或是一個角色或是整個故事的“引路人”。所以羅蘭·巴特說:“敘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紙上的生命’。一部敘事作品的(實際的)作者,絕對不可能與這部敘事作品的敘述者混為一談。”[4]
根據敘述者與文本的親密關系,敘述者可以分為異敘述者與同敘述者。異敘述者是敘述者不參與到故事當中,他置身事外講述故事,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可以對整個故事進行高屋建瓴的架構。而同敘述者是指講故事的人同時又是文本中故事的角色,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根據敘述者的主動性,敘述者又可以分為自然而然的敘述者和有意識的敘述者。前者強調敘述者隱藏在文本中,盡量不露出敘述者的痕跡;后者強調的是敘述者意識到或者干脆在故事中說出自己的存在。根據敘述者對文本的干預程度又可分為客觀敘述者和干預敘述者。客觀敘述者只充當故事的講述者,而不顯示自己的主觀態度和價值判斷;干預敘述者則是在文本中敘述者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主觀感受,可以對故事中的人或者事件發表個人的看法和評價。
首先,影片《瘋狂動物城》的敘述者是以兔子朱迪為核心的故事講述者,欲講述兔子朱迪以及狐貍尼克等動物的全部故事。這個故事可以是美國社會的故事,也可以是整個世界秩序的問題,所宣揚的是一種成人寓言式的政治意識形態。《瘋狂動物城》的敘述者既有異敘述者的特點又具有同敘述者的影子,朱迪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它參與到故事當中,但又具有一定的“代言”性質,它是“美國夢”的代言人,也是美國理想社會的代言人。動物城里復雜的生態環境就如現實中復雜的社會關系,不論個頭大小、食肉食草,雖然時而有隔閡與摩擦,但最終都能在自由、平等、博愛、包容的動物城里找到自己的歸宿并和諧地共存下去,正是本片宣揚的“美國夢”的終極理想藍圖。
其次,影片的敘述者是有意識的敘述者具有較強的干預性。影片所宣揚的動物烏托邦是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的縮影,但是對權利與權力的描述是集中而深刻的。這種“和諧的世界秩序”是一種符合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確”的思想意識,是美國用來宣揚自己理想世界秩序的一種藝術化方式,說到底是西方文化霸權的一種表現方式,因為影片《瘋狂動物城》一直在沿襲迪士尼這種保守的政治說教,隨著影片在全球市場的蔓延,其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也在全球散布,這正是文化霸權全球擴張的一種主要途徑。
四、閱讀:接受主義美學時代的電影敘述話語
接受主義美學認為文本的真正意義存在于文本接受的過程當中。受眾在閱讀文本時,他的經驗、趣味、文學素養以及意識形態、理想等綜合素質都會對閱讀產生一種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期待視野”。因此,整個文學史就是不同的讀者閱讀的歷史,是不同的閱讀效果的綜合,“文學史——效果和接受的歷史,這一破天荒的大膽設想,對于傳統的文學史研究,不啻是一個有力的挑戰,也是堯斯對解決‘文學史悖論’這一難題所提出的答案”[5]。對電影史同樣適用。
《瘋狂動物城》具有多元化的閱讀理解效果,不同的觀眾觀看它會有不同的閱讀期待。作為一部動畫片,它的主要觀眾應該是兒童,影片也很好地滿足了兒童對天真童趣以及可愛的動物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說兒童從影片中所觀賞到的是兔子以及狐貍對整個動物王國陰謀的破獲。同時影片也是一部成人“寓言”,處于奮斗期的青年所觀賞到的是像朱迪與尼克等個體的奮斗過程,以及個體通過努力實現夢想的理想世界;政治學者看到的則是影片所透露出的關于平等、民主等的構建問題,以及和諧社會秩序的建立問題;文藝理論者所看到的是整部影片所透露出的文化偏見以及文化背后的根由;國家的弱勢群體看到的是關于面對強勢群體怎樣保持警惕以及怎樣合理實現理想的問題;強勢群體看到的則是關于整個社會秩序怎樣才能更加合理的問題,以及既有的社會秩序的維護問題……
《瘋狂動物城》故事文本呈現的“召喚結構”形成了隱含的讀者。接受主義美學認為文本意義的表現離不開讀者的閱讀和參與,但是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空白”和未定點,它本身形成一種“召喚結構”,它是讀者閱讀再創造的一個基本前提。文本的這種“召喚結構”就形成了隱含的讀者,二者的有機契合讓文本的意義完全表達出來成為可能。
《瘋狂動物城》呼喚不同的讀者對文本做出不同的解答和闡釋,它既包括了個人奮斗主題的召喚、種族平等問題的召喚,也包括對既有社會秩序批判的召喚。而影片的隱含讀者基本鎖定在兒童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對影片做出了符合自己閱讀期待視野的解釋,從而構成了《瘋狂動物城》影片的解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