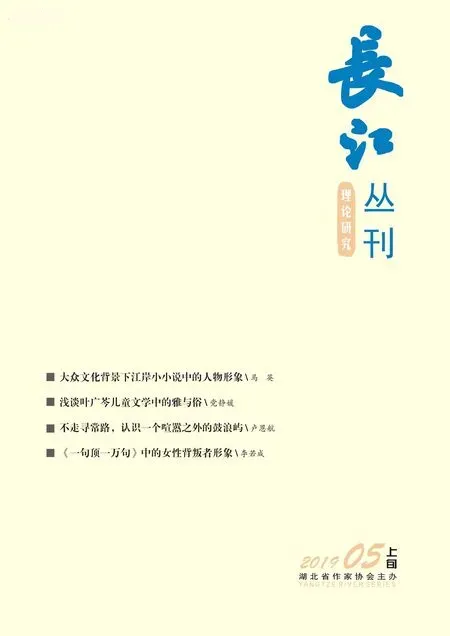2018年湖北短篇小說述評
■
“新時期”以來,湖北的短篇小說創作雖然不像中、長篇那樣耀眼奪目,但也從未隱匿過其鋒芒。劉富道的《眼鏡》《南湖月》,王振武的《最后一簍春茶》,俞杉的《女大學生宿舍》,李德叔的《陪你一只金鳳凰》,姜天民的《第九個售貨亭》,楚良的《搶劫即將發生》,映泉的《同船過渡》等相繼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李傳鋒的《退役軍犬》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些都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本省的文學創作。盡管90年代以后短篇小說在全國的地位因文學的去意識形態化而日漸衰落,湖北的中篇小說更是強勢崛起,但由于湖北的短篇小說創作一向比較沉穩質樸,緊貼現實生活,因而還始終保持著其活力,許多以中篇見長的作家也頻出短篇佳作,而曉蘇更是全國有名的短篇創作高手。最近幾年,湖北的短篇小說創作還呈現了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即創作群體的構成比較復雜,既有專業的作家,也有許多業余作者,既有基層工作者,也有高校的教授學者,年齡層次的跨度也比較大,從“40后”到“90后”,老中青三代濟濟一堂。這大概與湖北向來比較重視基層作家、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培養有關,形成了比較良好的文學生態和創作氛圍。因此,縱觀2018年湖北的短篇小說,雖在質量上參差不齊,有些許不足,但也顯得比較豐富、多樣,注重在本土的社會語境中探索短篇敘事的可能性,出現了一些令人稱道的作品和值得關注的傾向。
一
湖北作為農業大省,有著比較深厚的鄉土文學傳統。許多出身于農村的作家雖身在城市,在情感和心理上卻偏向故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打工潮的興起,傳統鄉土社會的瓦解,必然會激起他們強烈的鄉土意識,并產生不同的敘事向度和美學風格。
在去年湖北的短篇小說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是追憶故土的風物人事,或表現鄉間的情義倫理,抒發“僑寓者”的眷戀和詠嘆之情的。由于湖北的地域差異非常明顯,盡管同樣是對故鄉的美好回憶和想象,這些作品仍然具有不同的審美內涵和情感體驗。在舒飛廉(鄭保純)的《桫欏船》《雉回頭》中,鄉村裹挾著個人年少時的迷夢和力比多過剩的激情,甜蜜而憂傷,與多年后庸碌的生活相比,顯得飄渺幽絕,但也是自在自足的,連喪禮都是那樣的莊嚴而不悲戚,熱鬧而不喧嘩,就像保明們透過刨花看去,模糊又鮮活。浠水的夏艷平在《換面》和《的確良》中,以意識流的手法表現兒童或農婦單純的情思,全憑感覺繪制了一幅意境空靈、出世般的鄉村生活場景,自然地令人想到了早期廢名對其故鄉黃梅的記憶,由于浠水與黃梅同屬鄂東黃岡,兩人之間的相似性,既可能是一種自覺的傳承關系,也反映了夏艷平對鄉村永恒性的想象。而與廢名同鄉的於可訓,在《男孩勝利漂流記》中以筆記體的形式書寫故土的傳奇人事時,則去掉了那層晦澀的彼岸色彩,而保留了生活的簡單趣味,深受黃梅禪宗文化的影響,更多地在自然人性中發現善念。余書林的《相牛者》《挑擔子剃頭匠》《水月村的陳年往事》《與村長有關》等作品,則通過對狡黠而不失純樸、精明而又善良的鄉間匠人和普通村民的速寫,回憶了一種充滿諧趣、苦中作樂的鄉村生活。韓永明的《栽秧飯》,在物質與精神的悖反性主題中展現傳統鄉土社會的人性美與人情美。“栽秧飯”作為雨村人在饑荒歲月里每年一次的集體盛宴,不僅是對因吃草根樹皮而虛弱的身體的一種補償,也是人們在艱苦勞作中的一次精神享受,但當吃栽秧飯的臘肉被盜后,雨村人卻表現出一種樸素而莊嚴的情感,牛子夫婦的剛烈決絕、袁老五的覺悟擔當、村長的仁慈善良、村長與牛子的相互幫扶,都構成了傳統鄉村情義倫理的不同側面。段吉雄的《討水》,也將人物放在一種貧乏艱苦的生存環境中加以表現,夫婦之間在晝夜不停的勞作中的情義同樣令人感佩。劉益善的《老虎杌》《西山有座塔》等作品,雖然并非以他自己的故土為情感寄托的對象,卻也表現了傳統鄉土社會中莊重、古樸的人心與人情。這些回憶性的作品或明麗輕快,或婉轉低回,洋溢著濃郁的抒情色彩。
一旦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距離被拉近,懷想式的抒情便讓位于對現實鄉村冷峻的審視。雖然這些反映鄉村現狀的作品很少正面表現當下農村的社會變革,也無力揭示歷史發展的深層脈絡,卻始終把“人”作為藝術表現的中心,關注普通勞動者或隱或顯或獨特或普遍的生存經驗與現實境遇。曉蘇的《吃苦桃子的人》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收獲。小說以人帶事,用白描手法塑造了“憨寶”這一表面木訥、笨拙、古怪,實則善良、純樸、無邪的人物形象。憨寶之“憨”在根本上是因為他與那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鄉村的格格不入,他反復吃苦桃子的動作中有著他的與世無爭、與人無害、隱忍沉悶、真誠老實,他朦朧地意識到滋生的欲望可能成為洪水猛獸,會擾亂他的心智,于是本能地抵御著外界的誘惑。然而,他既不是智商低下的傻子,也不是道德高尚的苦行僧,他的自我克制完全是出于一種執拗而質樸的品性,沒有半點的虛偽與矯情,對于他自身無奈孤苦的處境也沒有任何的委屈和怨憤,因而顯得十分自在和純粹。實際上,曉蘇塑造了不少這樣至情至性的人,這與他對于底層勞動者的熟稔和體貼,認同他們的情感愿望所代表的民間倫理有關,他很少對他們的言行舉止妄下論斷,在敘事上顯得比較從容,因而在《夜來香賓館》中,他能夠捕捉到年近半百的農村婦女對于生活未曾磨滅的浪漫情懷,也能夠表現她在遇到舊情人后要求共度良宵的坦率果斷;在《說的都是一個人》中,他能夠發現在龔喜那由窮困坎坷的生活造成的冷漠庸俗中,還有基本的操守和不忍人之心;即使是在反映被金錢權勢所擺弄的人倫情感的《同仁》,尖銳的嘲諷也在知恩圖報的喜劇氛圍中化為同情與欣賞。與此不同,許多描寫現實鄉村人物的作品則顯得較為局促緊張。比如,葉牡珍的《塆落深深》、陳旭紅的《柔情似水》,同樣反映農村婦女的情感與倫理沖突,她們卻始終處在一種煎熬和壓抑的狀態中,最后只能以出走的形式擺脫其存在的不自由;喻之之的《欒樹欒樹》,同樣書寫善惡沖突,卻展現了人性惡的猙獰,及其對于良知的步步緊逼,一種深深被傷害的情緒彌漫其中;周萬年的《尋豬記》,同樣反映權勢對人心的左右,矛盾沖突卻是在因果報應的覺悟中被化解,而喜劇的結局并未改變作品的憂憤基調。
不少作品都注意到了鄉村生活方式和人倫情感的變化,給老一輩農民帶來的困惑與不適。呂先覺的《煙火行》,細致地刻畫了一對因受惠于精準扶貧而即將搬離故居的老夫婦在轉煙火時的矛盾心理。作為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下的最后一代農民,他們既有對新生活的向往,也有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留戀和不舍。小說通過極富表現力的動作和極具個性的對話,表現了他們自我克制而又不能自已的內心沖突,以及那種表面粗疏平淡實則細膩深沉的夫妻感情——這正是根植于農耕生活的傳統鄉土倫理的集中體現。秦祖成的《分家》也描寫了農民老夫婦之間相濡以沫因而難舍難分的感情,卻又進一步揭示了這種感情在兒女那里的被漠視和不理解。小說中,張大芬夫婦分家后的失落孤獨與相互牽掛,竟激化了互有嫌隙的兒子兩家的矛盾,于是他們決定不要任何人養活,最后不知所蹤。葉牡珍的《痛詞》與此異曲同工,只不過“老伴”換成了“棺材”,兩代人的隔膜中更多了生死倫理的沖突。在一個以金錢衡量一切的社會中,丁道士、田老頭等人為棺材而舍命抗爭,顯得凄涼而悲壯。晚年的衣食無憂,在子女眼里就是“享福”,老一輩農民在乎的卻是家庭的團結和睦,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和價值觀念上的理解和尊重,這種精神需求實際上正是對于傳統人倫情感的一種自覺維護。秦祖成的另一個短篇《人物》、鄭廷局的《搭把手》等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這一主旨。對農村老年群體的關懷,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些作家對于傳統倫理觀念的強烈認同,因而這類作品更像是時代的挽歌,整體上顯得較為沉郁。劉會剛的《鄉村葬禮》、陳章華的《故人沐浴》,顯然正是對傳統鄉土社會衰落的隱喻,無論是了卻死者未了的心愿,還是給故人沐浴入殮,都不過是一種最后的也是最深情的告別儀式。
打工潮背景下留守人員的現實困境,仍然是去年湖北短篇小說表現的重要領域。閻剛的《狗事》,圍繞留守婦女的性問題描寫了婆媳之間的一場防范與越軌的倫理沖突。在這場沖突中,兒媳王會玲與婆婆柳成英利用一條狗斗智斗勇,始終未能敞開心扉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故事結局是在王會玲等待下一個圈套時,婆婆卻把狗賣給了狗肉店,說狗被養得太胖不能叫了。這實際上意味著婆婆的妥協,但這種妥協不完全是出于理解和同情,而包含著更多的無奈,因為她也不愿看到兒媳的偷情敗露后的“雞飛蛋打”。相比之下,李旭斌的《夜半知了聲》中的田蕙蕙就比較幸運,她的公婆對她的孤寂難耐和滿腹牢騷萬分諒解,最后決定挑起照顧她的偏癱父親的擔子,讓她能夠安心地隨丈夫出去打工。朱華遜的《村事》,則將留守婦女的辛酸苦痛表現得極為沉重,這里有村長對婦女的禍害,有婦女之間的相互嫉妒,有村民的流言蜚語,使得留守婦女的整體生存狀況令人堪憂。譚巖的《風雪回家路》中,則以男人留守、女人打工的模式,反映了因打工而生的流言、猜忌給整個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也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農村婦女生存的艱難。韓永明的《我的好伙伴順子》,則反映了留守兒童的孤獨和危險處境。這篇小說同時也揭示了整個鄉村的困頓與衰敗,打工固然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但那些沒有能力出去打工或者因打工而喪失能力的人,則仍會處在貧困之中,而且打工帶來的鄉村空心化、倫理失序、道德淪喪等問題,構成了留守人員殘酷的生存背景。這種現實對于老人來說,則意味著死神的隨時降臨。喻長亮的《遠山》中,遠山姆沒能等到傻兒子回家就被狼咬死了。滕樹勇的《背老大》中,兒子兒媳為了擺脫背老大的命運而決然離去,留下孫女丫丫和林大漢相依為命,當丫丫考上大學即將踏上新的征程時,林大漢也被洪流沖走了。劉浪的《消失的村莊》,則以寓言的方式描寫了鄉村隨著老人們的相繼死亡而消失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莊嚴的,也是狼狽的。
二
對城市的書寫是短篇小說的強項。顯然,人口密集的地方,故事更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而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千差萬別的故事瑣碎而短暫,若不是放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一切似乎都無力支撐宏大的敘事結構。契訶夫的小說早就啟示我們,井然有序卻平庸乏味的生活不需要大刀和闊斧,更適合用一根針去刺破它表面的平靜,去刺痛它的麻木神經。要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內里,揭示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反映個體的心理、情緒和情感,短篇小說是再合適不過了。以短篇小說書寫城市生活也是“新時期”以來湖北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特別是始于劉富道,經方方、池莉,到鄧一光等人創作的“漢味小說”,充分發揮了短篇小說靈活多變的優勢,形成了鮮明的地域色彩和獨特的審美內涵。
去年,扛起湖北城市文學大旗的是一批青年作家,與前輩作家相比,他們更傾向于咀嚼一己的悲歡,表現個體內心的感受,而缺乏對充滿煙火味的市井生活的熱情,更無意于“以小見大”,關注個人以外的歷史走向和社會語境。因此,“家務事,兒女情”首先成了他們表現的一類題材。謝絡繹的《多聲部》反映的是產后育兒引發的家庭關系的緊張與沖突。“火星四濺的埋怨”、丈母娘“平平淡淡的支使和說教”、新生兒“沒完沒了的哭鬧”,構成了環繞在范斌身邊的“多聲部”。表面來看,這是一個在婚姻中受傷的故事,范斌是無辜的,對于照顧孩子,他想插手而不得,他不聞不問亦不可,他既是家庭生活的“多余者”,又必須成為“在場者”。但小說在對世俗經驗的新寫實式的細密敘述中,似乎又別有深意,當丈母娘的“過分”被揭示為一種對女兒的自私的疼愛時,范斌的“多余”與“在場”就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被戲弄和被迫害,而是一種被設定的姿態。這種姿態似乎包含著作者對于人與人、特別是男女之間關系的一種獨特感悟。肖靜的《水霧》,同樣寫到了生孩子給夫妻感情造成的創傷,但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不似范斌這般隱忍深沉,不能悟透生活的荒謬本質,試圖在婚外情中獲得拯救,卻被欺騙了感情,而女主人公也同樣因為單純而深陷情感的圈套。馬桂蘭的《本命年》揭示了情感與婚姻的錯位,同樣表現了生存的荒誕性。無愛的婚姻與沒有婚姻的愛,到底哪一個更值得珍重?如果說多年前張潔以《愛,是不能忘記的》通過婚外情表現的是道德對人性的束縛,那么《本命年》則試圖用良知救贖人性。然而,老嚴的去世和老黃的出軌及離婚請求,卻將蘇景的這種良心上的不安與愧疚都驅散殆盡,這個不無荒誕的結局給小說增加了一層悲觀的色彩。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寫,似乎成了女性作家的專屬。然而,丁東亞卻以其男性的深邃視角反復咂摸婚姻的本質。《人間無恙》中,蘇琴和穆月白之間婚姻的外衣典雅華麗,內里卻千瘡百孔、狼狽不堪,但這不像許多女作家描寫的那樣是因為情感與婚姻的錯位,而是由人性的殘缺所決定的,他們的女兒也必然帶著殘缺的印記。小說中無處不在的欲望與痛苦具有一種先驗性的色彩,實際上是個體生存的孤獨本質的表現。丁東亞的語言細膩縝密,有著濃重的文藝腔調,外在的雅正與內在的凄絕,似乎也對應著他對婚姻和人生的感受。從婚姻這一世俗經驗出發,又超越這種世俗經驗,上升為一種存在之思,正是許多女性作家所不及之處。
女性的情感心理和生存處境也是許多年輕女作家所熟悉的題材。張慧蘭的《托》,描寫了一個離異的中產女性在婚介公司一面當托,與不同的男性相親,一面又對其進行審視,物色心儀對象的經歷,但最終被欺騙受傷害的還是自己。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給渴望獲得情感慰藉的現代都市女性的內心罩上了濃重的陰影。于是,在張春瑩的《鋼琴別戀》中,大齡女鋼琴師對于未婚成功男士的迎與拒,正是內心惶惑不安的表現,對外界的將信將疑,使她無端生出了許多的自尊與自卑,而這兩種心理糅合在一起產生的冷酷與無情,必然會在兩個人親密接觸后變成一種折磨和凌辱。謝絡繹的《蘭城》,繼續了她對于城市外來女子的觀察。小說中從農村來到省城的女白領,內心有著揮之不去的自卑感,這使她在遇到心儀對象時只好通過自欺和想象的方式獲得自我的優越感。謝絡繹對于其筆下的人物總是溫柔和仁慈的,她不忍心這位無根無系的外來女子的幻想破滅,而給了她一個美好的結局。劉琛琛的《遁》,通過閨蜜三個不同的生活,表達了對于女性自身價值的思考。彭亞玲以色侍人,因插足而嫁給有錢人,過著任性花錢和拼命保養的富貴生活;程靈兮在事業單位上班,有點才華,閑時看書寫文章,生活平靜;顧丹丹和老公開了個蛋糕店,累死累活也就夠養家糊口。一時來看,彭最有架勢,程最超脫,顧最平庸。但彭最心虛,得不到真心相待,怕“色衰而愛馳”,生活中并沒有她的位置;程最憋屈,老公花天酒地,沉溺賭博,內心也并不淡定,只好遁入小說的虛構世界中;顧最充實,有體貼的老公可以偎依,靠自己的日子也最有盼頭。作者最后以彭的離婚,程的消失和顧的生意越來越好結局,觀念是明確的:女性在生活中的位置和價值,是任何人都給不了的,必須放下幻想,直面現實。肖靜在《我來安排》中則刻畫了一個無論在家庭還是在事業中都得親自出馬的女強人形象。恐怕沒有多少女人天生地能干剛強,把一切負擔都扛在自己身上,但當她不愿向生活低頭、不愿喪失尊嚴和價值時,她已經變成了生活的強者,而不得不負重前行,這樣的女人令人敬佩但也令人心疼。
對于小人物灰色人生的書寫,構成了城市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謝絡繹的《當我面向太陽時》,聚焦于城郊青年的生存狀態。小說中的“我”出身卑微,從小缺乏仁慈的母愛和溫馨的家庭,唯有垃圾場是“我”身心的休憩之所,但不是因為“我”甘于平庸,而是因為垃圾場給我的東西太多,除了吃的、用的,更重要的是“眼界”,還有懂“我”、不愿“我”被這個地方毀掉的管理員“貓師傅”。當“我”從垃圾場撿到一本飛機構造的書后,就有了自制飛機、帶“貓師傅”離開這里的計劃。為了這個計劃,“我”上了技校后進了汽車生產車間,這工作在別人是枯燥無聊的,在“我”卻因為與夢想有關而有意義。但“我”卻因為認真上進遭到工友的嫉恨而被打一頓,再次被打入一種灰色蕪雜的境地。小說最后,“我”又回到了垃圾場,完成了飛翔的計劃,面向太陽而去。與《蘭城》一樣,這個短篇的結局也是詩意美好的,主人公的夢想和意愿都得到了實現,表達了謝絡繹對于筆下人物的深切同情和愛惜,但又不禁讓人深思,他將飛向何處,又是否能夠安全著陸呢?同樣是關于“飛翔”的故事,宋離人的《迎風飛翔》卻讓人質疑“飛翔”的意義和價值。小說中的楚生,與成熟懂事的哥哥蘇生不一樣,他任性沖動,執著于愛情和理想,不會為了家庭而犧牲自己,不甘于按部就班的平庸生活,考上大學而后事業有成,徹底遠離了那在他眼中“愚魯而灰色”的黃泥壩。他說他哥哥“就曉得按部就班的生活是幸福,被命運安排好的人生是幸福的”,這樣的人生過程“多像豬的一生”,但他卻從未意識到,正是因為哥哥安于這樣的生活,無怨無悔地付出,才成就了自己的“飛翔”。這樣的“飛翔”終究顯得有些輕浮,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在廢斯人的《去某一個地方》中,作為政府辦公室文員的明志,也是個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他甘于現狀,對生活已經徹底喪失了激情,更沒有想過要“飛翔”,但他潛意識中仍然想要“去某一個地方”,這種沖動被喚醒是在他遇到了“與眾不同”的安迪后,安迪朋友圈里環游世界的照片讓他想到了自己因喪失勇氣而沒能成行的川藏線騎行,因此又把這種沖動變成了對安迪的一往情深,但當安迪最后坦白自己在旅行中被孤寂折磨得死去活來,“發現人生的深度不是一本回憶錄,不是生與死,不是一味地離開和路過,而是平凡地生活”時,他似乎才真正得到了拯救。劉浪的《失蹤》,揭示了北漂青年的艱難處境。阿慶和“我”曾為了維持生計,干起了幫人尋找失蹤寵物的勾當,當周太太的狗失蹤而無果后,阿慶為了兩萬塊的懸賞,沒有放棄對狗的尋找,為了弄清楚狗是如何從監控視頻中消失的,他跑到現場一次次像狗一樣爬行,最后竟離奇失蹤。人與狗的相似結局和不同命運,既揭示了小說的異化主題,也產生了一種反諷的藝術效果。此外,鄭新能的《人事問題》,周承強的《文行天下》,熊湘鄂的《敬酒》也都揭示了小人物生存的悲劇性,那種謹小慎微、命運被人左右、情感被人愚弄的處境,著實令人唏噓。
打工者的生存境遇,也是許多作者關注的話題。韓永明的《在城里演孫猴子》、譚巖的《愛穿制服的人》、廢斯人的《坐北朝南》,重點描寫的都是打工青年在坎坷的遭際中走向自尊、自強和自覺。這些新一代進城務工者雖然還有著農民的身份,卻不會也不愿再回去種地,而有著扎根城市的強烈愿望,他們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城市底層的重要部分。但與城市中其它階層不同,他們身上具有一種難得的清新剛健的氣質。其中有很多人不斷換工作,居無定所,但又對生活充滿信心,生機勃勃,對城市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因而又格外敏感和自尊。《愛穿制服的人》中的章萬貴對于當保安充滿激情,正是因為這份工作不僅讓他干凈整潔,而且使他更自信更有存在感,即使后來因為家庭的變故不得不當泥瓦匠,他仍然抽空穿上制服去當馬路志愿者。顯然,盡管章萬貴的尊嚴感不是來自于對勞動自身的肯定,而更多的是受外界的刺激而引起的虛榮的表現,但他對尊嚴的維護和強烈的自我意識還是很令人感佩的。相對而言,女性打工者的心理更為脆弱,因而其處境也更為艱難。章國梅的《護工》反映了階層的隔膜和矛盾對女性的傷害。趙麗的《青枝綠葉》則描寫了青兒在城市中坎坷悲慘的遭遇。像青兒這樣十幾歲就出門打工的女孩所面臨的困苦,除了有來自于男權社會的傷害,也有著其自身的局限性,單純善良有時候會變為軟弱無能,從而輕信于人、不懂得如何自我保護,性教育的缺乏則導致她一再被欺騙,作為情欲的對象也往往被欲望所捕獲,而無力主宰自我的命運。
三
顯然,對于鄉村敘事與城市敘事的分類考察,不可能勾勒出去年湖北短篇小說創作的完整面貌。作為近年來湖北中篇創作的中堅力量,曹軍慶、普玄、陳應松等人去年為數不多的幾個短篇作品,雖然也脫離不了城鄉變遷的社會背景,但與前述關注個體生存經驗的小說不同,它們更注重對短篇小說敘事可能性的探索,從而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
曹軍慶似乎一向都比較重視話語形式的獨立性,試圖對我們所熟悉的現實世界進行重新命名并有所發現,因而他的小說具有先鋒探索的特質,很少受到題材或主題的拘束。他在去年的兩個短篇《時差》和《天上的街市》,一者寫“嚴打”,一者寫電信詐騙,卻都“只取一點因由”,打破傳統的敘事法則,讓話語自身產生新的經驗結構。在這兩篇小說中,情節的串聯都不是依靠因果關系或性格沖突,而是“我”的生命時間的流動,因而純粹是一種自我對世界的發現過程。《時差》中,從“我”和同學造訪女工多的棉紡廠,卻被小靜趕走,到“我”回去路上腿受傷而碰到王老師,去她家讓溫克儉包扎傷口,后來溫克儉在“嚴打”中伏法,再到王老師多年后回來講述溫克儉和小靜的關系,最后在2017年的牌局上認識老李,得知溫克儉被陷害的真相,人物的關聯或故事的成型都是因為“我”的偶然發現,敘述者“我”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而是一個逐漸從主流意識形態中逃逸的感性個體。無怪乎當同學后來問“我”的腿摔傷是不是故意的時,我有點莫名其妙。這恰好體現了文學敘述對歷史敘述的解構。在“嚴打”時期,“我”和同學的荷爾蒙旺盛無處發泄,溫克儉和小靜(最后出家)的感情被壓抑并被消滅,把溫克儉當“延時器”的衛生院院長荒淫無度卻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不僅是歷史的荒謬所在,更是對歷史的反思喝隱喻,“嚴打”時期的禁錮與后來欲望的泛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只是“時差”的關系,個體就成了歷史的“炮灰”。同樣,《天上的街市》中,“我”進入響堂村并知道響堂村是個什么樣的村子也是偶然的,只是“我”去戒毒所采訪后想要去白龍山看看,忘了旅店老板的忠告,下山晚了而迷路,被羅爺帶到這個謎一樣的地方。這個小說與《時差》的不同在于,它更多地利用時間的塑形催生了一種陌生的經驗,使得“我”與響堂村的關系如同K與《城堡》的關系,雖然“我”的好奇心使我不斷逼近真相,逃離了“迷宮”,但“我”卻陷入了道德情感上的困惑。響堂村人為了生存為了尊嚴,走上了電信詐騙的不法之路,但誰又能夠剝奪他們生存的權利?他們對于帶領他們致富的孫叔偉的保護,在他們那里正是一種維護正義的抉擇。對此,“我”又無力反駁,只有逃逸。
普玄在《生·紙條》中,通過一場因人情禮金引發的血光之災,不僅僅折射了金錢社會人情的變味和人性的扭曲,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個關于如何拯救人性、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世界不可調和的關系的問題。當得知五一之后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再請客送禮時,“我”的爸爸即副科長決定把“我”提前剖腹降生,給“我”辦“九朝”,想收回送出去的人情禮金。而副科長最在意的是,曾經收破爛如今靠自己的關系而發達的李保衛能否把他送給他的五份人情一次性還回來,因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面子問題。李保衛與副科長都是劉姥姥一手帶大的孩子,可謂情同手足。但當他只送了一份禮金時,副科長當眾狠狠羞辱了他,因而被刺死。顯然,是人物的“擰巴”導致了人性的罪惡,這似乎是偶然的事,但也并非不可避免。普玄通過另一條故事線,即一種超現實的存在,表達了他的化解之道:“順其自然”。曾被孩子們從死亡邊緣救回的劉婆婆發愿要帶夠一百個孩子,并且見證他們的降生,卻在作為第一百個孩子的“我”降生時昏迷不醒。因為“我”的提前降生是違背自然的,“九天司命還沒有下命章”,沒有人敲鑼打鼓迎接“我”,也就不能把她喚醒。“順其自然”這個極為簡單樸素的道理,在生活中常常變成一種雞湯式的警句,普玄將之與人性、生死問題關聯起來,還原其屬于傳統道家思想的文化意蘊,其現實意義就變得深刻起來。
陳應松的《趙日天終于逮到雞了》,用后現代的黑色幽默手法記敘了一群“耐不住寂寞的老伙伴”進山抓雞的過程。無論是從陳應松自己的創作歷程來看,還是放眼全國的短篇創作,這都是一篇獨具一格的小說。在這里,激烈的憤慨或高亢的抒情已經被調侃式的反諷所替代,虛構與真實的界限也被模糊了。“我們”相互的斗嘴打趣,搔首弄姿的擺拍,對于鄉村物事的一驚一乍,對于老屋的掠奪,抓雞時的鬧騰,都在“生活流”的語言結構中自動呈現出荒唐、滑稽的一面,城里人對于鄉村的獵奇、向往和贊賞的背后,卻是對其內在的衰頹與病苦的漠視,是享樂主義和商品意識的作祟,特別是從失去了主人而快要餓死的狗那里奪走狗食盆,以及把田老頭拜托尋找兒子的尋人啟事當作廢紙擦拭嘔吐物又扔掉的細節,將他們的虛偽、矯情和冷漠暴露無遺。雖然陳應松的小說一向都存在著一種城鄉對立的模式,但這里卻多了一層悖論性的關系,即如小說中城里人因對鄉村矯情的向往又給死氣沉沉的鄉村帶去了一點生氣,也因為他們對鄉村的隔膜而成為被欺詐的對象。可見,陳應松對于城鄉關系以及知識分子與土地的關系的認識和反思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簡單和明確。
此外,作為90后的劉浪可以說是湖北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近幾年他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形式風格上都比較多樣。與湖北的幾個差不多同齡的寫作者(比如廢斯人、丁東亞等)一樣,他具有嫻熟的敘事技巧和自覺的文體意識,西方現代派包括中國80年代的先鋒小說對他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去年的幾個短篇中,除了《消失的村莊》《失蹤》等關注現實問題的,還有比較注重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辨的作品。《尋找詩人“芒”》講述的與其說是“我”與網友盲詩人見面的經歷,不如說是“我”對于存在的發現與接近。語言與存在的關系,在劉浪這里無疑是海德格爾式的。小說中“我”對詩歌的熱愛,對詩人“芒”的崇拜,也正是試圖超越表象世界而抵達存在自身。但“我”在等待并尋找他之前,并沒有意識到正是他的眼盲讓他能夠發現存在,并寫下那些令“我”震驚的語言。當“我”閉上眼睛尋找他時,“我”才真正進入了他的詩歌,感受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才發現眼睛和耳朵都是“我”擺脫生活的困頓、超越俗世的障礙。因此,當芒真正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就不需要他了,他對“我”來說變得索然無味了,特別是在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將要移植角膜而重見光明時,“我”感到了失落,并懷疑他的才華會不會因此而“瞎掉”。
以上所論,皆舉其犖犖大者。雖然2018年湖北的短篇小說創作取得了不小的實績,但就短篇小說所能達到的藝術成就而言,還是稍嫌不夠。短篇小說是一種獨立的文體。恐怕還有不少寫作者沒能意識到這一點。短篇小說與中、長篇的根本區別,顯然不在于篇幅的長短、字數的多少,而在于題材的選擇、情節的裁剪、結構的安排等方面的不同。短篇小說取材比較廣泛自由,觸角也就比較敏銳靈活,能夠從不同側面對社會生活作出及時的反應,也能捕捉到個人模糊的感受和瞬間的印象,并賦予其獨特的審美內涵。相對于中篇和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更為注重小細節、小事件、小人物、小心緒自身所包含的價值和意義,因而它不可能敞開了去寫,要求有更為嚴格的剪裁,更為精巧的結構,語言更要富有表現力。可以說,短篇小說是一種比較理性節制而又靈活自由的文體,需要極高的表現技巧和對生活的細致觀察能力,但也因此蘊含著巨大的創新潛質,成為許多作家進行文體實驗或施展才華時所偏好的一種敘述形式。無怪乎有人說優秀的短篇小說家都是文體家。不能意識到短篇小說的文體特征,或者干脆以為它就是“短故事”,必定會有人漠視其存在的價值和藝術探索的品格。湖北的短篇小說作者許多都是來自于基層的業余作者,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許多沒有太多經驗的寫作者很自然地會采用一種貌似簡便省力的敘述形式,而一些訓練有素的作家由于主客觀的緣故又不愿寫短篇或寫得比較少。這就使得去年湖北的一些短篇小說顯得比較粗糙,或剪裁不夠嚴格,或結構拖拉松散,或者主題過于直白,或人物形象蒼白模糊,或過分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的短篇小說作者在創作實踐中逐漸去克服,并充分發揮這一文體的優勢,創造出更多的藝術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