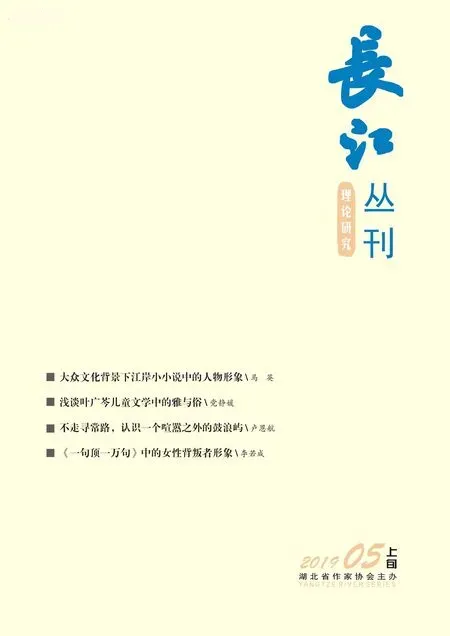在全球化時代詩寫
——黃斌詩歌讀札
■
在當下的寫作語境中,網絡平臺的拓寬尤其是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增加了詩歌發表的渠道,為詩歌從潛在創作轉向公共傳播提供了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創作群體的增長。創作主體的表達欲望加上一定的文字能力,再加之傳播渠道的多元化,用現代漢語寫詩似乎已不再那么困難,選擇以詩歌的形式來傳情達意的寫作群體漸漸擴大。然而這種詩歌創作的表面上的繁榮背后其實隱藏著危機。雖然一些優秀之作得以進入傳播和閱讀環節,但卻有不少詩作流于對公共經驗的跟風模仿和復制生產,缺乏明確的書寫立場和個人經驗的深刻體驗,缺乏高品位的藝術追求,最終變成缺乏個人詩歌立場的漢字符號和語段的拼湊。當詩歌創作的隨意性加大,“中國詩人”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曖昧的、可隨意粘貼的標簽。事實上,這種曖昧的界定矮化和消解了“中國詩人”的真正含義。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國詩人’”則成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作為一名“中國詩人”,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體現漢語詩歌的“中國特質”?黃斌作為一名詩人,劉潔岷稱他是“炎黃旗下漢字的歌詠與守望者”。這是在當代漢語語境下對黃斌的詩人情懷的理解,也是對黃斌的詩人特質、詩歌立場及詩學觀念的高度概括。黃斌傾心于漢詩的漢語性,在詩中保留了中國詩歌的古典氣韻和傳統,并將本土經驗、個人經驗和現代詩學經驗融化在詩歌當中,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在全球化時代的真正的中國詩人。
全球化時代,文化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在這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里,不少詩人的追求是“一路向西”,絕塵而去,也因此,在為建構個人詩學而跋涉的行旅上,他們在向一種詩學資源打開的同時遮蔽了另一種詩學資源,他們的寫作忽視了中國本土詩學資源的調動。同時,如若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的詩學經驗,便很容易陷入“食西難化”的尷尬境地。詩作看似深刻,實則淺陋,看似玄妙,實則晦澀蕪雜,詩歌創作以不落俗套的方式落入俗套。除了“一路向西”外,當詩歌缺乏真正深刻的生活體驗,缺乏真正堅實的詩學支撐,將世俗化流于庸俗甚至媚俗,將口語化膚淺理解為口水化,形成一種“梨花開遍天涯”的局面,詩歌創作便偏離了對詩這顆文學桂冠上的明珠的真正向往和追求。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中,黃斌卻依然保持著穩健的創作步伐,于“時尚化”的寫作之外堅守著傳統文化的立場,在對西方詩學資源敞開的同時有意識地規避對傳統詩學資源的遮蔽。黃斌在吸取現代詩學經驗的同時也不忽視對本土詩學資源的調動。他的詩歌中保有著一種古典氣質,身處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卻能與駁雜的文化形態保持著一種距離。
黃斌從小便受書法、繪畫、圍棋等中國傳統藝術的熏陶,這些傳統藝術陶冶了他的精神氣質,涵養了他的詩歌內蘊,成為其詩歌文化氣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他的詩作中,我們可以讀出這些文化養料對他的涵育。尤其是書法,受父親影響,黃斌七歲開始練習書法,一直堅持至今,在這個過程中醉心于漢字的魅力,專注于漢語詩歌的書寫,讓自己變成一個在漢字里存活的人。同時,漢字的美學也深深印刻在他的詩中,所見所想都以與書法相聯系的姿態在詩中呈現。當母親火化時,他看到的是“爐頂的煙子冒了出來/像永字八法那樣最先冒出一個點來”。《惜敬字紙》這首紀念母親之作是《黃斌詩選》的第一篇,于黃斌而言,母親是他心中漢字精神的象征。“永字八法”是書法中楷書的用筆法則,將母親火化時的煙灰與“永字八法”合二為一,是一種精神的升華。黃斌以這種動態的、形象化的方式來表達他此時心中的感受:“母親已經活到漢字里去了”。而他自己也將要在漢字里存活。長期醉心于書法的人能在書法藝術中體悟到人生的哲學,書法是他們感知世界、感知自我的一種方式。于是我們可讀到“有垂髫少年/悟得筆法/一撇一捺/勢如桃葉/厚重的墨點/危如墜崖/那是一種壓迫的美”。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在不懂書法的人眼中,那一個個漢字僅是入眼的視覺符號,也許他們能在形象上或多或少感知到一種模糊的美感。而在書法修習者眼中,那些漢字是鮮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一撇一捺勢如桃葉,雖狹長,卻挾帶著凌厲的氣勢,如年輕的生命中一往無前的勇氣。墨點厚重,雖圓潤,卻沉穩,且能給人以壓迫的美感,這是經歷歲月積淀后的人生姿態。那悟得筆法的少年。悟得的何嘗不是人生的活法呢?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散慮的山水》不僅有書法的美感和哲理,還極具畫面感,全詩勾勒了山清水秀處,隱逸的士人帶著小丫頭和小少年,煮茶品茗,研習書法這樣一幅畫面,頗有魏晉風度的隱逸和閑散之味。除了《散慮的山水》《黃梅四祖村下》《在唐寅墓前》《題八大<蓮房小鳥>》等畫面如水墨丹青的詩以外,黃斌還有一些色彩鮮明的詩,《車進秦嶺》便是一個典型:“蕭瑟無需提煉/呈現也包含假象/比如遠山比墨淡/誰料從灃峪進山/在盤山公路的右邊/陽光突然像聚光燈打在一山紅黃相間的秋葉上”。前三句仍是靜態的黑白水墨,豈料隨著人物的運動視角突轉,陽光如聚光燈般打在樹葉上,耀眼的紅、燦爛的黃、閃耀的金,都是極具視覺刺激性的顏色。從黑白到暖色調,從靜態到動態,六行詩中完成了這個鮮明的對比,畫面感強烈且具有沖擊力。這是黃斌參悟國畫的另一面:除了水墨丹青以外,同樣有濃墨重彩。
黃斌的詩作有不少表達了對傳統文化的哲思,蘊含著中國古典哲學的意蘊。早在1988年黃斌便已寫下富含哲理的《禪意》,錢文亮認為這首詩不同于王家新和陳應松的“文化詩”,它具體而微,化繁為簡,在一片普通樹葉的自然動靜中,表達了中國式“天人合一”的“禪”的生命姿態,以詩歌的形式詮釋了中國傳統的感應美學和自然而在的生命意識。樹葉是人感應自然最直接的事物之一,古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說法,黃斌有一首《絕句》便頗有此意味,因梧桐葉的凋落入秋有感而發:在自然時間之內,人的感知總是落后于自然的變化。將時間、自然等抽象概念具化到樹葉乃至樹葉下落時的回旋,以小見大。對于禪,黃斌似乎有種執著的追求,寺廟、曇花、僧人等在他的詩作中經常可見。《在薦福寺思禪》更是直接以“思禪”為題,短短六行詩中包含了許多復雜而深刻的體悟:與自然中存在千年的事物相比,人的肉身是多么渺小;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心臟也可以隱晦如點;靜是禪,心動卻更是禪;不相信肉身是靈魂的衣服這種說法,卻覺得這樣比喻二者之間的關系也不錯。如此豐富的思考要濃縮在六行詩中,可見其強大的語言駕馭能力、長久的生活經驗積累以及思想的穿透力。
在全球化浪潮滾滾而來,文化形態變得含混駁雜的當下,黃斌繼承著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于是陶淵明、李白、王維、賈島、姜夔、唐寅等人常在他的詩中“客串”。他通過對那些時代的回望和想象與當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我把冷的香氣作為名剌/去沔口結識姜白石/南宋太美我對他說/歷史基本上只會退步/我在21世紀的武漢/在他曾經生活過的上游/攝取了過多的重金屬/江水似乎變清了可惜/只是表象梅花還在開/開一次讓人尊重一次/我的這個時代有致人死命的電流和光明/急促如他聽過的青石上/馬蹄的雨聲/詞人的命運并不都一樣/金人的軍隊舉著月光的彎刀殺過去了/我這邊剛剛開完一場/資本在漢陽琴臺主持的新年音樂會(《冷的香氣》)
這首《冷的香氣》將姜夔擬想為對話對象,設置了南宋和當下兩個時空,在“我”對姜夔的傾訴中兩個時空交錯并行,以南宋的美反襯了當下的粗鄙與粗暴。相似的事物,在南宋是江水、青石上馬蹄的雨聲,在當下則是重金屬、致人死命的電流和光明。同為詞人命運的對比,雖然姜夔的命運歸結于戰爭,而“我”安逸地欣賞了音樂會,看似安逸美滿,實則透著一種失望和失落,這是一場“資本”主持的音樂會,僅“資本”二字便包含了太多情緒。
每個人在這個時代都會有自己存在的方式,或主動,或被動。黃斌屬于主動的清醒者,他就是這樣清醒地保持著詩中的古典氣息,置身于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卻又以不融入的姿態表現出疏離。
城市的文明形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亦然。在鄉土中國式的社會形態下,大多數人一生都在出生地或臨近的村鎮生活。而當鄉土形態的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時,開放和流動則不可避免。鄉土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態被打破,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生命軌跡漸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出走與歸來,離鄉與返鄉。這種流動和開放既造成了許多人無根的漂泊,同時也有些人把心留在了故土,他們“把家和姓氏裝進心里/就繼續滿世界地去生活”。于他們而言,故鄉是文化原點,是文化標本。于是本土經驗、家族姓氏、血緣宗親也成為黃斌詩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對本土經驗和地域經驗的關注也是黃斌詩歌展開的一種方式。黃斌曾寫過一首名為《我的詩學地理》的詩,詩中劃定了他詩歌的文化邊界——楚文化區,可見其對故土的熱愛和依戀。若在黃斌的詩學地理中標一個中心區域,那個區域必然是蒲圻縣新店鎮。《蒲圻農事詩》《蒲圻縣老城區》《蒲圻縣新店鎮》《1932年至1938年蒲圻縣新店鎮的日常生活》《蒲圻縣搬運站》《用詩守候一個已經在中國消失的縣名》……他寫故鄉的景物,寫故鄉人從前的生活方式,寫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生活。詩作中描繪的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那種原始、淳樸的氣質反襯了當下的單調和蒼涼。用黃斌的話來說,他想用文字構建自己的一個底盤,底色的、根性的東西。可以讓自己不發瘋,能夠很好地應對日常生活。于黃斌而言,“故鄉”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故鄉,更是文化上的故鄉,是精神上的原鄉。從這層意義上來說,蒲圻縣新店鎮則有著文化上的象征意義,黃斌對蒲圻縣新店鎮的描寫,可以說是地域經驗,對于同質化的書寫來說,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經驗。
對本土經驗的書寫與在詩中保持古典氣質一樣,都是黃斌與全球化時代的“當下”保持距離的方式。他認為鄉土可能是抵抗全球化最靠得住的武器,就像長矛對大炮,打不過,但是最順手。對于自己的姓氏,黃斌在詩中表現出一種自豪感:“很榮幸/從甲骨文到現在/這個漢字都綿延/我的姓氏家園/因此很大/很悠久”。家族姓氏與詩歌的淵源也增強了黃斌對自身詩人身份認同:“在通山的民居中/黃姓家的門楣上的四個字/是/詩祖傳家/或許我可以像杜甫那樣/說/詩是吾家事了”。
黃斌曾向故鄉的詩人饒慶年和葉文福學習寫詩。從饒慶年那里,黃斌繼承了對鄉土風物的描繪,從葉文福那里則承襲了對現實的映射,雖不像葉文福那樣姿態激烈,卻有一種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和把握。他用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審視當下的城市形態,并用詩歌呈現出來。
全球化在城市形態上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中國的城市化在1992年以后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而詩人對于這種“快”,大約是有些抗拒的。用黃斌的詩句來說就是“這個時代太直接了/直接得來不及修辭”“而時代只是京廣線上十五分鐘一趟的列車/不用一分鐘就轟隆隆離開了我的江南”。林立的高樓阻擋了陽光,快速的生活節奏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我們開始遠離自然,遠離他人。
《511路公汽》是一首長詩,全詩以幾個“依然坐在511路公汽的人/你們好嗎/有從1990年開始/至今/還在坐的嗎”發問,以一條公交行駛路線的不變來串聯起城市的變化、時間的變化、人的變化,烘托出世事的變遷,詩中反復提及“在511路公汽上找不到自己了”,表達了詩人對城市快速變化的陌生感、失落感和恐慌。若說《511路公汽》是對城市變化的失落與無措,那《城中村》則直指被商業化浪潮席卷的社會中人情的淡漠。詩的前半部分用了大篇幅來描寫詩人二十多年反復穿過的城中村的各種景象,后半部分才通過自己和城中村的人們的交往揭示出想要表達的失落和無奈:“這里有些人/我看著眼熟/但是叫不出名字/我們的關系/只是和人民幣之間的關系/吃/然后結賬/然后再次相見/也沒有什么話語/只是現在變化發生了/我和她們/連以前這點默契/也不復存在”。如果連金錢維持的關系都沒有了,那人與人之間所剩的維系確實令人難以想象。
內心有些抗拒不代表徹底拒絕當下的世界,黃斌在《廣水徐家河瞻眺》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或者說是處理方式:“現代化的五層樓房/高大/巍峨/既不能逼視/也不能一覽無余/我對嶄新的事物充滿敬畏”。簡而言之,這種現代文明不可屈服,也不可駕馭,那么就充滿敬畏——保持距離。
詩人夏宏曾說黃斌的詩在當代詩歌中很難被歸類。這與黃斌所持的詩學觀有關。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他仍抱著一種純粹和樸素的詩學觀,他堅持認為“詩歌不是政治”,它不需要靠不斷的青年造反運動去獲取話語權;“詩歌也不是產品”,它不需要納入到資本推動的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及不斷的升級換代的秩序之中。這大概是在全球化時代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黃斌從中國傳統文人那里承襲來的“清高”之氣,保持著對詩的虔誠。
詩是一種特殊的言說方式,這種言說方式自古以來就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奧斯卡·米沃什將詩歌定義為自人類開始以來的友伴:“那神圣的文字藝術,僅僅因為它從宇宙神圣深處涌出,在我們看來便比任何其他表達形式都要緊密地與那精神和物質的運動聯系在一起,它是那運動的催生者和指導者。當一個詩人虔敬地運用詩這種言說方式來言說他的生活之時,詩便真正地融入了詩人的血液里面。綜觀黃斌的詩作,從題目便可知這是一個用詩歌來言說生活的人:《初春過蓮溪禪寺》《詠神農架冷杉》《江夏民居記》《無量壽寺聞僧閑話》《長跪在杜甫墓前》《武漢關的鐘聲》《在大幕山看到蒼鷹》《菖蒲小賦》……都是一些極其平常的題目,沒有一眼便能震撼人心的沖擊力,也不是哲思或意象的高度凝練,但讀者卻能從中感知這是一個用詩來記錄,來言說生活的詩人。對黃斌來說,言之,即是詩。也就是說,詩是要說的,在形態上更多地表現為有說的沖動,因而書寫。生活中目擊的場景讓黃斌有說的沖動,因此他用詩來精密地表達生活的現場。黃斌的詩歌不刻意追求語言的整飭和精致,不耽溺于修辭,不鐘情于堆砌辭藻,也不在白話與書面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因而有一種流暢感。有的讀者可能覺得黃斌的詩不夠精致,李建春便認為黃斌的詩有點像草稿一樣,但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他的詩歌有種語言上的自我解放的意味。
詩歌的語言不以嚴密的邏輯、流暢的語言和完整的敘述為最高追求。在詩歌的語言中,斷裂、跳躍、空白、省略似乎隨處可見。但讀黃斌詩歌的時候,讀者也許會感覺似乎“不夠斷裂”。這并非詩人的語言駕馭能力不夠,而是詩人在詩歌中運用的“陳述性”言說機制。黃斌的日常之詩言說的是他的日常生活經驗,但非敘述。“陳述性”是“用陳述話語來代替抒情,用細節來替代意象”,在讀者看來那些“不夠斷裂”的句子實際上正是細節的刻畫,這種陳述性話語更能體現詩人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包容和轉化能力。
一個詩人,一個懷著純凈而樸素的詩學觀的中國詩人,在炎黃旗下歌詠和守望漢字。他將自身傳承的古典氣息、本土經驗和對現實的敏銳觀察與全球化的時代對接,卻又與這個時代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用漢語堅守著一個詩的國度。內心有堅持的人,就不會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變質,不會在紛雜的社會中迷失自我。如黃斌在《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做一個中國詩人》中所言:
由此說到中國詩人那不過是一群用漢字寫詩的人/這有如漢水雖死在長江但千百年來仍然是漢水/江漢湯湯不捐細流/大海茫茫不辨點滴/茍能點滴于江海/做一個中國詩人/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