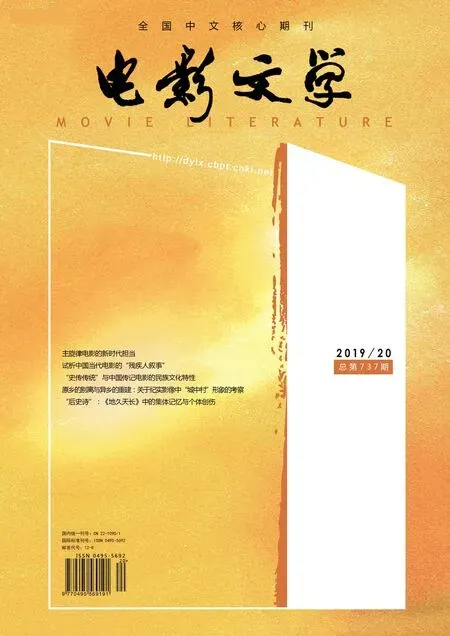媒介視閾下電影的現實主義
張慧娟 郝建國
(1.山西師范大學 學報編輯部,山西 臨汾 041004;2.山西師范大學 傳媒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4)
2018年暑期,由文牧野導演,寧浩、徐崢監制的現實題材電影《我不是藥神》吸引近億人次到影院觀看,票房超過30億元,被認為是本年度甚至是長久以來難得的現實主義電影佳作。有評論者說:“面對不斷升級的中國電影市場和產業化進程,近些年大部分現實主義國產影片始終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無法在商業電影的市場環境中獲得相應的價值認同。”“希望《我不是藥神》不是現實主義國產電影一次單槍匹馬的自我救贖,而是喚醒現實主義精神傳統真正回歸的契機”[1]。對于理論研究或電影評論而言,與其說是電影《我不是藥神》受關注,不如說現實主義電影才是關注的焦點。在影視理論中,現實主義是一種創作理念和創作手法。而影視評論或影視批評更多關注它的美學問題和創作問題,較少關注現實主義本身的社會意義及其規范性,導致了理論或批評滯后于電影實踐,或者被大眾影評或網絡影評邊緣化。因此,本文嘗試從媒介角度、媒介系統角度分析電影的現實主義,以此發掘其社會意義。
一、電影現實主義的媒介關聯
電影屬于大眾媒介是毋庸置疑的,且自誕生之日起就快速發展為社會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1895年,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對他們的“電影放映機”進行了商業展示; 1911年,美國就有11500家劇院用來放電影,每天有500萬人進入電影院;三年之后這個數字為每天700萬人,收入300多萬人民幣。[2]226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電影院被稱為“五分錢電影院”,說明在電影發展初期,其大眾媒介屬性已經非常明顯。經過百余年的發展,電影已經不僅是一種媒介,還是一個市場化產業,一個系統性的功能組織。它的技術屬性、市場競爭模式和自成一體的系統運行都和現實主義密切關聯。
(一)媒介技術性特征及其對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
電影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都高度依賴技術。從手搖的每秒16格的默片電影到每秒24格電動馬達驅動、攜載聲音膠片而呈現的有聲電影;從彩色電影到數字電影,再到現在的3D、4D電影都使得電影藝術的表現力越來越強,越來越豐富。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即信息”,即“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3]。在此,要特別注意技術和電影藝術的關聯。西方有學者認為,自有聲電影出現以后,“聲音標準化的電影使得電影不再那么有可塑性,對個性化的理解也沒有那么大的發揮空間。暗指和隱喻是默片的基石,但是對話使每時每刻都拘泥于字詞,將電影的主觀性變為客觀性”。[2]238從某種程度上講,技術是理解電影或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甚至是基點。
(二)大眾媒介市場化特性中的現實主義電影
電影誕生在西方世界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就與市場緊密結合。愛迪生不僅是一個電影技術發明家,還是一個商人甚至是壟斷資本家。美國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夠持續地影響世界電影,正是憑借其日益成熟的商業模式和推廣手段。“對于類型電影而言,制片廠通過觀眾對于電影的喜好程度來確定一種類型的生產規模、周期和營銷方式,作為成本回收和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保障”。[4]從理論上講,類型電影和現實主義電影相對,但它們的分野并非絕對,而是相互借鑒。市場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20世紀70年代,美國電影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那些帶動美國電影影像整體變革的標志性影片,很大一部分出自歐洲電影攝影師之手,其中觀念與技巧上的歐洲淵源清晰可見。特別是,歐洲電影攝影發展的兩條重要線索——對影像真實感的不懈追求以及關于影像表意和氣氛營造的深入探索”。[5]歐洲電影正是現實主義電影的發源地或主陣地。
(三)媒介系統性運作過程中的現實主義電影
20世紀中后期發展起來的社會系統論使我們對電影行業的理解具備了宏觀視角:一方面,電影和電影行業是由諸多部門分工或功能子系統組成的綜合社會系統;另一方面,它的系統性是由電影的制作者、傳播者、接受者等角色構成的循環系統。而從德國社會學家魯曼提供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系統理論視角出發,電影或電影行業的系統性特征則來自它和其他社會系統的差異性,即電影有其自身的溝通方式、運作方式,并按照自身的邏輯在運作過程中進行自我指涉和異己指涉,將非電影的排除出去,留下電影的,從而劃定自己的邊界。“系統的各自獨立性主要來自各系統內在生命的自律性,而這種系統自身的自律性,又是各系統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條件”。[6]這涉及兩個問題:電影的本體是什么?其本體又如何體現?電影自然是由視聽語言或話語體現的,但電影的本體卻有很多說法。無論哪種說法,都有敘事與影像的結合、藝術審美性、價值性等核心要素,而且它們的結合衍生出了兩種藝術分類,即現實主義電影和類型電影。這說明現實主義電影具有電影的本質屬性,也有自身的藝術屬性、藝術規定性和邊界。
二、電影現實主義的媒介建構及其規則
作為一種文藝或文化現象的現實主義,在創作原則上強調創作主體必須追蹤社會現實,把握時代狀況,反映社會矛盾,體現其批判性;在創作方法上倡導“真實論”與“典型論”,即“要求創作主體不僅要盡量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反映生活,而且要盡量擺脫對現實生活的自然主義實錄,創造出既符合生活的原貌又高于生活的藝術真實”。[7]11“典型”則是典型環境、典型人物。電影的現實主義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去創作電影。盡管冠以“現實”,但其實已經和“現實”有很大不同。創作在此轉向另一個層面或范疇,即建構的或建構主義的。
(一)關于“實在”
“實在”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指真實存在的事物,即人們身邊的或環境中可觀可感的人或事物。它可以由我們的親身體驗所觀察或成為我們觀察或實踐中的一部分。二是媒介實在,或說媒介本身,即人們借以獲取外界信息的中介組織的存在,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等即屬此類。三是媒介建構的實在。這里可能有誤解,既然是建構,那么就不能稱作實在。但在魯曼看來,由于距離或技術的原因,人對環境的了解和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被阻斷,人們對于實在的自主觀察沒法實現,只能借助于媒體。“大眾媒體建構實在,這是無可避免的。每一個觀察都是一種建構。”[8]且很多情況下,人們就是或只能以這種建構的實在采取行動。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社會的人必須通過媒體去觀察社會,但再先進的科技也沒法保障媒體做到客觀真實,因而我們始終面對一個被建構的社會,辨識本身也帶有建構性。
(二)建構實在
媒介建構實在的方式是通過信息選擇機制完成的。對于現實主義電影,它要經歷三個階段:
1.選擇性素材搜集
現實主義電影自然要關注社會現實或社會現實問題。以《我不是藥神》為例,編劇韓家女是在看了2015年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中《救命的“假”藥》后進行創作的,這種選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一是真實事件。2015年媒體以“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為題大量報道影片主人公原型陸勇的新聞。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的報道與其他社交平臺的傳播相互印證,確保了事件的真實性。編劇本人也和陸勇本人有交談了解。二是影響廣泛。整個事件從陸勇患病到難以承受高額藥價,從接觸印度仿制藥到為眾多病人代購,從涉嫌銷售假藥到擾亂金融秩序被捕,又免于被起訴釋放等,涉及情理法等多重因素,媒體一直在進行關注討論。三是由此引發的看病貴、看病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醫療制度等社會問題備受關注。
2.選擇性創作建構電影
從媒介角度看,只要信息流向媒介,通過媒介的方式傳播,就一定是一種建構,并沒有所謂的“實錄”“寫實”或“客觀”“真實”的說法,新聞節目也是如此。電影并不是對原有素材的簡單組裝拼接,而是選擇性加工,使其符合電影的特點。從《我不是藥神》的角色塑造就可以看出,如原型陸勇,在電影中變成了健康人程勇。不僅健康,而且與家庭殷實的陸勇相比,程勇的個人處境要復雜得多。另外韓家女了解到,陸勇被關押在看守所期間斷藥后是看守所里的幾個警察想辦法從印度幫他買了仿制藥,才使陸勇病情沒有惡化,于是塑造了“曹警官”這個角色;劇中“黃毛”的角色,源于程勇的父親,程父因程勇生病不得不繼續工作而遭遇車禍去世。另一位編劇鐘偉,也是從自己身邊的老師、合租房遇到的牧師、患病的小女孩等現實人物身上選擇了一些符合電影創作特點的東西塑造了呂受益、劉神父、思慧這樣的角色。除角色塑造以外,整個事件的過程也進行了改造,與現實中陸勇被捕又被釋放不同,電影中的程勇最終是進了監獄。
從角色塑造到事件的重新演繹,電影依據自己的規則進行了故事的藝術化建構,形成了另一個“實在”或“現實”。觀眾其實并沒有判斷它是否與真的事件一致,但都認為這樣的“實在”是存在的。
3.選擇性地傳播與理解
電影是通過受眾群體的接收、理解作為電影完成或更深遠的傳播支點。為了傳播和理解的需要,傳播方和受眾方在信息流的兩端都有選擇性的行為,《我不是藥神》三易其名,就是為了適合大眾理解。第一個名字《印度藥神》想反映藥是從印度來的,但容易引起誤解,認為是印度故事。第二個名字《中國藥神》回到了中國語境,但太過平淡,無法反映電影情節的波瀾起伏。最后是《我不是藥神》這個名字,導演文牧野說,從《中國藥神》到《我不是藥神》,從肯定句到否定句,這本身包含著矛盾、辯證的東西,與電影更為契合。電影名稱的修改一是為了更契合內容,二是為了利于傳播和受眾接受。《我不是藥神》能夠引起共鳴,這個否定句有一定的作用。
媒介建構是雙向的。沒有受眾的理解,電影不可能實現其傳播效果。而這種理解是選擇性的,受眾只會保留自己能接受的,排斥那些不能接受的。《我不是藥神》原型陸勇曾公開表示擔心電影改編會給自己造成負面影響,因為他從來沒有為代購而賺錢。但當電影在清華大學路演時,徐崢問現場觀眾會不會因為他在電影中演了這樣的人物而覺得陸勇不是一個英雄。觀眾的回答是否定的。對于現實題材,觀眾關注的是這個電影反映的問題是否真實,而一些藝術加工的東西都會選擇性地過濾掉。
(三)建構的規則
媒介建構過程的選擇性有其特定的規則,規則是什么呢?它在媒介或電影建構過程中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
1.規則的社會含義
在魯曼的社會系統論里,規則是為了應對復雜社會而形成的簡單化措施。簡單化的原理則是社會分化,即通過分化出的功能性社會系統或組織去應對不斷復雜的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媒介的出現,是為了使現代社會復雜的信息環境秩序化。19世紀以后,大眾媒介先后分化出印刷媒體、電子媒體、網絡媒體等多種媒體系統,電子媒體又分化出廣播、電視、電影等媒體系統,其中的電影系統又分化出現實主義電影和類型電影兩種社會系統。它們都是以特定的功能實現信息社會的秩序化。秩序一方面靠社會分化出的功能性組織實現,另一方面靠系統之間的互動實現。由此觀察電影媒介系統,會發現它與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有很多關聯,而且現實主義電影與政治系統互動更多,類型電影則和經濟系統更為緊密。因為現實主義電影回應的是公共秩序的問題,類型電影則偏向娛樂,回應的是經濟系統大眾消費的需求。
2.規則所指
根據規則的社會含義和形成過程,可以明確媒介或電影在建構實在的過程中至少受到三種社會系統及其規則的影響:一是政治規則。它依靠權力進行系統運行,通過權力和其他社會系統產生互動。政治權力具有公共性和強制性功能,電影在與政治的互動過程中基本上是被主導的一方,必須遵循政治所規定的意識形態、法律制度和指向秩序的其他政治規則。二是經濟規則或市場規則。它依靠貨幣及買賣關系、利潤進行系統運行。貨幣本沒有強制性,但它的資源分配功能及其利益的誘導性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從而對媒介或電影產生重大影響。三是自身的媒介規則,即電影自身的功能規定性。其首要功能是通過觀察社會及其運作消減信息社會的復雜性。但電影必須遵循一定的藝術審美規則,即使是現實主義電影,其寫實性也并不應該和審美原則相沖突。
3.規則的認識與遵循
正如上文所說,規則與秩序依靠分化社會系統的功能性互動產生。但只有平衡的互動會產生合理的結果,對于處于電影媒介系統中的、具有意識能動性的個體,如果其作品要成為符合各方需求的作品,就一定要掌握這種平衡術,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毫無疑問,《我不是藥神》就是這樣的作品。如果其采取純正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與方法,那么很可能會因寫實的批判性而與政治產生某種糾葛。而如果采取類型化的創作方法,就可能會走向過分娛樂化而喪失其本來的社會意義。所以,它采取了一條中間路線,以達到平衡。正如饒曙光所說:“創作者借鑒了諸多‘現實主義’策略,但所謂的寫實的現實化影像和表演仍是以服務戲劇敘事為基礎的,類型法誘導影片擺脫了寫實范圍。”[9]鄭煬借曹警官與程勇之間從疏離到諒解的過程認為作品“恰強調了作為引導力量的中國政府在回應民間訴求、消弭民意裂隙的有效存在,并以此為前提在作品中進行批判與建設”[10]。曹晚紅教授則直截了當談到“平衡是一種技術,更是藝術,深諳平衡之道的導演,才能走得長遠”[11]。
三、電影現實主義的邊界
從理論上講,任何功能性的社會系統都有它的邊界。現代社會顯著的特點就是各系統之間功能區分明確、邊界明晰,而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混在一起,容易產生沖突。電影的邊界是通過它與其他系統的互動產生的規則來實現的。如現實主義的電影,必須考慮它和政治之間的互動,同時要兼顧其和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電影系統從它誕生以來就分化出一個專門用來界定電影邊界的組織或系統,即電影評論或電影批評群體。如果說電影是用來觀察社會的,影評則是用來觀察電影如何觀察社會的。參與影評的個體或群體來自學院派的專業群體、官方群體、電影業界群體,目前還加入了以網絡為陣地的大眾群體。他們的角色介于各個社會組織或系統之間,其影評是基于各自視角的判斷,共同形成了一種邊界化的存在,其批評性話語就是邊界最直接的體現。
但是,多種評論主體的存在,可能會使其評論產生分歧,電影邊界也就很難區分。那么,普通觀眾能不能看到這個邊界?或區分這個邊界呢?一般來說,普通受眾較難分辨。這也就是為什么觀眾有時會對一些類型的電影產生疑惑,為什么好的電影不叫座、叫座的電影不好看。馮小剛導演曾炮轟娛樂節目改編的大電影就不是電影。這說明,規則或邊界有時候是很難分辨的。
其實不然,權威的評論一定會對電影邊界的確定產生影響,中國20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的電影評論對電影的影響可見一斑。當前,權威的評論基本是學界和官方的聯合體。學界掌握了電影概念或電影理論的定義權力,官方掌握了電影生存和發展的制度性權力。他們的評論組合最終會對電影創作產生重要影響。在《我不是藥神》的諸多評論中,專業評論和官方評論幾乎都明確地分辨出電影的現實主義性和商業性,都贊揚了電影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節制性或克制性的處理方式以及對商業策略的精準把握。正如一位學者在論述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的時候總結道,“堅持現實主義電影美學,也就是堅持了電影的意識形態性,以及其在上層建筑中的重要地位”。[7]14現實主義電影的邊界大致在這個范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