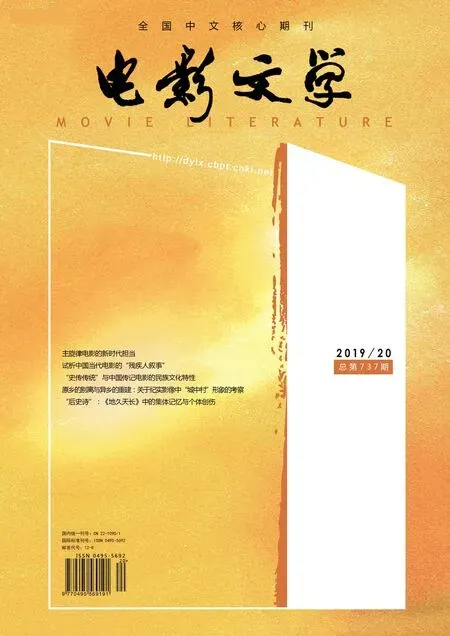從《最美的青春》論中國故事的創(chuàng)作策略
資小玉
(河北民族師范學(xué)院,河北 承德 067000)
在新時代語境下,講好中國故事是影視創(chuàng)作者的責(zé)任、使命和擔(dān)當(dāng)。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其中又包含了兩個核心問題:講什么樣的中國故事以及怎么講好的問題。近來一部主旋律熱播劇《最美的青春》以其獨特的浪漫主義情懷和現(xiàn)實主義精神,“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1],從主題立意、人物塑造等方面很好地回答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最核心的兩個問題,堪稱新時代現(xiàn)實主義題材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典范和精良之作。
一、講中國好故事,立具有時代精神的主題
新時代影視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胡智鋒教授曾談到,前提是要選好中國故事,選中國好故事。“好的中國故事應(yīng)該體現(xiàn)中華民族獨特的氣質(zhì)和個性,是在當(dāng)代依然充滿活力的,跟世界先進(jìn)文明相匹配的優(yōu)秀故事。”[2]可見,影視要講好中國故事的首先要義在于選材和立意,即關(guān)乎題材與主題的問題。
(一)象征與詩意的奮斗主題
關(guān)于主題,編劇理論家喬治·貝克曾這樣說:“只要這個(主題)中心弄清楚了,作者就好比得到了那道‘開門咒’,劇本寫什么故事都不成問題了。它又好像是一塊磁石,能把思想、人物、動作、對話都吸到它的周圍,因而也就構(gòu)成了情節(jié)。”[3]
電視劇《最美的青春》,脫胎于河北承德作家楊勇根據(jù)塞罕壩先進(jìn)集體事跡改編的小說《功勛樹》,該劇從影視藝術(shù)的視角對原小說進(jìn)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讓一個年代歷史題材故事具足了新時代精神,這首先源于其創(chuàng)作團(tuán)隊對故事主題的準(zhǔn)確定位和把握。該劇保留了原小說中那棵“功勛樹”,據(jù)老一輩回憶,在五六十年前已是一片荒漠的塞罕壩上,確實就有這樣一棵落葉松迎風(fēng)屹立。郭靖宇導(dǎo)演在接受采訪時曾坦言:“這棵神樹給了我們靈感,成為全劇靈魂。藝術(shù)家不會漠視身邊的美好與崇高,于是我決定通過第一批塞罕壩造林人青年時期墾荒的故事,來呈現(xiàn)這一代人的崇高精神。”[4]可見,電視劇《最美的青春》在創(chuàng)作構(gòu)思時,就找準(zhǔn)了題材的切入點和立意所在,意圖通過情境設(shè)置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來呈現(xiàn)思想主題和時代精神,這也是影視能夠講好故事的要義之一。
“對文藝來講,思想和價值觀念是靈魂,一切表現(xiàn)形式都是表達(dá)一定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載體。”[1]《最美的青春》以“樹”為載體,在劇中被賦予了極強的象征意義。這棵樹見證了歲月的滄桑和奮斗的奇跡——塞罕壩由綠林惡化成荒漠,又從荒漠變綠海;它被塞罕壩祖輩奉為“鎮(zhèn)風(fēng)神樹”——是村民內(nèi)心對抗黃風(fēng)沙暴的希望和力量的意象化身;它也是一座無形的英雄紀(jì)念碑——曾在抗日中犧牲的游擊隊長馮程的父親就被戰(zhàn)友偷偷埋在這棵樹下。它不再是一棵普通的樹,它承載著淳樸的希望、崇高的信仰,傳承著英雄的氣節(jié),突顯了中國精神,它頑強的生命力也是激勵馮程堅信能夠在壩上種活樹苗的信念之光。從荒漠中孤獨的一棵樹到最后的松濤綠海,塞罕壩實現(xiàn)了自然生態(tài)的完美逆襲,這綠水青山的背后是一群人艱苦奮斗的結(jié)果,是無私奉獻(xiàn)的青春。劇中這棵樹后來被女主人公覃雪梅的父親國家林業(yè)部的領(lǐng)導(dǎo)覃部長命名為“功勛樹”,它蘊含著對在這片土地上播撒過青春甚至熱血生命的英雄們最高的敬意。圍繞著“樹”的意象,該劇的核心主題自然詩意地呈現(xiàn)于眾——奮斗奉獻(xiàn)的青春就是最美的青春。這樣一個核心主題是非常富有主旋律和正能量的,同時又極具時代精神,契合了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與習(xí)總書記呼吁的“奮斗的人生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不謀而合。
除了有形的“樹”的外在象征意象,還有“詩”的內(nèi)在精神意象。劇中男主人公馮程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用“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詩意地表達(dá)了真情實感。同一句詩,在不同情境下,它的意味又有著細(xì)微的變化,從全劇來看,隨著馮程人物的變化和發(fā)展,這句詩豐富地表達(dá)了他對塞罕壩這片故土的深情,對奮斗事業(yè)的篤定和決心,以及對民族事業(yè)和國家責(zé)任的擔(dān)當(dāng)。尤其是馮程在經(jīng)歷了與大學(xué)生們從對抗到共同奮斗之后,這句詩也從一開始作為馮程個人的情感表達(dá),變成了由他領(lǐng)誦其他大學(xué)生集體接連吟誦而出的場面。這句內(nèi)化為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詩,彰顯了在塞罕壩奮斗奉獻(xiàn)的過程中,這種責(zé)任和擔(dān)當(dāng)已然從個人情懷上升到集體共通情感的詩意主題表達(dá),塞罕壩從荒漠重回松濤綠海,不僅是個人的奮斗和努力,更是一群人一個大集體的奉獻(xiàn)與付出。艾青的這句詩在全劇貫穿式地反復(fù)表達(dá),讓這樣一部取材于五六十年前歷史的現(xiàn)實主義題材劇作又富有了浪漫主義情懷。同時,這種表達(dá)與人物內(nèi)在的心理情感和精神指向是一致的,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是人物內(nèi)在動機(jī)最豐富感性、最本質(zhì)淳樸的情感力量。
(二)愛與責(zé)任的生態(tài)主題
1886年,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寫道,“美索不達(dá)米亞、希臘、小亞細(xì)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塞罕壩本為“美麗的高嶺”現(xiàn)實卻變成了黃沙漫天的荒漠,這種特殊情境環(huán)境表征在劇中通過鏡頭直觀畫面、戲劇性事件以及人物之口反復(fù)闡述和表達(dá),夸張、揶揄、諷刺的黑色喜劇意味昭然若揭,人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保的主題油然而生令人反思。
《最美的青春》開篇前兩集用了兩個戲劇化的事件——馮程老舅接親途中突遇沙塵暴嚇跑新娘和馮程帶女友唐琦去看神樹遭遇風(fēng)沙,夸張式地渲染了塞罕壩環(huán)境的惡劣。沙塵暴像突襲的怪物,令當(dāng)?shù)鼐用衤勶L(fēng)喪膽,趴下屈從是唯一的躲避方式。仔細(xì)剖析,前一個是壩上老光棍翹盼已久的娶親結(jié)婚,后一個是一對將塞罕壩意象化為世外桃源本想在此落戶成家的外來青年情侶,惡劣的環(huán)境讓結(jié)婚變悔婚,戀愛變分手。你會發(fā)現(xiàn)這兩個事件都直指一個驚人且殘酷的現(xiàn)實隱喻:它將人類最重要的情感愛情和婚姻,與塞罕壩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并置一處,生存還是愛情?該如何抉擇?
于是,成天刮著黃風(fēng)卷著沙土的荒漠不僅僅是塞罕壩當(dāng)時的自然景觀,它被構(gòu)建成了一個人類生存的考驗場試驗田,是屈從它還是改化它,這勢必是一場艱苦的斗爭。而這種難堪的生態(tài)景觀并不是大自然的天然造化,馮程給女友唐琦展示的那幅畫卷則為觀眾展現(xiàn)了幾百年前的塞罕壩:“浩瀚的森林,遍地的野花,風(fēng)吹草低現(xiàn)牛羊”,這是真正的“美麗的高嶺”,“是皇帝木蘭秋狝的地方,你坐在家門口,就會有梅花鹿向你跑過來,鳥兒會為你歌唱”。從前清以來的過度惡性砍伐樹木造成了自然生態(tài)的破壞,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場人為的災(zāi)難,人類必須為自行的惡果付出代價。
習(xí)近平總書記曾在講話中指出:“要把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護(hù)眼睛一樣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yuǎn)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最美的青春》正是以這樣一種被破壞的惡劣生態(tài)環(huán)境為劇作背景,展現(xiàn)了人在修復(fù)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奮斗精神,也進(jìn)一步彰顯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主題。而新時代影視要講好這一類型題材的中國故事,同樣需要在故事的講述中融入關(guān)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愛與責(zé)任。
二、講好中國故事,在戲劇化情境中塑造鮮活人物
從編劇學(xué)的角度,影視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第二層核心要義“怎么講”,一般來說,還是在探討講故事的藝術(shù)方法和創(chuàng)作技巧等問題,而塑造好人物形象又是“怎么講”好中國故事的重中之重。習(xí)近平總書記曾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diào),要“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nèi)心的沖突和掙扎”[5],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塑造典型、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提出了明確要求。
如何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戲劇化的情境建構(gòu)尤為重要。譚霈生先生曾在論著中強調(diào):“情境是為人物而設(shè),考察情境的價值,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是它能否使人物的生命活動獲得完整的顯現(xiàn)。”[6]電視劇《最美的青春》從以馮程為代表的年青一代,到以于正來為代表的老革命一代,每個人物都非常鮮活,在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的情節(jié)中,在極具壓力性的事件中,在人物關(guān)系的矛盾沖突下所做出的選擇和行動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個性化人物和豐富生動的人物群像。
(一)正面人物的“反面形象”塑造
《最美的青春》第一集,馮程在老舅新婚媳婦娘家門口拉“哀樂”逼得新娘摔下禮金遠(yuǎn)走他鄉(xiāng);去了林業(yè)局白天不務(wù)正業(yè)在宿舍拉琴晚上整宿看書影響同志們休息;林業(yè)局領(lǐng)導(dǎo)本以為來了個林業(yè)專家安排他負(fù)責(zé)壩上種樹攻堅小組,他以專業(yè)不對口斷然拒絕;他拿食堂的好糧食喂狗引發(fā)眾憤之下又打傷了德高望重的伙食師傅老劉頭;北京學(xué)校保衛(wèi)科的人來追緝唐琦,馮程隱瞞組織真相與之周旋并把女朋友唐琦窩藏在了壩上老舅家……戲劇性事件一出接一出,在矛盾沖突的關(guān)系建構(gòu)中,在極富張力的戲劇情境中,不僅抓住了觀眾還設(shè)置了懸念:這樣一個妄自尊大、執(zhí)拗不羈的馮程,竟然是這部主旋律的男一號?!這個讓人有些討厭的“搗蛋鬼”形象何以支撐作為主要正面人物的塑造呢?
然而,恰恰正是這樣的“反差式”塑造吸引了觀眾,而關(guān)乎這個人物形象的一切塑造都是基于對他的性格定位,就像尹鴻教授所解讀的那樣,“每個人都有個人史,英模片不夠鮮活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個人史,而在《最美的青春》中,各個人物性格定位準(zhǔn)確,使得他們的行為不完全按照創(chuàng)作者的概念去行動,而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定位去行動,在這一點上顯示出了很好的創(chuàng)作功力”[7]。
馮程起初的這些“反面形象”表征,也恰恰扣準(zhǔn)了主題關(guān)鍵詞“青春”二字,馮程在他的青春年華同樣具有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shù)年輕人的通病:自信又有點自傲,堅定又過于執(zhí)拗,激情又容易沖動。這樣的“青春”癥狀超越了時代的隔閡,讓新時代的觀眾在戲劇化的情境中感同身受,拉近了觀眾的心理距離,增加了親近感。他有別于一般主旋律影視劇中高大全的主人公形象,呈現(xiàn)了一個帶刺的、有缺陷的、鮮活接地氣的人物。然而,反差式人物塑造更重要在于,以鮮明的反差與對比方式來突出人物最主要和本質(zhì)的特征,如果說青春的不羈只是青春年華的共性,那如何引向“最美青春”的主題指征,則必須深掘于典型人物不同于一般的個性和特殊性。《最美的青春》在劇的第二集臨近結(jié)束時,塞罕壩條件的艱苦讓女友唐琦不辭而別,馮程從拒絕上壩種樹,突然主動請求上壩并且立下誓言,種不活樹堅決不下壩。這是年輕人失戀后的一種情感疏解?還是為了逃避懲罰的一種聰明手段?這樣一個加工木材專業(yè)、在林業(yè)專業(yè)眼中只會砍樹不會種樹的馮程能在條件艱苦的荒漠壩上種活樹嗎?新的懸念又產(chǎn)生了。
(二)荒誕式的戲劇化情境
黑格爾認(rèn)為:“藝術(shù)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從來就是尋找引人入勝的情境,就是尋找可以顯現(xiàn)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蘊的那種情境。”[8]
《最美的青春》中,主人公馮程只身一人上壩種樹一待就是三年,在這三年中,他孤身一人,常年面對的只有塞罕壩上不請自來的黃沙和貧瘠無邊的荒漠,正如同處在一個被大海包圍的孤島一般,只有一條叫星期六的狗做伴。劇中用了大量馮程勞作和自學(xué)書本的空鏡頭來表現(xiàn)一人一狗一樹和一荒漠的荒誕式戲劇情境,具有一種獨特的中華寫意美學(xué)氣質(zhì),靜謐、孤寂、蒼茫,一下把時光拉得很長,這與前兩集快速喧鬧一出接一出的戲劇性場面情境風(fēng)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劇作節(jié)奏有張有弛,由快入緩,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人物內(nèi)心的成長也在不同的情境中得以發(fā)展和呈現(xiàn)。壩上孤寂的生活甚至讓他忘記了具體的時間,他對著狗自嘲像魯濱孫,又突發(fā)奇想根據(jù)魯濱孫當(dāng)時身邊的一個叫星期五的伙伴來給狗命名為星期六。
三年的壩上時光讓他從一個年輕氣盛意氣風(fēng)發(fā)的帥小伙子變成了一個胡子拉碴、蓬頭垢面的“野人”。然而,相對于外貌最直接的改變,馮程最大的變化來自內(nèi)心的歷練和自省。上壩獨自種樹三年,從信誓旦旦一定能種活樹,到承認(rèn)自己失敗了絕望了甚至想輕生,再到重拾囑托繼續(xù)奮斗,堅持和堅守。這期間展現(xiàn)了馮程的改變、馮程的成長和馮程的另一面。這樣的塑造也是在一波三折的戲劇情境中完成的。北京學(xué)校保衛(wèi)科的人來讓馮程確認(rèn)女友唐琦的遺物,得知愛人死訊的馮程一下暈倒在地。這個“倒下”預(yù)示著一種悲觀情緒的累積已然沖破了可承受的界限。青春氣盛的馮程一直跟別人較勁跟自己較勁,對愛情的認(rèn)真、對工作的努力到來頭他發(fā)現(xiàn)只是一場夢幻泡影,借著酒勁,他扛著鐵鍬來到塞罕壩那棵唯一的樹下自掘墳?zāi)梗麑﹂L眠于此的父親訴說內(nèi)心的絕望:“我種的樹一棵都沒活,愛我的母親走了,我愛的唐琦也走了,我……我太累了,從今往后,這棵樹就是咱爺倆的墓碑了。”
不料,一個戲劇性的突轉(zhuǎn)又出現(xiàn)了——村民鄭三兒帶著三人來鋸樹想蓋房做大梁娶媳婦,馮程為了保護(hù)樹拼死斗爭最后保住了樹。非常有意味的是,他本來萬念俱灰想自殺結(jié)果卻因為救樹而自救了,事后他感嘆道:“雖然我沒種活樹,但我卻保住了這棵樹,哦,不對,是這棵神樹救了我的命。”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背靠大樹抬頭仰望時,樹枝上稀疏的綠芽給了他信念之光:“這棵樹至少有兩百多年了,到現(xiàn)在還在生長,應(yīng)該說它就是活標(biāo)本。它向我們證明,塞罕壩一定有種活樹的條件。”樹給了他新生的希望,也堅定了一定要種活樹的決心和信念,他救了樹,因為他救樹的真心實則又救了自己的命,這種微妙的互救關(guān)系,顯現(xiàn)了編劇在人物塑造方面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力道和高明,馮程的新生和突轉(zhuǎn),外來力量僅僅是一種輔助因素,真正的力量來自他善良真誠的本心和人性的成長,來自對塞罕壩這片故土的熱愛和責(zé)任。馮程性格的轉(zhuǎn)變和青春的歷練也正是在符合事理邏輯和情感邏輯的情境中,順理成章、一脈相承地自然發(fā)生發(fā)展,至此,馮程的生命也獲得了一次新生。
(三)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
馮程從一個孤獨的奮斗者如何完成個人的蛻變和成長,新的戲劇情境的鋪展則是將他置于時代的大集體中、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中去建構(gòu)完成的。
軍人出身的趙天山領(lǐng)導(dǎo)的四人先遣隊首先打破了馮程壩上一人一狗的生活,緊接著大學(xué)生上壩拔苗事件讓馮程就像點燃的爆竹一樣激烈,新的事件發(fā)生,新的人物關(guān)系建立,新的戲劇情境得以建構(gòu)。馮程與趙天山從對立、了解到成為朋友知己,以及馮程對以覃雪梅為代表的大學(xué)生,從對抗懷疑到信任包容再到互相幫協(xié)共同奮斗,圍繞壩上育苗種樹、攻堅克難一個個專業(yè)性事件,水乳交融著人物的關(guān)系沖突和情感糾葛,劇作將人物塑造與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在典型的情境和情節(jié)的發(fā)展中展現(xiàn)了典型人物。從三年獨自壩上種樹到之后大學(xué)生上壩建立育苗實驗室再到之后的馬蹄坑集體大作戰(zhàn)這幾個大的情境事件來看,作為個人的馮程是在集體中才有了真正的成長歷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集體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關(guān)系,反而起到了否定之否定的促進(jìn)力量,馮程在集體事業(yè)的奮斗過程中才真正完成了心靈的成長與生命的蛻變。
除了馮程這個主要人物充滿了“人物弧光”之外,對英模群像的生動塑造也是電視劇《最美的青春》的可取之處。比如林業(yè)局負(fù)責(zé)伙食的老劉頭師傅,他是與馮程父親及于正來局長并肩作戰(zhàn)過的老革命,起初老劉頭因為馮程偷偷拿食堂好糧食喂狗憤怒之下要殺狗示眾反被馮程失手打傷,在得知馮的身世之后又不計前嫌要與馮程論爺們。劇中大雪封山壩上斷糧那場戲,老劉頭為了提前一點給壩上被困已久的大學(xué)生們送上糧食,不料上壩途中馬車出了事故他被拋下雪窩子里凍成了一座錚錚鐵骨的冰雕人。在采訪劇中飾演曲和的演員于洪州時,他對當(dāng)時老劉頭那場戲的拍攝情形十分感慨,“當(dāng)時于局長和我(曲和)帶著大伙兒上壩上找人,在那樣的情景下,大伙兒包括我當(dāng)時流下的眼淚都是非常真實的”。“《最美的青春》其實展現(xiàn)的是為塞罕壩奉獻(xiàn)過的一批人物的群像。哪怕戲份少或者是群演,每一個人物都非常鮮活。而我認(rèn)為,他們的偉大正在于,他們在那個時代并不認(rèn)為自己這么做有多么偉大,他們認(rèn)為這是黨交給他們的任務(wù),是他們的使命和責(zé)任。而恰恰這種自認(rèn)為平凡的事業(yè)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是無比偉大的”[9]。
三、結(jié) 語
電視劇《最美的青春》謳歌了艱苦奮斗無私奉獻(xiàn)的青春,刻畫了以馮程為代表的一群最美人物,這樣的影視中國好故事值得贊美和弘揚。另外,《最美的青春》整個創(chuàng)作演職團(tuán)隊秉承著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盡可能地還原真實場景去拍攝,不畏嚴(yán)寒困苦、盡職敬業(yè)的“塞罕壩”精神,同樣值得我們影視人贊頌和學(xué)習(xí)。影視要講好中國故事,創(chuàng)作者和從業(yè)者的觀念態(tài)度亦是關(guān)鍵,不忘習(xí)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寄語,“雖然創(chuàng)作不能沒有藝術(shù)素養(yǎng)和技巧,但最終決定作品分量的是創(chuàng)作者的態(tài)度。具體來說,就是創(chuàng)作者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去把握創(chuàng)作對象、提煉創(chuàng)作主題,同時又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把作品展現(xiàn)給社會、呈現(xiàn)給人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