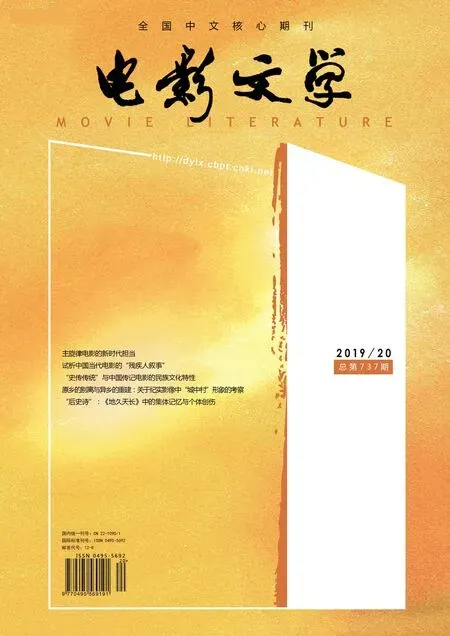“后史詩”:《地久天長》中的集體記憶與個體創傷
陳家洋 宋雪薇
(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提到“第六代導演”時,人們一般會賦予其較為鮮明的代際特征,諸如對底層人物的關注、紀實性的影像風格,等等。無疑,這些代際特征來自人們對第六代導演諸多作品的概括,彰顯出第六代導演作為一個代際群體的整體性創作面貌。
然而,在中國電影發展與衍變、堅守與游移、突破與激蕩的進程中,第六代導演也在不斷演變和分化,所以,用整體性的代際視角看待多樣、復雜的創作群體,以靜態的代際審美特征來概括發展與衍變中的電影創作,有可能產生偏頗。事實上,當人們認為“第六代”往往聚焦個體命運、放棄宏大敘事時,一些導演已經將目光轉向了社會轉型與時代變遷。在《二十四城記》中,一直關注底層人物命運的賈樟柯仿照“口述歷史”的方式,再現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工廠的消失;《江湖兒女》則在開闊的時空背景下呈現出“江湖兒女”的命運起伏。這一次,同樣對邊緣群體與底層人物充滿熱情的王小帥,也以一個充滿“時間”意味的片名“地久天長”,耐心地展現了時代變遷中的個體命運。
在中國電影快速的商業化浪潮中,人們對第六代導演的關注度正在減弱,而“第六代”作為一個評論范疇,也給人明日黃花之感。然而,兀自前行的第六代導演,似乎正在悄然間轉向闊大的世界和深邃的歷史,依稀體現出對“史詩性”的潛在訴求。而帶著“第六代”獨特印記的“史詩性”,卻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后史詩”的審美特征。
一、集體記憶:《地久天長》的“史詩性”追求
作為一個重要的美學概念,“史詩”一直受到美學家、文藝家的關注。黑格爾認為:“史詩就是一個民族的‘傳奇故事’,‘書’或者‘圣經’。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這樣絕對原始的書,來表現全民族的原始精神。”[1]108在黑格爾看來,“表現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就是“史詩”的基本內涵。《荷馬史詩》即是如此。在此語境下,“史詩”成為特定時期的特定“文體”。“特定時期”,指的是人類的童年階段;特定“文體”,指的是講述這一階段神話傳說,或人類重大事件的敘事長詩。進入現代社會后,這一文體隨之消失,它成為人類永遠不會復現的童年鏡像。
作為一種“文體”的“史詩”雖然消失了,但“史詩性”卻作為一種美學積淀留存在文藝作品中。“史詩精神在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敘事藝術中得以延續,以審美范疇——史詩性的形式存在。”[2]從特定的“文體”,演化為一種跨越時空的“審美范疇”,“史詩性”成為人們對民族歷史進行審美觀照與美學表達的重要載體。
從字面意思來說,“史詩”包括“史”與“詩”兩個層面。“史”首先意味著一定的歷史跨度,比如《白鹿原》涵括了渭河平原半個世紀的變遷;其次意味著在長時段的歷史跨度上,關注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這些歷史事件勾連出民族的發展進程,《白鹿原》中的內戰、抗戰可作如是觀。“詩”則意味著文學性的表達。也就是說,它不是對歷史的直接展示,而是通過跌宕起伏的情節、豐富的細節來講述歷史大背景下的世事變遷與人物命運,最終建構出民族的“精神圖景”,誠如《白鹿原》扉頁上所引巴爾扎克的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所謂“秘史”,自然包含著精神層面的內容。
歷史變遷、精神圖景,這些審美內涵,可以被視為“史詩性”的“質的規定性”。從這個視野來看《地久天長》,就不難發現該片對“史詩性”有著或顯或隱的追求。
將《地久天長》放在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序列中,可以看出該片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那就是對長時段歷史的觀照,這可能也是該片給觀眾留下的突出印象。一個中國工人家庭在三十多年中的命運,被導演娓娓道來。雖然該片使用了非線性的敘事方式,但時間脈絡依然清晰可辨。這三十多年之所以被視為“長時段歷史”,不僅因其跨度之長,更是因為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在這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因改革開放而獲得了長足發展,物質財富迅速積累,人們的生活條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地久天長》以具有時代感的影像呈現出三十年來生活空間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街道拓寬,高樓拔地而起;寬敞明亮、設施齊全的大醫院取代了簡陋落后的小醫院;英明一家從擁擠的筒子樓搬進舒適的大房子;桌上的下酒菜從一盤花生米變成了大魚大肉;出行工具由老式自行車變成了小汽車,而影片最后,麗云和耀軍乘坐飛機返回故鄉,更是凸顯了出行方式的“現代感”。我們置身在社會變遷的舞臺上,或許對這些變化習焉不察。然而,當影片以豐富的畫面將這些變化呈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們仍然能夠清晰地感知到時代的發展脈絡。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增加,更是人們觀念的嬗變。影片中的幾個主要角色,最初都在國營工廠工作,他們穿著單調的工裝,過著集體化的生活。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大鍋飯”開始解體。大家不再執著于統一標準,而是追求各自的道路;也不再故步自封,而是求新求變。社會思想則變得開放和多元。就此而言,影片所表現的時空,分明體現出“史詩性”的特征。
影片內容涉及諸多歷史性的事件:計劃生育,企業改制,工人下崗,南下打工潮,出國潮,房地產開發等。影片中,幾個主要角色都在鋼鐵廠上班。很快,他們遇上了企業改制。為完成下崗指標,工廠說服“先進工作者”下崗。他們被召集到大禮堂,工廠領導以“我不下崗誰下崗”鼓勵大家自謀職業走向社會。安靜的禮堂里工人們神色凝重和慌張。最終,麗云不幸下崗,她臉上閃爍的淚光凝縮了改革的陣痛。在經歷陣痛后,影片中人物的命運朝著不同的方向延伸。美玉南下打工,耀軍夫婦在承受失獨之痛后前往沿海生活。英明投身房地產開發成了大老板。茉莉則走出了國門。
這些歷史性的事件不僅是影片中耀軍與英明兩家人活動的背景,一些事件還成為情節的一部分。其中,計劃生育,是對人物命運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影片的敘事內核是“失獨”。耀軍夫婦的失獨之痛是雙重因素的疊加:一是耀軍愛子星星的意外溺亡;二是海燕態度堅決地帶麗云去做人工流產,由此造成麗云不孕,讓“失獨”成為耀軍夫婦終生的傷痛。如果說溺亡是個不可控的突發事件,那么流產導致不孕則是人為的結果。在計劃生育的時代語境下,麗云被強行帶往醫院做手術。耀軍雖有反抗,但終歸無能為力,只能絕望地用手捶打著墻上“計劃生育”的宣傳畫。耀軍夫婦的內心創痛,都與英明一家有關。影片中英明一家三口對耀軍夫婦的負疚與救贖讓敘事充滿張力。可見,計劃生育,這一特定的時代話語,深深地嵌入人物的命運。一直以來,反映計劃生育的影片并不多。就此而言,《地久天長》通過向觀眾展現特定時代語境下人物的命運,使自身具有較高的辨識度。
除了耀軍與英明兩家外,還有一條副線,就是新建與美玉相愛、結合的故事。實際上,沒有這條副線,影片的故事依然完整。那么,這條副線承擔了什么樣的敘事功能呢?影片中新建最先感受到文化的解凍。他拿著錄音機,聽著鄧麗君的歌,后來因為嚴打被捕入獄。出獄后遠走海南,與美玉結合。顯然,這條副線所承擔的功能更多的是展現文化觀念的嬗變。
可見,“時代變遷”不僅是影片的敘事語境,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片隱性的“主角”。對“時代變遷”的言說,讓影片具備了“史”的內涵。而“史”的內涵又與“詩”的表達密不可分。影片借助人物命運的敘述,讓“時代變遷”轉化為民族的“精神圖景”。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形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都被影片所展現的“長時段歷史”重塑。由此,影片所展現的三十多年中的歷史事件與文化景觀,都成為民族的“集體記憶”,諸如計劃生育、企業改制、工人下崗、南下打工,莫不如此。此外,影片還用密集的細節強化了“集體記憶”建構。筒子樓、車間、具有時代特征的宣傳畫與標語、舞會、喇叭褲、雙卡錄音機、熱水壺、具有鮮明時代印記的歌曲,甚至是孩子們玩的游戲機,都能夠喚起人們對特定時代的記憶。進一步而言,“集體記憶”并非人們對時代表象的記憶,它意味著無數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奮斗、悲歡離合等心路歷程。事實上,影片所建構的“集體記憶”,正是民族的“精神圖景”。凡此種種,都體現出《地久天長》對“史詩性”的追求。
二、解構宏大敘事:第六代導演的“反史詩”趨向
有學者將傳統的“史詩性”審美特征概括為“民族性”“整體性”“英雄性”“全景性”四個方面。然而,在后現代語境下,全景性、整體性、英雄性等宏大敘事受到冷遇,而碎片化的“小敘事”,凡人、常人乃至庸人的“日常生活敘事”受到青睞和關注,從而出現“反史詩”趨向[2]。這樣的審美趨向,契合了第六代導演的創作實踐。實際上,第六代導演從一開始便體現出解構宏大敘事的審美特征和“反史詩”的敘事風格。
論者常將第六代導演與第五代導演進行比較。這一方面是因為二者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另一方面在創作上又顯示出質的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第六代導演的影像敘事特征正是借助第五代導演的參照才得以呈現。雖然在快速的商業化語境中,人們已經很少使用代際視角觀照當代中國電影,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第五代”“第六代”的確成為研究中國電影創作的有效視角。
在筆者看來,“第五代”“第六代”之所以成為有效的觀照視角,根本上是因為這一視角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文化轉型若合符節。都市化、世俗化的進程成為第六代導演創作的時代背景,而隨著社會轉型,時代的審美趨勢也在發生變化,由此,第六代導演在對第五代導演的反思中開啟了自己的創作之旅。早在1993年,第六代導演就對第五代導演的標志性作品《黃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部作品把黃土地上人們的生活“風格化”了,由此“導致了一種以浮淺的社會學、文學、文化學甚至精神分析解釋自我作品的風格”,而這種混沌的、盲目追求風格化的時代應該結束了[3]。
“風格化”意味著第五代導演的電影所展現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對“生活”寓言化的、隱喻化的表達。第五代導演大多在時代的動蕩中有著切身的浮沉體驗,這讓他們對中國文化有著比較自覺的反思意識。有論者認為,“第五代導演是主體意識自覺和強化的一代。追尋和建構歷史主體性和大寫的人的形象,一直是第五代導演的精神主流”[4]。也正因此,第五代導演偏愛歷史表述與文化反思,對“宏大敘事”有著內在的追求。《黃土地》中,陳凱歌導演運用象征化的表達手段,淋漓盡致地呈現了黃土地上人們的堅忍。《霸王別姬》跨越半個多世紀,用宏大的敘事結構,表現出歷史的動蕩和民族的不幸。《紅高粱》以隱喻性的影像語言,對民族的內在力量予以浪漫的表達。《菊豆》則批判了宗法秩序對人性的摧殘。正如論者所指出的那樣,“第五代影片大體上是一種宏大的歷史敘述,是對民族、國家歷史的想象和敘述,即使敘述個人的事情,其象征隱喻的內涵又使之超越了個體”[4]。
第六代導演恰恰是將宏大敘事、文化反思意識,以及相應的修辭性的影像表達視作“風格化”窠臼。他們普遍缺乏第五代導演在時代中的浮沉體驗,但他們成長于經濟復蘇的開放年代,都市化進程、世俗化進程,讓他們更為關注社會轉型背景下個體的生命體驗,而不是群體的命運變遷。在第六代導演的創作視野中,“大寫的人”轉變為平凡之人、底層之人,他們身上毫無光環。第六代導演的創作并非始于群體命運與文化反思,而是來自創作者對生活的感受,甚至是對生活的感覺。《北京雜種》《頭發亂了》《長大成人》《小武》《十七歲的單車》等影片都可作如是觀。當“風格化”消失后,“生活”以赤裸的形態出現在第六代導演的鏡頭前。當他們不再借助寓言化、隱喻化的手段后,他們便與生活“短兵相接”了,相應地,修辭性的表達轉化為原生性的表達,“紀實”遂成為第六代導演的影像風格。
對平凡人物的關注、對生活的原生性表達,以及相應的紀實美學,都意味著第六代導演在創作上有著“反史詩”的趨向。這種趨向讓傳統的“史詩性”產生了變異。也就是說,當第六代導演希望在更廣闊的歷史維度上進行影像呈現時,“史詩性”最終結出了“后史詩”的果實。
三、個體創傷:《地久天長》的“后史詩”敘事
當第六代導演在長時段的歷史跨度上展開影像敘事時,他們獨特的創作美學使得傳統的“史詩性”演化為“后史詩”。這種“后史詩”敘事,呈現出新的形態。“小民性”“日常性”是其主要特征,“小民性”意味著作品所表現的人物不再是英雄,也不再是社會上的精英,而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日常性”意味著作品所表現的乃是世俗生活[2]。“小民性”和“日常性”,都是解構宏大敘事的結果。對《地久天長》來說,“后史詩”敘事還意味著修辭性的影像被紀實性的影像所取代。
《地久天長》圍繞個體創傷展開“史詩性”的敘事。影片中耀軍、麗云夫婦痛失愛子,這對耀軍、英明兩個家庭來說,都是創傷性的事件。這一創傷性的事件雖然也與時代有關——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讓耀軍夫婦無法再生孩子,這讓創傷無法隨時間而平復,但總體而言,這一創傷更多地與個體命運有關。它并非歷史性的事件,而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而影片也用生活化的影像展現了時代的發展與世事的變遷。
《地久天長》中的人物毫無疑問都屬于“小民”,他們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有著蕓蕓眾生的期待與快樂,也有著蕓蕓眾生的性格弱點。在影片中,浩浩一直沒有勇氣坦白自己的過失,多年來選擇逃避痛點和隱瞞真相;主角耀軍夫婦,沒有宏大的理想,只想得到和諧的家庭生活,而從耀軍出軌茉莉,也可以看出他們在道德上并不完滿。
影片中,耀軍夫婦默默地承受了命運所帶來的傷痛。對于墮胎、下崗,耀軍夫婦顯得非常“被動”,他們沒有抗爭,也沒有憤怒的吶喊,在時代的浪潮中他們選擇了隱忍,選擇了承受。被動性,是“小民”,而非“英雄”的性格特征。然而,小民有小民對待命運的方式,他們遠走他鄉,在陌生的地方忘記傷痛,在光陰的流逝中撫平傷痕。他們既有小民的沉默,也有小民身上韌性的人格力量。正如論者所指出的那樣,“‘第六代’導演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歷史英雄,而時常是一種人格英雄”[3]。事實上,正是人格的力量讓影片中的每一個人達成了與現實的和解,也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在影片中,麗云說:“時間已經停止了,剩下的就是等著慢慢變老。”這是有別于“進步敘事”的時間觀。在傳統的“史詩性”作品中,主要人物承擔著“進步敘事”的功能。也就是說,主要人物的性格、命運、主體精神,都與時代的進步息息相關。然而在《地久天長》中,承受著失獨之痛的耀軍夫婦,卻似乎脫離了火熱的時代。他們生活在時代的邊緣,那里安靜如常,時間的流逝不是以“變化”的形式出現,而是以“不變”的形式悄然發生。當耀軍夫婦時隔多年回到舊居時,發現老屋子中的各種擺設一如幾十年前,在老屋子里,時間停滯了。只有樓道里微微閃耀的“按摩店”的牌子,顯示出時代的巨大變遷,反襯出耀軍夫婦與時代的疏離。影片由此顯示出與“進步敘事”的差異,而這一點,正體現出“后史詩”的敘事特征。
與解構宏大敘事相適應的,是“去修辭化”“去象征化”的影像呈現方式。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第六代導演紀實的影像風格。大量的家庭生活畫面,建構起影片的“日常性”。影片中的一些畫面,比如頻繁出現的麗云炒菜、耀軍就著花生米喝酒的生活場景;耀軍夫婦家中因大雨進水,雜亂的物品在水上漂浮等畫面,都具有很強的寫實性,甚至因此影響到畫面的美感。如果說美感是一種修飾,那么影片則為了寫實的效果拒絕了這種修飾。生活本身,而非對生活的修辭,成為《地久天長》的影像主體。
總體而言,在商業化的背景下,作為一個創作群體,第六代導演的代際特征正在模糊;作為一個評論范疇,“第六代導演”正在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這一切并不妨礙創作者的藝術探索。在《地久天長》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在長時段的歷史跨度上對集體記憶的影像建構、對“史詩性”的追求,但這種追求有別于傳統的“史詩性”表達。導演帶著“第六代”的印記,將平凡人物的命運放在開闊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表現,“史詩性”的追求最終演繹出“后史詩”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