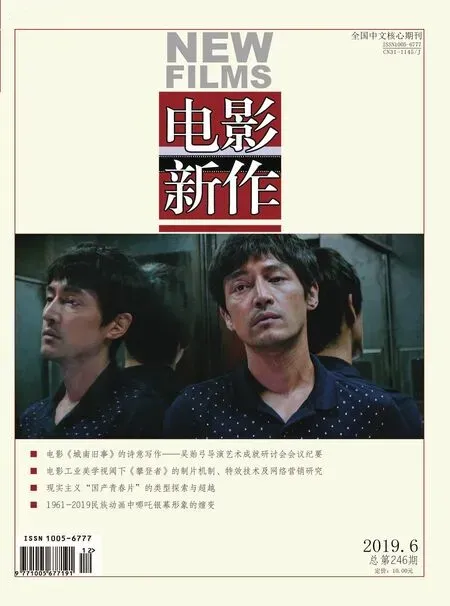解析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中配樂的三重功能
陳曉卉
英國是搖滾樂的故鄉。這里曾經誕生過引領全球搖滾樂風潮的滾石樂隊、披頭士樂隊、綠洲樂隊,還有鼎鼎大名的皇后樂隊。今天歌迷們耳熟能詳的“WE WILL WE WILL,ROCK YOU”,以及體育類節目中一次次唱響的《We Are the Champions》的歌聲,均出自于皇后樂隊的創作。而曾經為樂隊帶來無數榮耀的代表作《波西米亞狂想曲》,更成為搖滾樂壇不朽的經典之作。著名導演布萊恩·辛格以這一曲名為題,創作了一部驚世駭俗的音樂人物傳記類電影,重溫皇后樂隊主唱人物極不平凡的音樂人生。在第76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頒獎典禮上,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折桂劇情類最佳電影和最佳男主角兩項大獎。從電影創作的整體風格來看,戲劇進程與配樂之間環環緊扣,來自于皇后樂隊的多首經典作品引導著劇情的起承轉合。從另一角度來看,似乎又在用電影情節在詮釋著每一首作品復雜而深刻的創作初衷。在傳記類影片最為重要的復刻與重構兩個層面上,電影配樂分別指向戲劇主題詮釋、人物性格塑造和情境升華這三重功能,成就了影片文化內涵由內而外的生成與呈現。
一、詮釋電影主題的文化內涵
音樂人物傳記類型的電影并非鳳毛麟角,近年來相繼推出的《莫扎特傳》《玫瑰人生》《靈魂歌王》《海上鋼琴師》等作品使觀眾無數次感動于音樂大師的燦爛人生。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創作理念與一眾同類電影題材相比,力求體現出“和而不同”的新格局。傳記類電影的拍攝通常是在復原人物和事件真實形象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潤色修飾,以豐富電影的戲劇性。這類影片的拍攝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氣,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盡可能還原主題形象,保持與史實的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本宣科,需要一定程度的虛構和創新。如何把握“度”的權衡,往往決定著作品最終的成敗。以《波西米亞狂想曲》為例,影片將重心聚焦于皇后樂隊的主唱弗雷迪·莫秋里。講述其組建樂隊,開創華麗搖滾流派,實現音樂夢想的生平履歷。通過整個故事線索的延伸,深入淺出地體現出對于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尋求人在精神高度層面的掙扎、求索與解放。影片既然以其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名曲為名,自然將音樂放置在重要的位置高度,以音樂點燃影片戲劇內涵的生命之火。
影片為完成“傳記”風格的創作使命,節選了皇后樂隊從創建到謝幕的整個歷程,前后時間跨越了幾十年之久。如果按照常規的拍攝手法步步為營,不免會有流水賬之嫌,或者對于每個戲劇細節只能淺嘗輒止,無法濃墨重彩。但是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拍攝顯然沒有默守成規,選擇了一條“用音樂點睛事件”的鏡頭聚焦方式。這樣一來,既滿足了樂迷的審美,也顧及到了影迷的情懷。影片并沒有以主人公或樂隊名稱命名,而是選擇了用那首巔峰之作《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歌名。如若沒有對這首歌曲的創作深度了解,很難讀懂導演的良苦用心。
首先,這首歌曲可以代表皇后樂隊最為卓著的樂壇地位,影片以此命名,無疑是在向經典致敬。原創單曲《波西米亞狂想曲》經歷了漫長的制作周期之后,在1975年11月收錄于專輯《A Night at the Opera》正式發行。這首作品的制作成本是當時全英地區最為昂貴的,樂隊還為這首歌曲制作了全球首個商業MV。鋪天蓋地的宣傳造勢席卷全球,歌曲曾經創紀錄地在英國電臺一天播放了36次,連續四周在英國流行音樂排行榜位居榜首。歌曲《波西米亞狂想曲》所創造的華麗搖滾樂風影響了20世紀后期的諸多重金屬樂隊,成為萬人敬仰的搖滾樂榜樣力量。電影導演之所以用歌名來命名影片名稱,正是感受到了這首歌曲與樂隊名稱、主唱者以及其偉大音樂功績的密切關聯。以歌名代指人物和整個戲劇主題,用作品來為其非凡的榮譽正名。
其次,這首歌曲風格的特立獨行,可以完美體現影片內涵對于“自由”和“不拘一格”的呈現。一首常規歌曲的創作,往往只含有一種唱法類型。即便偶爾出現跨界風格,也無外乎兩種唱法的混搭。《波西米亞狂想曲》在短短六分鐘的音樂進程中,竟然穿插了人聲合唱、民謠、美聲和搖滾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獨創性和聽感。同樣的,歌曲的結構并沒有采用套路化的主歌與副歌交替呈現,而是采用了“人聲合唱開頭——民謠呈示部——歌劇插敘——硬核搖滾副歌——呼應式結尾”的結構脈絡。如果將這種音樂創作立意進行溯源,可在20世紀60年代“海灘男孩”的《完美顫動》和披頭士樂隊的《生命中的一天》中尋得蛛絲馬跡,但顯然,《波西米亞狂想曲》將這一創作風格推向高潮,并為公眾所接受和狂熱追捧。糾結、彷徨、掙扎、叛逆,顯示出那個時代大眾群體共同的精神狀態,也為電影內容對這一主題的解剖與精耕細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本。在布萊恩·辛格導演看來,弗雷迪·莫秋里所向往的自由正如歌曲所顯示出的創新力量一樣,在竭盡全力地挑戰著社會的刻板與保守,追求著人性的徹底解放。
此外,以《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曲名來同構影片之名,也意在借此歌曲創作之靈感來深度剖析弗雷迪·莫秋里的人物身份、理想和心緒。這位才華橫溢的主唱憑借著個人魅力撐起了皇后樂隊的半壁江山。他出生于東非,確是地道的帕西人,印度血統的后裔,長著一口時常被旁人所取笑的齙牙。17歲與家人移民來到英國,由于與眾不同的相貌和種族關系,很難融入主流文化,受到各種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但與此同時,他又擁有常人所無法企及的華麗嗓音,多達四個八度的音域使其能夠駕馭多種曲風。正是得益于對多種文化和宗教背景的耳濡目染,使其在音樂創作中靈感縱橫。
二、揭示影片主人公的雙重性格
音樂傳記電影是一種獨立的電影類型,它有別于《至暗時刻》一類的人物傳記,也不同于《愛樂之城》的歌舞片體裁。影片中對于每一個音符的運用均有著強烈的象征性價值,在融入了時代背景和人物氣質之后,可以形成聲情并茂的敘述空間,使觀眾對傳記塑造的人物主體感同身受。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創作因主人公弗雷迪·莫秋里而生。他的特殊性不僅在于搖滾樂壇當之無愧的巨匠身份,更源自于其特殊的出身,充滿矛盾的心理,渴望進入主流社會群落的潛意識,以及向往自由和天性釋放的夢想。這種人物個體內部的矛盾感成為電影戲劇內容可以無限拓展的基礎,而影片中適時加入的多首來自皇后樂隊的原創配樂,則是自我詮釋和自我消解的最佳伴侶。
一方面,對于主人公的非主流意識形態和無法融入主流社會之苦,影片用貫穿式手法將這一人物特性竭力表達,并借音樂之力渲染,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影片中多次直觀感受到皇后樂隊演出時極富個性的音樂風格和夸張癲狂的表演舉止。另一方面又通過行為舉止的張揚,在為自己尋找勇氣和歸屬感。然而,即便在他獲得成功之后,他蹩腳的名字、突出的牙齒、隱秘的性取向仍然成為眾矢之的。導演用抖動和近距離的鏡頭頻繁在記者和弗雷迪·莫秋里之間切換,一面是咄咄逼人的窮追猛打,另一面則是手足無措的慌張惶恐。
以上種種在電影鏡頭中意欲表達的離群之悲,除了用各種事件和人物的表情、語言、舉止進行詮釋,適時出現的配樂也恰到好處地形成同步的聽覺關聯。巧妙的是,影片主創者幾乎全部運用了弗雷迪·莫秋里創作并演唱過的經典之作。比如:在影片開頭,主人公在機場搬運著沉重的行李,生活的窘迫和內心的不自信在鏡頭中明顯表現出來。背景音樂選擇用翻唱版的《過得還好》與此情此景搭配,略帶調侃和自嘲的歌詞,體現出弗雷迪·莫秋里對生活境遇的不滿足,同時又有意回避著別人注視的目光,有一些成年人對陌生之地的無所適從。這首音樂作品出自于樂隊主唱失意時的靈光一現,本身也是皇后樂隊音樂作品中為數不多的以舒緩樂風表達失落心境的歌曲作品。電影開篇處選擇這首歌曲與莫秋里狼狽的生活面貌相對應,可謂恰如其分;又如:面對未婚妻和一生的摯友瑪麗·奧斯汀,弗雷迪·莫秋里寫下了皇后樂隊最柔情的一首歌曲《Love of My Life》。在影片中,這首歌曲作為他向瑪麗表明心跡,終止戀人關系時的配樂,飽含了內心的愧疚和款款深情。這首歌曲在電影中的選擇,精確還原了史實,重溫了莫秋里對瑪麗的愛意和歉疚。歌曲用抒情搖滾風格表達莫秋里的浪漫情愫,與電影畫面中柔和的燈光和緩速的特寫鏡頭相得益彰。從電影引申的畫外音來看,這首歌曲中所帶的哀怨氣息,也悄悄透露了莫秋里最終選擇了放手,選擇忠于自我,而正是由于無法言明的性取向,也使他長期游移于社會邊緣,無法正視自己的存在感。在經歷了成功的喜悅和音樂成就的巔峰過后,弗雷迪·莫秋里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仍舊回歸到孤獨清冷的境遇中,命運終究沒有逃脫揮之不去的陰霾。
影片行將結束之際,一首《The Show Must Go On》縈繞于銀幕空間中。熟悉這首歌曲的樂迷都知道,它的原版音帶錄制于1990年。當時的弗雷迪·莫秋里已然病入膏肓,歌曲由樂隊的吉他手創作。弗雷迪·莫秋里精神振奮,在錄音棚一鼓作氣,唱響人生最后的絕唱。歌曲以第三人稱的視角給予弗雷迪·莫秋里無限的關懷和希望,憐憫其所遭受的社會不公待遇,理解他內心所不為人知的創傷與困苦。影片選擇這首作品片尾的壓軸之作,用意在于兩點:一方面,敘事體傳記電影保持了對人物生平總體面貌的真實還原。此時選擇這首歌曲,符合莫秋里臨終前的心境,作為與世界告別的絕唱,這首歌曲使影片看上去更加完整,有始有終,符合樂迷的審美情愫。另一方面,歌曲本身具有對人生和世界的無限展望。將其放置在片尾位置,使影片的終止感弱化,余味悠遠,借音樂之手延續電影的畫面空間。
另一方面,無論是籍籍無名時主動的毛遂自薦,或是成名之后陷入失落的困局時,影片均展示出弗雷迪·莫秋里對融入群體和渴望認同感的熱切期盼。電影通過兩個具體事件體現主人公的這種性格面貌。一個是在皇后樂隊如日中天時,弗雷迪·莫秋里風光無限地站在舞臺上,引領數萬歌迷一同唱響《We Will Rock You》,那一刻可以感受到弗雷迪·莫秋里全身心地沉醉其中。當這首象征著力量和希望的配樂奏響時,無數影迷眼含熱淚。他們見證了弗雷迪·莫秋里為換來短暫人生榮耀而付出的艱辛和努力,更看到一個搖滾青年內心澎湃的熱血和對歸屬感的渴求。另一個是他與瑪麗·奧斯汀的第二次相遇,他其實正在為自己挑選心儀的女裝。片中,他留著長發,涂著顏色絢麗的眼影,穿著緊身皮褲。女性化的著裝風格并沒有受到奧斯汀的嘲諷,而是給予他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這使弗雷迪·莫秋里感受到并沒有被社會完全邊緣化,即便只有一個人能夠懂他,也足以溫暖寒冷的心。此時,背景音樂響起了溫情的舊曲《生而愛你》,緩緩流淌的音樂中夾雜著復雜的感情。這里“愛”的對象,包括了生活、憧憬和希望。這首配樂作品在此處戲劇情境中的出現,除了旋律及風格與電影格調的呼應,更重要的是想表達一種人文關懷。即便莫秋里的隱私被曝光,但作為深愛著他的女人,可以用愛來包容他的一切。此時的歌曲中充滿了善意和寬容,也是對戲劇畫面的深層文化寓意注解。
三、推動戲劇矛盾的激化與消解
傳記體電影用臨摹的方式重構一張歷史的“草圖”,將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還原,使當代觀影者能夠客觀多面地了解過往。由于影片時長的限制,往往會選擇某一個特定的切入點和視角,擺脫紀錄片的乏味之感,用具有戲劇性的敘述方式進行表達,并根據主觀愿望進行修飾,尋找矛盾對立面。有些戲劇矛盾體出自于正反派人物的較量,有些則來自于人物內心情感的矛盾。就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而言,片中只有一個明確的反面人物——見利忘義的經紀人保羅。
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主人公與命運的互搏中。一方面,他桀驁不馴,有著非比尋常的傲骨;另一方面又心思敏感,容易受到傷害。由于這一內在矛盾的發跡點被開門見山地呈現出來,促使片中他的每一次努力、成功、犯錯、無助都是矛盾對弈失衡造成的結果。在弗雷迪·莫秋里與眾不同的華彩人生篇章中,三位樂隊成員和“一生摯愛”瑪麗,共同給予他足夠的精神支撐和音樂創作動力。而作為主人公本身,在對待生活和朋友的時候,則夾雜著熱情、勇氣、脆弱、無奈和肆無忌憚的放縱。如此交錯和豐富的內部矛盾對立體,使人物角色變得立體多元。隨著越來越多來自內心的扭曲和外在客觀力量的畸變,弗雷迪·莫秋里逐漸走向痛苦的深淵,甚至連命運也不再受自己掌控。但驀然回首,即便物是人非,仍然有一種力量可以搭救迷失的心,重塑其生命的閃耀光芒。這就是音樂,也只有音樂。
在影片的最后20分鐘,曾經被奉為經典的1985年皇后樂隊溫布利球場“拯救生命”演唱會被創作團隊精心復刻。影片事無巨細地將30多年前的演唱會實錄進行重塑,從形態上看來,忠實的還原程度大到演員的表演姿態和歌唱曲目,小到舞臺的布局、樂器的擺放、觀眾和記者的著裝,就連電聲樂器在地板上的布線方式都按照舊時的模樣。
此時的弗雷迪·莫秋里已然功成名就,在享受樂迷的萬般寵愛之余,也經歷了人生誤入歧途之后的清醒與悔悟。莫秋里與樂隊成員盡棄前嫌,重新回歸。在得知自己罹患艾滋病之后,百感交集的他也在崩潰過后與自己的人生慢慢和解。在生命即將結束之際,也許,只有音樂才能使他的心靈得到救贖。片中,他如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刻一樣,身著白色背心和淺藍色牛仔褲,坐在鋼琴邊靜靜地彈出《Bohemian Rhapsody》的旋律。而作為與世界最后的告別,弗雷迪·莫秋里用一曲《波西米亞狂想曲》結束自己的歌唱生涯,也在高潮中結束了整部電影。為渲染高潮迭起的音浪,電影原聲音樂并沒有直接復制莫秋里的聲音,而是將拉米·馬雷克、馬克·馬爾泰勒和弗雷迪·莫秋里三人的聲音進行混合處理,既有復古聲音魅力的重現,也有當代搖滾樂更為勁爆的力量感。在璀璨炫耀的光芒落幕瞬間,影片也戛然而止。一位搖滾巨匠的生命隕滅,留下的唯有意猶未盡的品味和長長的感嘆。
結語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作為一部成功的音樂人物傳記類作品,成功將音樂、人物、戲劇事件三者完美融合在一起。音樂充當了一種潛在的重要素材,不同于一般電影作品中的配樂。這些熟悉的旋律由真實的主人公創作并演繹過,透過歌聲,可以洞悉弗雷迪·莫秋里所走過的不凡人生,也在歌聲中深刻感悟他內心的糾結、矛盾和勇氣。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借經典歌曲命名,將音樂靈魂注入戲劇主題。配樂風格所體現出的明暗變化,構成了弗雷迪·莫秋里氣質性格的雙重對立,在過渡轉換中引導戲劇劇情的跌宕起伏。最終,人物生命的輝煌和悲劇在無法調和的狀態下匯集成一臺山呼海嘯的演唱會,用音樂的力量抹去一切憂傷、隱痛、懊悔和難以割舍的情懷。一言以蔽之,音樂多元化的功能成就了這部電影的酣暢淋漓,也在旋律音符中向弗雷迪·莫秋里和皇后樂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