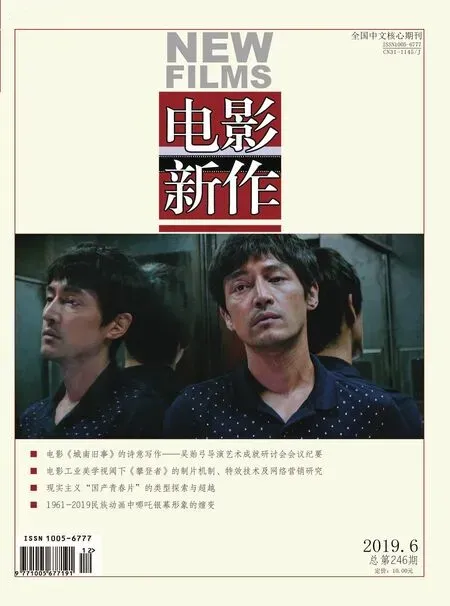1961-2019民族動畫中哪吒銀幕形象的嬗變
彭慧媛 李柯穎
中國動畫電影鼻祖萬籟鳴先生曾在《閑話卡通》中說“要使中國動畫事業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必須在自己民族傳統土壤里生根”。中國民族文化深厚的文化資本所孕育的民族風格在動畫藝術領域大放異彩,自1941年中國第一部動畫長片《鐵扇公主》誕生之日起,民族動畫創作者們就堅定著追尋和探索民族風格的文化自覺,不斷從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中汲取力量。早在20世紀60年代,以中國動畫學派為領軍,確立了民族動畫的美學范式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動畫最杰出的成就——民族風格。
哪吒,作為中國神話故事中經典人物和民族文化符號,自出現以來,不斷被文藝創作者進行民族化取用、創造,在多種樣態的藝術化過程中承載著民族情感和價值認同。從1961年到2019年,我國文化語境、社會風貌經歷了近60年的巨變,哪吒形象也以民族動畫的形式為載體,相繼經歷1961年《大鬧天宮》、1978年《哪吒鬧海》、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三次典型的銀幕演繹,呈現出視覺形象、敘事結構、價值訴求的差異性,代表著各自時代里中國動畫的民族風格最高典范,折射出我國民族動畫的審美特質和影像嬗變歷程。
近年來國內動畫電影相繼出現《大魚海棠》《大圣歸來》等多個現象級熱潮,2019年暑期爆款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簡稱為《魔童》),以近50億元票房的成績,成為中國最賣座本土原創動畫,“國漫崛起”的贊譽不絕于耳。“叫好叫座”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觀眾對影視作品的文化需求和審美傾向,以及動畫生產和工業水平取得了突破性成績,然而反觀這些影片,會發現他們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題材表面化、主題同質化、唯技術論,以及過度借鑒等弊端。在全球化和國內主流文化在恰當的歷史路口,我們該如何開掘民族傳統文化和神話題材的同時又葆有民族核心精神內涵,中國動畫的民族性如何尋找創新的活力,成為亟待探索的時代課題。
一、哪吒銀幕形象的演變歷程
民族集體將對信仰與向往付諸于文學藝術的特定主體中,凝聚成民族精神的標志——神話,不同時代的藝術創作者和民間智慧共同創造著文化形態和集體想象,周而復始地在不同“講述神話的年代”里重新呈現“神話講述的年代”。梳理哪吒形象的演變首先要基于中國歷代造神過程、宗教思想和民間力量的共同作用,經過傳說、小說、戲曲、話本的通俗藝術形式演繹,哪吒形象由“哪吒護法神”形象日趨通俗化為“哪吒英雄神”形象。
哪吒的最早記載源自中亞佛教:“忽若忿怒哪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攝慈光。”哪吒的佛教原型三頭三眼六臂,威猛兇悍,作為護法神、夜叉神,輔佐毗沙門天王(李靖原型),忠誠衛護佛法,掃除邪惡,這一基本形象固定至北宋初期。南宋時期,人們將佛教故事進行了本土化重塑,哪吒成為毗沙門天王李靖之子,正神形象被廣泛認定下來。明代“儒釋道三家思想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也互相斗爭。在這種形勢下創造的哪吒神形象也有三教混一”的特點,此后明代的通俗小說、曲藝,以及后來的《封神演義》《西游記》基本形成了我們目前人們所熟知的哪吒兒童形象框架。有關哪吒的故事講述,都必然要與原記載、此前版本進行比對,凝練和創造出新的形象與敘事特征,而時代文化語境決定了語義關系和改變,哪吒形象的再書寫、再創造,顯示了中國動畫自己的獨立品格。
(一)《大鬧天宮》中的神勇戰神形象
1961年這個時間點,屬于十七年電影和“中國動畫學派”興盛的時期,萬籟鳴導演領銜制作的《大鬧天宮》是中國動畫黃金年代里的集大成之作。影評家凱恩·拉斯金曾贊譽稱“這部影片可以和《圣經》中的神話故事以及希臘民間傳說相媲美,他們同樣是充滿了無窮的獨創性、迷人的時間、英雄式的行為和卓越的妙趣,影片通過杰出的美術設計而成為一部擁有強烈感染力的作品”。
本片講述孫悟空不滿天庭招安,與天兵天將在花果山大戰的故事,哪吒作為天庭派出的一名天神,與猴王斗法,哪吒的故事角色是執行神勇天將忠誠戰斗的敘事功能,反面角色哪吒,造型臉譜化、性格單一化,用以襯托孫悟空的集猴性頑劣、人性善良、神性法力為一身的豐滿形象。形象很大程度上依循了《西游記》原著第五十一回“額闊凝霞發髻髽。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環絳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襯戰靴”的描述,結合了民間藝術的傳統美學元素,“三頭六臂”“玉面嬌容”“身小”的外在特點,年畫里紅肚兜、雙發髻的胖娃娃樣式,創造性地采用京劇白臉元素,三角眼略帶陰狠,腳踏風火輪,手擒乾坤圈,突出“奮怒”“兇惡”的性格和勇猛剛強的“斗士”角色設定,通過精美的工筆畫描繪,實現了神采奕奕、神勇無比的外形和個性的鮮明塑造,十分貼合人設內涵和敘事需求—天威強權的代表,孫悟空正義行為的反抗對象。
(二)《哪吒鬧海》中的悲劇英雄形象
《哪吒鬧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獻禮影片,由嚴定憲總導演,王樹忱編劇等動畫界精英集體制作,在短短65分鐘內施以濃墨重彩的寬銀幕長篇動畫。承襲了《大鬧天宮》在工筆重彩美學技藝和高超的意境化處理手法,《哪吒鬧海》整體風格靈動雋永,藝術性成就極高。
與前作取材不同,本片故事源自《封神演義》神魔小說體系,敘事核心集中在“哪吒”人物上,在審美傾向上更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道家美學意味。劍眉星目,正氣凜然,灰白色長上衣,素褐色長褲,用自然簡淡的筆觸和大量留白的畫面勾勒人物所處的環境,呈現天人合一審美意境。經改編后,哪吒成為反封建反黑惡勢力的正義形象,紅色飄帶飄揚,手持乾坤圈的造型,十足的小英雄。完全脫離《大鬧天宮》中的單一面貌,從面露兇相的“戰神”,轉變為血肉豐滿的“人神”,宣告中國動畫界重歸傳統文化。
2003年,中央電視臺《哪吒傳奇》系列動畫片,可視為1978年《哪吒鬧海》在電視劇中的延續,“少年英雄小哪吒”人物設定和正邪對立不變,塑造“我們的朋友小哪吒”的親和形象,開啟新時期哪吒的序曲,奠定此后一大批哪吒影視一輪輪的新講述。
(三)《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魔童形象
新編的人物、完整的敘事、吸睛的特效、成功的營銷,是《魔童》成功的四大要素。它的出現,打破了長久以來“孫悟空”“西游”IP在中國動畫題材的壟斷局面,啟迪影視創作者向中國傳統神話故事、傳統文學里開掘新故事、新人物、新素材。
故事講述“天地靈氣孕育出一顆能量巨大的混元珠,元始天尊將混元珠提煉成靈珠和魔丸……太乙受命將靈珠托生于陳塘關李靖家的兒子哪吒身上,然而陰差陽錯,靈珠和魔丸竟然被掉包。本應是靈珠英雄的哪吒卻成了混世大魔王。調皮搗蛋頑劣不堪的哪吒卻徒有一顆做英雄的心。然而面對眾人對魔丸的誤解和即將來臨的天雷的降臨……”串聯起了哪吒親情、友誼、自我追尋和反抗命運的故事。
人物形象塑造也伴隨故事新編而顛覆。因循前作深入人心的“哪吒”人物基本元素:兒童身形、紅肚兜、雙發髻等相關符號之外,大膽創意“丑哪吒”形象,打造了一個黑眼圈、血盆大口,穿蘿卜褲,雙手插口袋的叛逆少年形象。充滿現代感的臺詞,玩世不恭的表情姿態,頹喪的語調,惡作劇行為,都貼合“魔”“惡”的特點。隨后在哪吒化身戰神時又出現“三頭六臂”的成人身形、超能力英雄形象,當回溯神話哪吒神形象時,既滿足了觀眾的偏愛新鮮感的審美享受,又超出了觀影期待,讓人熱血沸騰。通過比較我們發現,以上三部動畫電影中的哪吒形象由民族風格突出、形式感強、臉譜化的神形象,轉化為情感飽滿、貼合時代訴求的英雄形象,到今天脫胎為一個當代少年與超級英雄混搭的魔童形象,哪吒形象和寓意從傳統定義走向了更開闊的表達空間。
二、哪吒銀幕形象的民族風格變遷
以1961年、1979年、2019年三部涉及哪吒的動畫電影為代表,筆者將民族動畫分為了以三個階段:《大鬧天宮》為代表的民族風格濃郁的美術片時代,《哪吒鬧海》為代表的中國民族動畫風格的成熟時代,《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代表的多元融合的動畫時代。中國動畫也從民族風格的頂峰,逐漸步入全球化大眾文化形態影響下的民族風格弱化和多樣變革中,如今動畫技術信息化更帶來寫實風格的提升,呈現動畫產業在近20年低谷后的上升姿態。
(一)藝術手法:從傳統美術到現代技術
早期國產動畫電影人是一批優秀的中國美術繼承人,他們不僅貢獻出寶貴的藝術作品,更將對中國傳統美學與詩意文化的理解全數灌注于創造,“美術片”正是在這樣文化情懷中誕生。移植與運用中國傳統美術工藝,如水墨、剪紙、蠟染、版畫、皮影等,強調作品的藝術性和文化價值,傳達獨特的民族情感。而“動畫”概念,是由錢家駿在1946年《關于動畫及其學習方法》一文正式提出的,面對這種外來文化,中國動畫先驅們嘗試賦予其信達雅的文藝理想和民族內涵,為我所用,成為承載中華文化的新的藝術形式。
《大鬧天宮》是當時耗資百萬的大片投資,色彩瑰麗的工筆畫卷,整體形式美強烈,突出中國傳統藝術景物處理虛實結合的手法,呈現想象豐富的裝飾性設計。萬籟鳴團隊歷時四年,考察各地建筑、陶器、手工藝品,選用了如意頭云紋樣式,設計出變化莫測的云朵和中式樓蘭亭閣;參考敦煌壁畫,繪制了蟠桃園仙女衣裳輕盈浮動的狀態,人物形象均稍做夸張變形;空間環境設計在鮮明的民族化意味中區別了花果山晴朗明凈、天庭富麗堂皇兩個不同空間。本片開創了動畫音樂制作新的表現手法,即大膽采用了京劇、民樂、昆曲等形式配樂,“在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時則配以輕盈的樂器從而將人物內心世界的忐忑不安與情緒的復雜多變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同時鼓點節奏配合動作,用不同的音樂段落進行劇情轉接,全片動畫視聽異彩紛呈。
《哪吒鬧海》手工繪制七萬幅珍貴水墨原畫,同樣運用了多樣化中國傳統藝術形式和民族元素,融合其中,并推陳出新,簡化環境。強調人物而自然地寫意抒情,最典型的是哪吒死前一幕,作一種超現實處理,小鹿在藍色幕布里伴著琵琶聲輕盈跳躍,哪吒淚眼與雙手交替特寫,線條柔軟,水波似有若無,形成流動的視覺美感。哪吒出生,以輕快活潑的鼓點進行定場亮相,展示可愛的性格和靈活的形態。
前兩部影片同為美術片范疇,在人物造型、景物造型、環境空間等傳統美學元素上有很高的相似性,通過三維動畫視聽再造了“四項變化無窮之妙”的美妙幻境。意境美為觀眾留下無限想象空間,但也引發不同的審美想象,《大鬧天宮》鏡頭語言強調“形”,夸張造型和設計構成強烈的舞臺感,《哪吒鬧海》則強調“神”,在“有”與“無”營造寂靜空靈的情緒,鏡頭平緩移動猶如定點立足,目光遠眺,符合中國畫散點透視的創作方式和靜觀方式。
《封神演義》原著的一大精髓在于“奇觀”,《魔童》作為首部IMAX國產動畫電影,從視聽設計、表意空間、鏡頭設計、觀眾參與度上與前兩部作品有極大差異性。通過3D技術將該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現代感十足的奇觀的堆砌、吸睛特效,都已經成為商業類型片的必要元素。山河社稷圖的包羅萬象的空間、萬龍甲匯成時的美輪美奐,天馬行空的想象力,通過技術具象為視聽盛宴。科技發展帶來了哪吒微微抖動的小肚子,龍王細膩流動的須髯和盤旋的軀體,細節寫實更生動真實;皮克斯風格的電腦繪畫、豐富的場景轉換,太乙真人“七彩仙蓮”指紋解鎖、“指點江山筆”時空穿越等流行元素提高觀影距離和代入感;在動作設計和景別選用上,相較于前兩部,電影語言更明顯,而民族化的美學特征遠不如前。
此外在配樂上,必須提到《小刀會序曲》,自1962年推出以來,被諸多影視作品采用于高潮情節點的氣勢營造,從胡金銓《龍門客棧》到周星馳《大話西游》《功夫》,再到2015年《大圣歸來》,音樂一旦出現,就能立即喚起觀眾對振奮的情感參與和熱切認同。時至今日,對眾所周知的曲調沿用仍是一種安全的燃情套路,更遺憾的是我們的影視作品配樂創作匱乏而保守,這么多年來竟然沒有出現更多有新意的作品來被觀眾認可。
(二)敘事模式:從戲曲樣板到美日模式
哪吒動畫形象發展至今,美術片影像創意與傳統敘事方式、情節程式化的藝術手法式微,而具有現代感的好萊塢經典三模式劇作結構、日本漫畫情節模式成為全球通行的影視法則,對我國當前的動畫作品有諸多影響。
1.敘事策略與人物塑造
《大鬧天宮》采用中國傳統的戲劇式結構,保留原作章回體小說形式,采用主動式單線性敘事方式,“敘事過程中常常以繪畫性的平面鏡頭語言以生動的、聲情并茂的對話圖解文學故事,并輔以戲曲式的表演推動劇情發展,在敘事空間表現上呈現出繪畫性、表現性、意境性等藝術美學特點,呈現出一種戲劇性空間”。《哪吒鬧海》是經典改編案例,在故事上延續了哪吒相關人物關系圖譜和“陳塘關-龍宮-天庭”的故事構架,將哪吒生性頑劣、惡意殺龍,改為:龍王欲求童男童女,危害百姓,哪吒為保護鄉民才殺死敖丙,四海龍王布雨威脅索命,哪吒為救一方百姓,自刎謝罪,節節攀升的沖突,不斷推動悲愴感提升。
在劇本結構上,將《封神演義》原著中的靈珠子設定,改為混元珠,從《哪吒鬧海》的主角哪吒、反派敖丙,變成《魔童》“哪吒-敖丙”雙雄結構,是對前兩部最大的結構更新,是符合當前市場和受眾觀影偏好的選擇。“在肉眼可見的雙雄結構之下,哪吒-鳴人、敖丙-佐助、太乙-自來也、申公豹-大蛇丸、龍族-宇智波一族、陳塘關-木葉村……從人設、性格、背景設定以及最終對決,《魔童》與日本動漫《火影忍者》有著清晰的人物對應關系。”
其次,好萊塢經典三幕劇結構的成功運用促成了《魔童》的流暢敘事,同時符合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貝爾的英雄之旅理論結構。第一幕,建制。通過交代陳塘關背景和混元珠來源,引出申公豹調換雙珠,魔丸降生破壞力極強,將面臨天劫,李靖求天尊解咒,哪吒作惡惹是生非被太乙真人帶入山河社稷圖,聽信自己靈珠轉世后拜師修行;第二幕,發展過程。修煉兩年,逃出山河社稷圖,擒拿海夜叉,解救女孩,與敖丙相識,卻遭百姓誤會,敖丙得知自身重任,誅殺哪吒才能建功立業拯救龍族,哪吒邀請敖丙赴宴,哪吒得知真實身份,并獲得武器裝備,解開乾坤圈咒語,大開殺戒;第三幕,解決問題。太乙真人控制哪吒威力,再次化身童身,得知命符。敖丙身份暴露,決定活埋陳塘關,冰火雙方斗法,遭受天劫,哪吒敖丙共抗天劫,七色寶蓮保住靈魂不滅,留住魂魄后完成救贖,被百姓認可。也有學者指出與日本動漫的燃魂四步結構也有相似之處,雖說中國起承轉合與經典三幕劇結構有相似之處,運用經典的商業類型結構,可以快速獲取受眾歡迎的方式,但《魔童》無論是上述哪種敘事模式都大有借鑒、套用之嫌,且與中國民族化藝術創作方式相差甚遠。
2、情節設置與借鑒問題
情節發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依賴于角色表演動作、對話與臺詞,在美術片時代的顯著民族特點表現為對傳統戲曲、樣板戲的程式化借鑒和使用,在時代氣息中與動畫影像貫通融匯。《魔童》存在著情節拼貼感和經典影視情節借用學習的問題。作者餃子,非科班出身的天才型動畫創作者,他在前作感謝了手冢治蟲、迪士尼等動漫名家,在大量學習和借鑒了日本漫畫、歐美的優秀影視作品中吸取靈感、習得技巧,在此我們通過具體的文本細節梳理,觀察對比情節設定的相似之處。

表1.《哪吒之魔童降世》與其他影視作品情節對比
影片大量使用港片搞笑橋段、動作設計、低俗笑料,通俗大眾文化少有全新的風格,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也不可能有全新的影視創新,對日本動漫的模仿導致了相似度高,本土原創性不足,沒有新意,雖然在技術上有所提升,但對動畫民族性的理解、繼承、結構、立意上還很空缺。
(三)文化價值:保守-開放-回歸
民族動畫的文化價值通過具有強烈民族性特征和內涵來建構,從神話故事中提煉出穩定明確的人物精神內核,在時代環境中勾勒切合文化大眾化思潮的故事主題。現代社會已與神話講述的時代大不相同,在哪吒動畫的改編進程中,主題深度從深刻悲壯到淺顯大眾化,神話象征意義的功能性已經轉變為電影敘事的符號功能,哪吒故事原初的文化價值在銀幕演繹中已經大大改變。
1.原型反叛的消解
我們討論從神話取材時,是在認可所選取人物以及他的核心精神,兩者合一的前提下進行的。在傳統神話中哪吒精神核心是“反叛精神”,與之密切相連的行動集中用強烈的“自我傷害”的情節作為反叛的能指。《封神演義》中的“刮骨還父”,《哪吒鬧海》中的“舉劍自刎”,而《魔童》中對自我傷害只是撕去命符紙條,哪吒反抗力度逐漸縮減,不只是儒家文化孝道對其的改造,也是順應時代文化品格的調適。
《哪吒鬧海》中的哪吒,發展至今天已經成為流行文化中一個反叛精神的符號。它在片中的反叛表述有三個步驟:第一,把龍王從無辜受害改成吃人的大反派,給予哪吒大鬧龍宮的行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正義動機。第二,刪減了哪吒的作惡段落,從邪惡的反骨者變成正氣凜然的反叛者,增加了大眾對哪吒的接受度。第三,將神魔小說中“刮骨還父”以“舉劍自刎”的形式替代,自殺前“程式化”系列動作,極力渲染了對抗的決心和絕望感。那是在特殊變革時代里,人們需要英雄,來寄托革陳除舊、熱血犧牲的精神和決心,成為人們心中獨特的記憶。
《魔童》中的哪吒,將“自刎”改成“撕紙條”這樣的溫柔處理,意指“哪吒自殺”,把以往的大悲化解掉,把自殘、弒父,改寫為父與子換命符、撕命符的相互犧牲,將“反面角色”消解為“正邪合一”,把此前抗爭對象由具象化的“父”“惡”轉變為抽象化的“命運”和“自我”。縱然敘事流暢、人物出彩,但失去了反骨的哪吒還是真哪吒嗎?而哪吒的矛盾過早通過內在“愛”化解,總是處于問題被解決的局面中,被“天劫”“父愛”所推動的,同時,哪吒和敖丙的動機不強,轉變太快,也造成反叛也不夠徹底,最后的大團圓結局更趨近于主旋律和諧的價值觀,片尾處已經丟失了片頭所談的“不信命”的議題。
2.宏大母題的日常化
倫理關系,這個宏大母題伴隨著哪吒故事的變遷,哪吒父子關系的文本溯源,有幾個重要環節。宋代慧洪《禪林僧寶傳》記載問“哪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后化身于蓮花之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此前通俗文藝形式的基礎上明確了哪吒“投胎童身”“怒殺龍王”“殺石磯子”“析骨析肉”“蓮花化身”“天帥之領袖”的重要設定, 但“剔骨還父,割肉還母”之舉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中國儒家孝悌思想大相違背。將道家的舍生取義,以及儒家孝文化融入對佛教的本土化改造,融入繁榮開放的文藝創作中,于是明后期,《封神演義》增加了“父子和解”,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哪吒動畫中父子關系的文學發源。
哪吒作為反權威的圖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反對父權。在動畫世界中這個父權不僅僅是李靖本身,還被引向了更多的表意中——“天命”。1979年版與2019年版,都提到這個詞,正是兩部影片的敘事驅動核心。
《哪吒鬧海》的天命理解為“權威”,當興風作浪的龍王發難時,李靖只敢屈服于上級天神,并指責兒子的正義行徑,在君臣等級和骨肉至親之間說出了“天命難違啊”,懦弱的他繼續擔當一個秩序維護者。當哪吒大喊“爹爹,你的骨肉我還給你,我不連累你”,抒發一種對父輩的絕望的時代情緒。正如蔣勛評價哪吒“這個角色在過去飽受爭議,大家不敢討論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個孤獨的出走者”。哪吒自刎的方式表達對“子道”的反叛,但這種叛逆一定是在主流文化框架以內的,蓮花化身后重獲新生,也重拾了親情。
《魔童》成功將我們時代的情感融入神話新編的過程。哪吒的口號:“我命由我不由天”,“天”成了一種抽象的壓力,現代人的情感呼喊。基于“我命”的自我問詢,我是誰,是魔丸還是靈珠。缺席的長輩是現代家庭關系疏離的寫照,留守兒童哪吒被禁閉在家、社會偏見、孤獨成長這些來自現實主義的境況,讓年輕觀眾產生代入感,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陳塘關的百姓,而我們都是哪吒。《風語咒》《大圣歸來》《魁拔》等,均與《魔童》“我命由我不由天”有類似的議題,2000年的《悟空傳》喊出“逆天改命”,《魁拔》也有“只要還活著,就絕不認輸”的臺詞。當代中國家庭結構和倫理關系被重構,宿命反叛者經歷自我追求后,家庭與社會認同是最好的歸屬,成為這個時代的共同話題。
此外,創作表達不足導致了主題模糊、淺顯。前半篇幅提出了“逆天”的大議題,但前面鋪墊娛樂性太多,不足以撐起如此厚重的議題,難以表達反抗的悲愴感,甚至在打斗戲中穿插笑點橋段,他們再次進入山河社稷圖,被捆綁在一起卻用低俗“屎尿屁”梗,讓前面蓄積起來的壯闊激烈頓時消散,不斷破壞了命運的節奏,緊接著通過煽情點轉而變為父子和解的溫情,徹底地轉移了故事的核心矛盾。影片前后的表達沒有形成一以貫之的力量去抵達初衷“逆天”的大議題,唯有落腳在親情、友誼,并以此化解矛盾來收尾。
三、哪吒形象嬗變的反思
哪吒形象的演繹有著復雜性與多義性,這三個時期的哪吒文本形成一種跨時代互文,形象上的差異也昭示出政治話語、文化邏輯、產業等多方面的因素糾葛。《鐵扇公主》用帶有迪士尼模仿痕跡的形式,呼喊反抗侵略的號召,成就自己民族的一套獨立語言。20世紀50年代,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提出“走民族風格之路”的口號,探索民族動畫創作之路,萬氏兄弟提供了獨立于好萊塢之外的另一種動畫創作的可能性,中國動畫民族化是時代規律的必然要求。
80年代改革開放后,大批優秀國內動畫人加入了日本、美國的動畫代工廠,造成本土動畫行業的人才流失;追求經濟發展的追逐中,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發展緩慢,美術、動畫教育匱乏,從社會歷史情況上局限了動畫發展。如今《魔童》所張揚的“燃”文化——并不屬于中華文明的精神范疇,而是一種現代人對激情、速度、強烈感的吶喊,那不是中華民族精神原有的、根源性的民族性格。當一個個取材于傳統文化的人物精神流失后,套用“舶來”的敘事方式、精神內涵,源頭故事和形象的符號就成為變異物,民族性淡化、幼齒化、低俗、借鑒痕跡明顯,是中國動畫在今天的缺點,對此我做出以下思考。
第一,尊重民族文化,正確地從民族文化中取材,開掘傳統故事題材是最優路徑。“我們不得不面臨因習以為常而常常忽略的兩個危機:在借取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化的過程中如何避免電影性和當代性的失落。這意味著首先,對神話等文化資源的挪用、改造和創造,需遵循電影敘事的內在法則,造型、人物、意象、儀式、情節、故事等敘事要素的選擇必須遵循電影敘事的特殊性;其次,電影的立意和價值傳達需充分注意神話等傳統文化資源的移位置換功能,投射出精神價值充沛的當代品格或超越性內涵,切實改變該類型淺表化、符號化、技術化的當下創作狀況。歸根結底,如何利用神話、傳說等民間資源對神怪片進行組合創意,是該類型獲得良性創作土壤,成為具有無限潛能的可持續發展的國產優勢類型電影的關鍵。”傳承獨特民族藝術風格,用東方美學的表達方式與當下的動畫電影技術結合,開發傳統藝術,比如水墨畫、皮影等中國獨有的藝術形式,尋找在當今可以相互契合的技術呈現方式。
第二, 理性面對國外動畫的影響,合理借鑒。廣泛學習借鑒是沒有錯的,它是成長的必經過程,只有當我們珍惜寶貴的文化資源,從古代典籍、現當代優秀文學里吸取養分,尋求到自己的特色,吸取精華,辯證地借鑒,將各國動畫優勢容納到中國文化體系內,民族文化的根源才不會斷絕。假借他人的模式和風格,不是長久之計,在階段性的進步和發展局限中,是有效果的,借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本民族的動畫產業和文化趣味是否合適那些已經賣座、已經被接受的模型,是否可以再進一步突破,突破可以到什么程度。
第三,尋找突破口,提升動畫產業原創動力。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在計劃經濟年代,沒有市場壓力,精工細作投入巨資,不計回收的《大鬧天宮》時代絕無僅有。中國當前的動畫市場同時存在著產業分散和文化內涵淺薄的困境。打造優質IP,以“封神宇宙”系列動畫的開發為突破口,鼓舞中國動畫業向傳統民族文化找出路,將會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
第四,深挖民族心理,引導和培養受眾觀影。國漫復興,既是口號,也是我們中國影迷和動畫迷的期望。受眾與創作者都出于同樣對本民族文化和藝術的熱愛為每一部優秀國產動畫喝彩。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心,必須經由我們自己去獨立思考、獨立發展,中式審美與當代思想文化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中國民族動畫與傳統文化交融、與市場接洽、與觀眾對話,希望看到中國動畫真正崛起,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熱情所在。
少數影片的成功爆紅,遠不足以扭轉整個行業的現狀,中國動畫面對著豐沛民族文化資源和有限的動畫發展局面,如何將傳統文化與動畫藝術交融,用中國人自己的影視語言和特色去影響中國觀眾的觀影習慣,是目前需要思考的問題。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