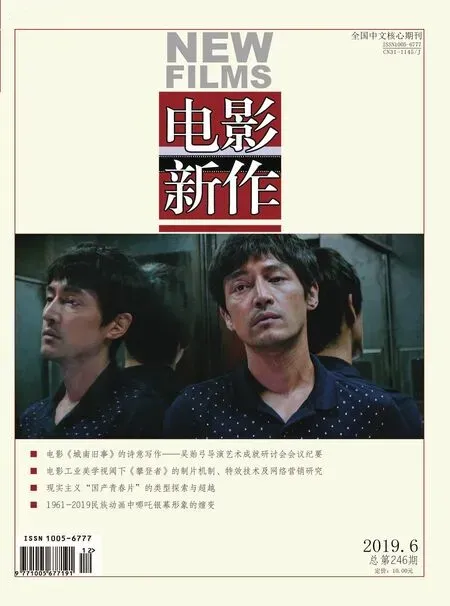謝幕與登場:基于代際價值觀演變視角的青春片風格轉向研究
尹敏捷
作為一個國慶檔和“雙誕”檔之間的傳統電影淡季,2019年的11月卻因為《少年的你》在票房與口碑上的雙向成功而顯得熱鬧異常。這部聚焦于中學校園暴力題材的“另類”青春片,將當下青少年成長之痛生猛地直接呈現在了大眾面前,并在近年來青春片所構建起的柔光回憶景觀上撕開了一個口子,讓我們看到了現實主義青春片的可能路徑。自2016年,《七月與安生》《閃光少女》等影片便開始了現實主義青春片的嘗試。到2019年,《狗十三》(2013年制作完成2018年底上映)《過春天》兩部頗受業界與觀眾肯定的影片,以其完整的視聽語言和敘事方式,為內地現實主義青春片提供了一種記錄式再現青少年成長震蕩歷程的可借鑒美學范式。而沿襲和完善了這一范式的《少年的你》,則是標志著現實主義青春片類型構建的完成和青春片風格轉向的開始。
內地青春片在2019年開始出現的風格轉向的核心推動力,是已經開始掌握社會話語權的“90后”一代取代“80后”成為青春片主體形象轉變的發生。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 在其產生廣泛影響的代際價值觀演變理論中提出了“社會化假設”,指出青少年時期的生存環境和成長經歷決定了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這些基本價值觀在成年以后不易發生大的改變,不同代際因成長環境不同而導致了價值觀念的代際差異,代際更替使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念逐步取代老一代的價值觀念,推動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轉變。作為在改革開放后快速發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兩代人,青少年時期經歷與環境的不同造就了“80后”與“90后”價值觀念的代際差異。因此,當他們開始嘗試去書寫各自的代際歷史時,這種差異便以青春片的不同風格特征被呈現出來。
一、轉向歷程:從懷舊敘述到寫實表達的青春書寫演進
要總結出2011年以來青春片的風格流變就需要將青春題材電影作為一個整體的產生、發展歷程進行梳理,進而解析其作為一種獨特文化現象的審美特征與文化心理。2013年,趙薇導演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不僅成功完成了對“臺式”青春片的本土化改造,更是以7.11億元的票房成績讓業界再次看到了這一題材的巨大市場價值。此后幾年,一大批懷舊主題青春片諸如《同桌的妳》《萬物生長》《匆匆那年》等開始爆發式上映。這些電影大都沿襲著《致青春》的同名IP+明星粉絲電影的制作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具有電影理論意義的“懷舊青春類型片”。在這種類型語法下,“懷舊敘事”成為這些電影能夠構成類型的保障,并作為一種表達結構和類型成規參與建立影片與觀眾之間的約定。
需要注意的是,“懷舊”與“回憶”雖然是兩個“家族相似”的概念,但實際并不相同。懷舊行為雖然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上,但懷舊其實是對于回憶的美好想象,是一種選擇的回憶,是對所選擇記憶的價值加工和審美化處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懷舊的本質是審美。在青春片中,創作者普遍采取了將“回憶”置換成“懷舊”的敘事策略,通過對大量懷舊元素的舞臺式呈現,來完成了對上世紀90年代或21世紀初校園青春歲月的想象性重建。《致青春》中樓管大爺電視機里播放的《新白娘子傳奇》、晚會上大合唱的《紅日》、宿舍樓下排隊打公用電話的場景等時代化符號,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著觀眾影片所期望建立的“年代性”。到了《匆匆那年》里,這種時代符號的拼貼被進一步強化:《當》《信仰》《Don’t Break My Heart》等等兩千年左右的流行音樂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影片中;韓國組合HOT、東方神起、香港歌手謝霆鋒等明星的海報貼滿了溜冰場和主角房間;韓日世界杯、櫻木花道、新概念作文大賽等時代感十足的話題成為人物的談資。這種在影片中對于時代符號的狂歡化穿插展現所指向的,是一種試圖將私人性質的回憶拓展為更加廣泛群體記憶的嘗試。《那些年》的開場處,旁白說道:“每個人的故事里都有一個胖子”拉開了懷舊青春片對“我們共有”青春烏托邦的構建序幕。影片在大陸上映的2012年,也正是“80后”一代全部離開校園走上社會的時期,這些年輕人在體會過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之后迅速扎進了懷舊青春烏托邦之中,并順便貢獻了電影票房。
“80后”是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經濟體制的轉軌,在長大成人后又被直接推到了社會轉型期的撕裂地帶。階級固化、房價攀升等一系列現實問題與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的割裂給置身其中的“80后”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與精神壓力。尤其是2010年前后,第一批“80后”進入而立之年,購房、育兒、父母養老等現實問題的接踵而來讓這種壓力空前巨大。面對重壓的當下和由于上升通道收縮造就的不確定未來,選擇借助懷舊回到青春烏托邦就成為一種集體選擇。2008年由一段名為《80后的回憶錄》的視頻所引發的懷舊文化潮流,實質是這一代人于現實重壓下的精神退行,是這代人轉向過去逃避現實的無意識沖動,是被“猛然拋入”現實,經歷挫折后的一份重返伊甸園/精神故園的渴望。電影由于其作為“造夢機”的特質恰好為“80后”們提供了一個重回青春烏托邦的入口,雙方的“合謀”共同造就了2013至2015年懷舊青春片的全盛時代。然而這種風潮卻并未持續太久,2016年《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泡沫之夏》《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里》等懷舊青春片票房均大大低于預期就已經表明了這一類型的后繼乏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既有大眾對此類影片的審美疲勞,更重要的是作為懷舊主體的“80后”已經褪去了最后的青年色彩,回歸到了社會主流價值觀之中,并將討論青春的權利留給了后來者。在2017年上映的《閃光少女》中,“90后”和青年亞文化已經開始成為敘述中心,青春片的轉型已成為必然趨勢。
當然“90后”在青春片中的銀幕形象也并非是一開始就被定位到了現實主義類型中。《匆匆那年》里已經出現了一個“90后”女孩七七來作為“80后”主角們的回憶觸發者。此后《會痛的十七歲》《遇見你真好》《最好的我們》等影片也做了“90后”主角嵌套懷舊青春片模式的創作嘗試。但是這些作品不僅未能像前作們那樣取得票房奇跡,甚至沒能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任何有熱度的討論。而2018年,一部回歸“80后”主體的懷舊青春片《后來的我們》卻以13.5億元的票房位居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十一位,還把歌手出身的劉若英送上了“票房最高華語女導演”的位置。這種差異性再次證明了懷舊青春片其實并不是一種具備普世意義的審美體驗,而是“80后”群體在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其實,哪怕在懷舊青春片風頭正盛的時期,現實主義青春片也從未銷聲匿跡。2013年上映的的電影《青春派》用專業演員混搭素人學生的方式講述了一段未經美化的“90后”高考故事,稍晚的《狗十三》《黑處有什么》等也都是以現實主義手法再現“90后”甚至“零零后”成長陣痛的影片。只是這些影片雖然大都取得了不錯的口碑并得到了專業電影節的認可,但均未能從懷舊青春片手中搶下市場,因而票房慘淡也沒有獲得足夠的關注。到2017、2018年,“90后”已經全部成年,并開始成為文化消費的主力,他們希望自己不再是作為一個被獵奇觀賞的對象而是文化敘事的主角。2017年10月,真實事件改編的泰國青春電影《天才槍手》在幾乎零宣傳的情況下取得2.71億元的內地票房,即證明了新一代電影觀眾對現實主義青春片的消費需求。而《少年的你》在2019年的成功,正式標志著“90后”由觀看者和被觀看者到講述者的身份轉變,也標志著“90后”青春片銀幕形象的確立。更為重要的是,這部作品在承襲以往現實主義青春片創作風格的基礎上,融合其他類型片元素構建起了一套成熟的可復制類型化特征,啟動了青春片風格轉向的按鈕。
如果說《致青春》開啟了懷舊青春片對過往歲月“向死而生”的書寫方式,其結局必然是青春的消逝,那么《少年的你》完善了對少年“涅槃重生”的影視化表達,其最終指向的是少年的成長以及對成人社會的融入。與懷舊青春片最大的不同在于,2018年以后羽翼漸豐的現實主義青春片沒有急于去構建一代人的群體記憶,而是傾向于更加個人化的青春經歷表達,并建立起了自身迥異于懷舊青春片的類型特征。《狗十三》講述少女面對家長粗暴式教育由反抗到接受的過程;《過春天》聚焦香港“單非”女孩的成長困境;《少年的你》關注校園暴力問題。《狗十三》還將女主角設定為小眾搖滾音樂愛好者,并穿插了大量冷門搖滾歌曲作為背景音樂,更是直接強化了這種個人化表達。在敘事方面,電影也大都放棄了對青春群像的刻畫選擇圍繞著主角遭遇困境(粗暴教育、身份困惑、校園暴力等)——進行抗爭——走向成人世界的成長歷程來展開情節。同時,這些電影創作者走出了懷舊青春片中柔光鏡頭和符號拼貼泛濫的窠臼,轉而以紀錄片式視聽語言和生活化布景來呈現影片的嘗試,也為影片注入了濃烈的現實主義風格。《過春天》中,一個跟隨佩佩在香港大排檔中穿行的長鏡頭不僅把都市片中所遮蔽的香港底層景象納入了影片,還為故事的發生構建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敘事空間。可以看出,現實主義青春片其實是更加接近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的作者電影青春片創作實踐,它們有著對于《長大成人》《青紅》《孔雀》等保留了青春期特有反抗性和邊緣性色彩“灰色青春”電影的風格延續。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實主義青春片也更加符合好萊塢青春片的類型語法:青春電影基于青年——成人這對穩定關系,來自于成人世界的主導價值觀和青年叛逆亞文化之間的緊張感。劉易斯認為青春片的文化功能是對于主流價值觀的再確認,并具體地通過青年的異化和再社會化來完成。反觀懷舊青春片,其類型化構建動力來自于臺灣言情偶像劇、大陸“新都市電影”“80后”懷舊潮流三者的融合統一。兩個本就致力于“造夢”的影視類型在懷舊風潮的裹挾下,其實是把都市言情劇的人物與情節直接移植到了校園中。同樣是穿校服的造型,《狗十三》里李玩的青春痘和鋼絲牙套讓她看起來就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中學女生,但《匆匆那年》里林嘉茉的栗色挑染頭發和大地色眼影仿佛是在告訴觀眾這就是一場都市白領的校園cosplay。也正是這種在類型承襲上的差異,造成了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倒掛現象:不論是影片本身還是其宣發營銷都竭力強調“我們共同記憶”的懷舊青春片常常被指責為失真,而更加個人化的現實主義青春片卻因為對少年在向成人過渡時期心態細節的還原再現引發了廣泛共鳴。
“80后”在人生特殊時期的精神退行把青春片推向了主流視野,而“90后”由邊緣到主體的銀幕定位,則讓現實主義青春片開始復蘇回溫。兩種類型源流各異,青春片從懷舊敘述到寫實表達的流變,所指向的是“80后”“90后”兩代人不同的青春書寫方式。
二、轉向動力:青春解讀方式的代際差異
懷舊青春片作為“80后”一代人的“青春烏托邦”,是其在面臨當下困境時一個聊以慰藉的精神家園。這種與生俱來的功能屬性,就決定了懷舊青春片不可能是對校園青春歲月的現實再現。畢竟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中學時代是一段被書山題海和升學壓力填滿的高壓歲月,而大學又是匆匆而過的平庸時光。《那些年》上映時,即有網友表示自己的青春應該是“那些年我們這些沒人追的女孩”。因此,懷舊青春片所指向的是一種站在當下對過去的美化性再構建。同時,“80后”作為一個被以出生年份命名的群體,其內部的差異性卻是十分巨大的,致力于制造“我們共同回憶”的懷舊青春片也必然選擇盡可能地去展示一代人成長的共性。基于這兩個原因,每個人年少時都普遍存在又大都美好的懵懂情愫被選擇成為青春的等價物,并被進一步放大和演繹成為一場又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匆匆那年》里陳尋為了和方茴上同一所大學而放棄了一道17分的高考大題;《同桌的妳》中周小梔翻墻砸窗帶因非典被隔離的林一逃跑;《左耳》中蔣姣為了挽回許戈以跳樓相威脅。然而,懷舊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目的并非僅僅是美化構建一段過往歲月,而是把過去當做向未來挺近的材料。?懷舊青春片所指向的其實是以盛大青春愛情的逝去為自己當下的平庸提供一個借口:既然所有的美好都已經隨著青春的終結而離去,那么我在冰冷當下的碌碌無為也就情有可原。而為了完成由青春回憶到當下現實的過渡,愛情往往被以一方出國、第三者、車禍等等偶像劇式的橋段被終結。這種經年后回望意外逝去熱血愛情的敘事模式,構成了懷舊青春片中一種“舞臺劇”式的成長儀式,并遮蔽了現實中成長的殘酷性,是只有情節沒有故事的一代人在蒼白枯燥的教育體制下成長經歷的粉紅色涂鴉。?
美國社會學家艾克里森將12-20歲的青春期定義為“兩性期”,這一時期是個人脫離童年身份并在成人社會中重新尋找個人定位的階段。在懷舊青春片中這種身份的再次找尋被簡單拆解成了對愛情的初體驗,而稍晚出現的現實主義青春片則補全了銀幕上所欠缺的當代青年成長歷程。《狗十三》中李玩問同樣作為中學生的堂姐:“你愛他(堂姐男友)嗎?”堂姐回答:“愛太沉重了,頂多算喜歡。我總得喜歡個誰吧,不然多無聊。”這段對話,是“90后”學生時代對感情的態度,也是“舞臺劇”化愛情元素在現實主義青春片中退場的寫照。片中的女主角李玩也并沒有對愛情有所期待,她所在意的是能否選擇自己喜愛的物理小組以及如何找到走失的寵物狗。而且,《過春天》中女主角佩佩所苦惱的是如何攢錢與閨蜜去日本旅行;《少年的你》中陳念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學習考上北京的大學。這些影片中的“90后”主角們顯然更加關注自己的生活和未來,愛情退化成為互相在對方身體上綁手機時欲言又止的曖昧或者是放學路上的一段無聲守護。與愛情退場相對的是身份認同再找尋在青春片中的回歸。《狗十三》中李玩在長輩的暴力教育下被迫適應了成人世界的語法獲得了新身份;《嘉年華》中孟小文面對家庭關愛的長期缺失,只能在“干爹”的迷惑中尋找認同;《少年的你》中陳念渴望考上大學獲得新身份以擺脫糟糕的當下。這種身份找尋在《過春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佩佩作為一名住在深圳卻在香港念書的深港跨區域學童本身就有著身份歸屬上的撕裂,加之特殊家庭中雙親的“愛無力”和“兩性期”自我意識的逐漸覺醒,讓佩佩寄希望于遠走日本來逃離這種生活。在一次意外中,急于籌措旅費的佩佩進入了偷帶香港蘋果手機到內地的“走水”行當中,而在由各種邊緣人群組成的“水客”群體中,佩佩卻感受到了另類的情親、友情甚至愛情,找到了一種錯位的身份認同。影片結尾處,因“走水”被抓而取保候審的佩佩將小鯊魚放歸了大海,所隱喻的是她放棄了借由他者賦予自己身份的幻想和將要向著更大世界去成長的蛻變。除了對成長本身的敘述,現實主義青春片還改變了懷舊青春片中對社會背景的虛化處理,將地域差異、階級與貧富分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等現實問題納入了影像中,這種背景的復雜性,讓現實主義青春片有了一種“紀錄片”式的真實感。隨著現實主義青春片開始走入主流視野,此前被轟轟烈烈青春愛情所遮蔽的“生長痛”開始在大銀幕上被正面呈現,“舞臺劇”式的假想成人禮亦開始讓位于“紀錄片”式的成長敘述。
在當前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代際傳承的連續性和平緩性被現代社會價值觀傳承的急遽性和斷裂性所取代,作為文化自覺的共同體意識開始覺醒,各代之間的價值觀清晰地凸現出來,并互成相對之勢,社會價值觀開始發生代際分化就不可避免。懷舊青春片與現實主義青春片對成長主題的不同表述,亦是“80后”“90后”代際價值觀差異的具體表現。“80后”作為經歷了從整體價值觀向整體價值觀與個體價值觀融合變化的一代人,其在計劃經濟體制余暉下度過的童年乃至少年時期決定了他們相較于“90后”稍顯貧乏且更具統一性的成長歷程。同時,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同學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80后”成長過程中兄弟姐妹的角色功能。因此,有同齡人陪伴且目標價值明確的校園生活構建起了“80后”的集體記憶,也讓校園成為“80后”在追求個人價值受挫后渴望退回尋求群體認同感的地方。與“80后”在變革中成長不同,“90后”的成長過程中個體價值觀念的復蘇已經完成并和整體價值觀趨向融合,而分眾化互聯網的興起更是放大了其成長歷程中的“個人性”,“90后”實際上是集體記憶缺失的一代人。隨著21世紀初互聯網在大陸的普及,處于價值觀塑造期的“90后”很容易就可以在互聯網上建構起不同的“小團體”,這些群體的建構和維系都非常簡單,公共事件和議題、相似的經歷、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甚至流行語和符號都可以建構和維系一個“小團體”。如果說同學扮演了“80后”成長陪伴者的角色,“90后”則將這一角色轉換成了互聯網“小團體”。然而,互聯網“小團體”的興盛拉遠了同學之間在現實交往中的距離并因為“小團體”自身的松散性和不確定性,其實是將“90后”推上了獨自長大之路。上海社科院在2009年針對“90后”中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67.3%的青少年不同程度地認同“我覺得有些同學很討厭”的說法,47.5%表示“和不熟悉的同學交往時,我感覺不自然”。也就是說,“80后”逃避當下壓力的校園烏托邦對于集體記憶缺失的“90后”來說其實并不存在。
同時,90年代以后我國迎來了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物質條件的改善和稍晚普及的互聯網,讓“90后”具備了更強的國家認同和對社會樣態的更早認知。《南都周刊》一次對“90后”的采訪中,最讓記者意外的不是“叛逆”和“非主流”,而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清晰認知和對自身未來的規劃十分明確。這種互聯網信息環境帶來的認知“早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90后”初入職場的心理震蕩,加之集體記憶的缺失,使得其面對生活的壓力沒有選擇通過“懷舊”尋求安慰而是轉入了低欲望的“佛系”生活。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是,“90后”作為第一代伴隨著互聯網長大的人群,他們的成長被互聯網事無巨細地記錄了下來。在“前互聯網時代”個人的經歷大部分都遺失了,只有少部分進入了記憶,所以人類需要通過懷舊去想象性構建自己的過去。而“90后”留在互聯網中的個人歷史卻是可以被隨時翻閱和溫習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互聯網拉近了過去和當下的距離,也扼殺了“90后”懷舊的空間。畢竟,一個被建構和美化的再逼真生動的過去,也會被一張人人網上十年前的舊照擊得粉碎。
“80后”橫跨兩種經濟體制的成長經歷,既造成了這一群體的割裂性,也為其提供了一個可以逃避現實的精神烏托邦,懷舊青春片則恰好為其提供了重返精神烏托邦的路徑。“90后”作為第一代“網生代”的身份卻帶來了其集體記憶的缺失和懷舊空間的消亡。因此,當“90后”開始直面生活壓力,他們選擇通過對當下現實的解構和逃避來“佛系”生活,而不是以懷舊向過去尋求安慰。現實主義青春片與懷舊青春片的功能區隔在于,它不是精神安慰劑,而是“90后”開始掌握話語權后為自身的證明性發聲。這種發聲所指向的,是生活在豐饒年代的“90后”渴望讓自己的真實成長經歷轉化為“個人史詩”,并扭轉大眾和媒介對自己長期刻板印象的嘗試。“舞臺劇”式的假想成人禮到“紀錄片”式的成長敘述讓位的背后,是兩代人回望青春的不同態度,也是兩種青春片的交替。可以預見的是,隨著“90后”文化消費力量的進一步崛起,這種轉變還將進一步加速。
三、轉向背景:青年亞文化與作為文化商品的青春片
除了對成長歷程本身的講述,青年亞文化作為成長過程中的一種獨特心理現象也是青春電影中的重要敘述元素。青年亞文化最早由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具體是指青年群體在主流文化之外形成的群體性社會體驗、心理結構。這種包含了犯罪、暴力等與主流價值觀相悖元素以及小眾藝術形式的文化類型,其本質是青少年在童年與成人之間一個暫時的文化棲息地。在內地現實主義青春片中青少年成長的復雜性和身份的邊緣性得以在銀幕上再現,青年亞文化構成了成長的一種表現形式:《嘉年華》中少女對性的混沌與迷茫;《過春天》所涉及的青少年犯罪;《少年的你》關注的校園暴力都是角色成長的重要推動力。但在懷舊青春片中,大眾流行文化完全遮蔽了青年亞文化,在這種語境中所有角色都被抹去特征植入了大眾文化和歷史事件中,其所指向的是對“80后”共同記憶的構建和群體歷史的再造。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既有在多元價值取向和互聯網“小團體”環境中成長起來的“90后”對青年亞文化的天然適應性。但更重要的是,懷舊青春片與現實主義青春片并不是“80后”與“90后”對個人成長經歷的回溯與表達,而是電影公司在與這兩個文化消費需求旺盛群體經歷磨合后為其提供的定制文化消費品。作為銀幕主體形象的“80后”“90后”不是敘述者,只是被按照消費偏好構建起的形象。所以“80后”青年亞文化是否存在、“80后”的真實成長歷程如何并不重要,懷舊青春片本質上就是一種用來逃避壓力的商品,它被生產出來的目的就是給觀影者提供一個精神烏托邦。同時,“80后”不同于青春同共和國早期歷史密切相關的父輩,亦不同于更加注重個人歷史的“網生代”后輩,他們的歷史存在感確實顯得薄弱,因此歷史大事和流行文化的符號化植入在懷舊青春片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電影創作者試圖在這些歷史坐標中構建起一代人的共同記憶,以此引發目標受眾更多的情感共鳴。可以說,懷舊青春片的一切創作都是圍繞著其作為文化商品的商業屬性而展開。因此,反映“80后”真實青春歷程的電影由于當前市場的缺乏,很難出現于主流視野之中。那么,“80后”的真實青春故事何時會在大銀幕現身呢?也許,當“80后”一代人不再僅僅是文化產品消費者,而是具有決定權的文化產品生產者時,屬于“80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孔雀》《芳華》才會誕生。2017年,“80后”作家韓寒導演的《乘風破浪》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這種意味。
相較于懷舊青春片對同一范式的不斷復制,現實主義青春片卻在青年亞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不斷嘗試跨類型創作的可能。《閃光少女》中歌舞片、喜劇片甚至二次元動漫的類型元素被融入影片;《過春天》中佩佩三次偷帶手機過關的場景中也有著明顯對犯罪類型片元素的借用。這種類型融合在《少年的你》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犯罪懸疑片與驚悚片中的懸念與驚險被加入了陳念的被欺凌與反欺凌之中,使得故事格外扣人心弦。影片以胡小蝶的跳樓開場,即以懸疑片典型的“命案發生”開場奠定了全篇的緊張感。此后一次次即將發卻又不知道何時會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被以驚悚片元素反復呈現,將緊張感不斷疊加。在小北希望替陳念頂罪的段落中更是巧妙采用了“最后一分鐘營救”的經典手法,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最高點。電影類型本身就是好萊塢商業電影發展的產物,熟練操縱類型愉悅內容更是實現商業電影吸引力的重要途徑。內地現實主義青春片的跨類型創作,是其作為商業片希望盡可能多地調動多種類型愉悅內容,進而帶來更高票房收益的具體表現。懷舊青春片與現實主義青春片作為面向“80后”與“90后”兩個不同代際群體文化消費品的屬性決定了它們各自的風格呈現。
這種商業片屬性,也造成了聚焦“90后”的現實主義青春片與第五代、第六代導演自我表達的藝術青春片雖然具有風格上的傳承,但其本質并不相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隨著《少年的你》成為繼《陽光燦爛的日子》后內地第二個票房口碑雙收的青春片,青春片由懷舊風向現實主義轉變已不可避免。未來幾年,一大批具有跨類型色彩的現實主義青春片的上映已是可以預見的趨勢。至于這些影片是能在《過春天》《少年的你》甚至《天才槍手》的基礎上開拓出新的藝術價值,還是像懷舊青春片一樣淪為對類似元素的簡單批量復制,我們不妨等這些電影上映后再做定論。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