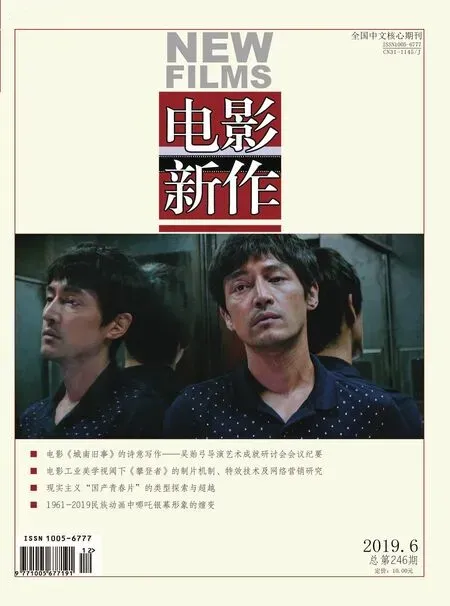牧野流光:蒙古族電影70載嬗變考索
丁 彥 蘇米爾
蒙古族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文化藝術歷史源遠流長。在影像時代,蒙古族電影成為追溯歷史、反映現實、照亮未來的重要途徑,是我國少數民族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毛澤東同志親自更名的《內蒙人民的勝利》(1950,原名《草原春光》)至今,蒙古族電影已走過近70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對這一歷史進行回溯,并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與蒙古國、俄羅斯等北線國家增強電影歷史交流,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礎上,逐漸走向“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俯瞰蒙古族電影歷史,既是蒙古族電影的審美史,也是內蒙古人民的心靈史。
一、初創期的“他者”觀照(1950-1978)
在1950-1978年的初創時期,蒙古族電影在“族群性”與“融合性”中傾向后者,是一種“他者”觀照下的民族影像抒寫。這一階段涵蓋了“十七年”電影階段。“十七年”電影時期紅色電影大量涌現,這是政治環境與觀眾需求的雙重因素使然。這些紅色電影通過對歷史創傷記憶的追溯,襯托黨和人民在偉大斗爭中締造的豐功偉績,是一種政宣需求。與此同時,社會大眾從黑暗走向光明的親身體驗也激發了其強烈的表達欲望,這些紅色電影正是抒發“新舊社會兩重天”之感慨與社會主義新生活之感恩的情感“場域”。
作為“十七年”電影時期的蒙古族電影,自然從自身角度詮釋了這一階段的作品形態。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指出:“電影事業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普遍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這一事業,以利于在全國范圍內有力地進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宣傳工作。”《內蒙人民的勝利》作為毛澤東同志親自更名的作品,最初在展現蒙古族上層矛盾時與黨的民族政策有所違和而被停映,后來經過周恩來同志組織電影界專家探討修改之后,才重新上映。
這一時期蒙古族電影的人物塑造與情節設計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個體不幸命運與民族啟蒙覺醒的重合,影片中往往有一個有待覺醒的民族代表形象,還有一個政治引領的啟蒙者形象。《內蒙人民的勝利》中的頓得布和《鄂爾多斯風暴》(1962)中的烏力吉開篇都是王爺的馬倌,遭受壓迫,命運坎坷。頓得布起初由于國民黨特務挑唆與愛情上的誤會,對漢族與共產黨持有偏見,后來隨著情節發展出現反轉,遇到領路人蘇和,頓得布覺醒,最終加入中共的革命隊伍。烏力吉親人遭受迫害,他前往北平告狀結識共產黨人劉洪太,受到啟迪而覺醒,最后加入中共的革命隊伍。在一種“他者觀照”的創作中,由于對民族文化與相關問題欠缺深入考察,人物塑造容易陷入標簽化、臉譜化泥淖,人物關系容易陷入簡單化、表面化窠臼。恰如《內蒙人民的勝利》編劇王震所言:“我們只看到了王公對人民的壓迫和少數民族中的敗類通敵叛賣的事實,卻忽略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者面前,這樣的王公雖然與其本民族的人民大眾之間有著矛盾,但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也有矛盾。因此,在一定條件下,人民就有把這些上層分子爭取過來或使之中立的可能。”
一些蒙古族電影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指導下創作,竟仍有可圈可點之處,實屬難能可貴。比如,《沙漠的春天》(1975)雖然也大量表現了“階級斗爭”,但影片中牧民娜仁花帶領群眾植樹造林、緩解沙化的生態意識和家園意識,在當時是一種難得的生態文明先進意識。《戰地黃花》(1977)展現了內蒙古草原文藝輕騎兵“烏蘭牧騎”的風采,閃耀著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蒙古族能歌善舞,將歌舞元素融入銀幕敘事,不僅豐富了電影的藝術形式,凸顯了蒙古族的歌舞優勢,也以輕歌曼舞柔化了“政治圖解”的剛硬刻板。
二、復蘇期的題材突破(1979-1985)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中國社會局面的同時,歷經寒冬的文藝創作也迎來了復蘇的春天。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貫徹和改革開放序幕的拉開,中國電影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相應的,蒙古族電影也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下開啟了新的征程。這一時期的蒙古族電影弱化了對意識形態的直白表述,而是通過對人性深處的探訪委婉地揭示主旨,更接近藝術情感特質。這一時期有三部重要的作品,對題材的突破具有探路者意義。
第一部是《玉碎宮傾》(1981),這是一部蒙古族愛情片,仿照了“羅密歐與朱麗葉”模式,講述了主人公塔娜公主與善于騎射、英俊瀟灑的洪古爾相愛,但是遭到塔娜父親甘珠爾王的百般阻撓,塔娜萬般抗爭,最終與洪古爾雙雙殉情。深長思之,這段愛情悲劇源自不可調和的封建禮教與現代文明的沖突,將國家意識形態隱匿于草原兒女的悲情戀歌之中。當然,該片也存在不足之處。由于主創人員悉數非蒙古族,在“他者觀照”視閾下,人物塑造、演員氣質與舞美布景等方面比較欠缺民族性與地域性,使故事不免放之四海而皆準。
第二部是《重歸錫尼河》(1982),影片講述了蒙古族青年哈日夫隨父親到城市生活,經歷了種種不幸,落魄地回到草原后,又遭逢不順。經過一番生活的磨煉,哈日夫終于回歸往日溫馨的牧民生活。在這部作品中,首先,“城市”作為一個被扭曲的意象,成為與游牧文明對峙的工業文明化身。在這場文明較量中,來自草原的牧民之子傷痕累累。其次,繼母實際上是“城市”生活的“代言人”,其無理苛責與蓄意陷害帶給蒙古族青年難以彌補的心靈傷痛。這似乎隱喻了牧民對城市的一種扭曲的想象。最后,作品直面道德善惡與世態炎涼,透過文明沖突深入到人性與心靈深處,也贊頌了人間至情至善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洗禮與升華。
第三部是《獵場札記》(1985),作為田壯壯導演的一部代表作,不僅于蒙古族電影譜系而且于80年代的中國影壇都具有重要意義。盡管這也是一部“他者觀照”的作品,但影片以類似紀錄片的紀實美學手法較為真實地再現了牧民與草原的血脈相連。同時,電影在視聽語言上的創新、敘事情節的簡略、紀實美學的承襲都對電影本體的探索是一種貢獻。應該說,這部介于紀錄片與故事片之間的作品由于弱化情節而沒有充分滿足當時觀眾的定向期待,然而在弱化情節的同時強化了生活的記錄,從而較為充分地詮釋了蒙古族的粗狂與豪情,將游牧民族的陽剛之美與灑脫飄逸展現得較為淋漓盡致。
總體而言,蒙古族電影復蘇期的三部代表作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意義。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還有回溯蒙古族人民革命斗爭而又融政宣于審美的《阿麗瑪》(1981)、《母親湖》(1982)、《騎士的榮譽》(1984),以及規避宏大敘事而聚焦日常生活的《綠野星辰》(1983)等。這些作品在“乍暖還寒”的復蘇期既有“政宣品”創作模式的自然沿襲,也有對“藝術品”本體價值的主動探索,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蒙古族電影全方位的大發展提供了范本。
三、發展期的“自我”詮釋(1986-2000)
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文化思潮八面來風,中國電影整體上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確立,產業思維推動了商業片的興起。相較于初創期的“政宣品”,經過復蘇期的探索,發展期的蒙古族電影彰顯了電影的本體屬性“藝術品”特質,并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電影“版圖”。這一時期在意識形態上具有至少兩個方面突破。
一方面,意識形態的突破表現為題材突破,較為典型的是對歷史時空再現的突破。1985年抒寫蒙古族歷史偉人成吉思汗豐功偉績的同名電影《成吉思汗》問世,電影將歷史推至相較革命歷史更為前端的歷史時空。無獨有偶,在屏壇上,我國首部帝王題材電視劇《努爾哈赤》次年問世。該劇中的努爾哈赤形象從“神人模式”“偉人模式”中解放出來,并未隱去其政治生涯中的失誤,也未借用“腳踏七星,帝王之相”等傳說,而是遵循唯物史觀,審美地再現了一個從普通女真貴族到反抗明末暴政的革命者,再到開國帝王的成長史與心靈史。這說明創作者已經獲得了相對的創作自由,可以開掘之前被視為“階級敵人”的封建帝王題材。“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成吉思汗》與《努爾哈赤》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成為推動中國“銀屏”歷史之雙輪,《成吉思汗》在蒙古族電影版圖和中國影壇中功不可沒。由蒙古族導演塞夫與麥麗絲夫婦執導的蒙古族歷史題材影片《東歸英雄傳》是繼《成吉思汗》之后的又一力作。影片審美地再現了公元1771年由中國遷徙至伏爾加河下游近200年的蒙古土爾扈特部落遭到沙皇種族滅絕政策的戕害,在部落首領渥巴錫汗率領下開啟了東歸大遷徙,歷盡艱辛回到中國。應該說,不論是表達國家一統思想的《成吉思汗》,還是歌頌回歸故國事跡的《東歸英雄傳》,都以春風化雨的方式宣傳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的突破表現為對單一“他者觀照”的突破,強調“他者”與“自我”的協同合作。蒙古族導演哈斯朝魯在談及“他者觀照”與“自我詮釋”孰優孰劣時回答:“有些蒙古族題材的電影我看了就覺得不太切實際,很多內容在我們蒙古族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有的人想當然地以為只要穿上蒙古袍、住上蒙古包,就是蒙古族的電影了,這是不對的……是否只有本民族的電影人才能拍好本民族題材的電影?我覺得這不是絕對的,但是編劇和導演非常重要。”哈斯朝魯導演的經驗之談啟示我們,少數民族電影的“族群性”是其存在的價值所在。對這種“族群性”的彰顯需要主創者把蒙古族文化放在56個民族的文化碰撞交融中去體悟,方能發現蒙古族的個性與民族間的共性,這一點應處在創作的第一位。
四、成熟期的多元呈現(2001至今)
21世紀,隨著中國加入WTO世貿組織和全球化進程加速,國際文化貿易日益頻繁。在文藝領域,隨著2002年國家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劃分,以及2009年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頒布,電影迎來了全面商業化時代。隨著跨文化交流日漸頻繁和網絡時代受眾力量的逐漸強化,國家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更加開放和包容。在新時期,蒙古族電影的外部要素的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經濟環境相對薄弱,整體而言文化環境的影響顯著。文化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生態家園焦慮、精神家園隱憂與普世價值共鳴三個方面。
一是生態家園焦慮。在主流意識形態層面,國家在經濟建設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也反思了過去粗放型生產,開始轉向集約型生產。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美麗中國”,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蒙古族電影自新世紀以來就十分注重對草原生態文明的憂慮。在《天上草原》(2002)中,寶日瑪帶著虎子歸還鴻雁蛋,對著天空向鴻雁喊話道歉;在《索密婭的抉擇》(2003)中,荒蕪的草原成為老牧人心中的遺憾;在《圣地額濟納》(2010)中,當紅柳林被砍伐時,不僅牧人潸然淚下,連駱駝也發出哀嚎。這些電影都閃耀著蒙古族與生俱來崇尚自然、愛護家園、尊重生命的生態觀。
二是精神家園隱憂。隨著國際文化交流在網絡時代不斷加速,不同文明對中華文明的沖擊也日益嚴重。不必諱言,新世紀以來我國文化市場上“哈韓風”“哈日風”“歐美風”輪番登場,所謂“中國風”大都只是拼貼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較為表層化而且邊緣化。歷史悠久的蒙古族文化和對應的草原文明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在各類中外文化駁雜碰撞的今天,蒙古族通過銀幕也抒發了文化隱憂。《長調》中的琪琪格為了發揚蒙古長調來到城市,但是最終失聲,失落而歸,最后在草原重新找回久違的天籟之聲。長調作為蒙古族聲樂藝術,2005年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長調》作為一種銀幕象征,代表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面對工業文明時的焦慮,這宛若是對于蒙古族精神家園日漸式微的一曲挽歌。
三是普世價值共鳴。從國內來講,社會學家費孝通對于我國多民族格局提出“多元一體論”,并以十六字詮釋之,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對于民族文化危機和精神家園焦慮具有啟迪價值。從國際來講,網絡科技的日新月異與網絡文化的高度普及已經使過去山海永隔、不相往來的國度變成無遠弗屆、雞犬相聞的村落,麥克盧漢“媒介是人體延伸”與“地球村”的命題已經兌現。因此,在國內外大勢之下,蒙古族文化在注重保護其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應當以更大的格局、更廣的視野在人類普世價值坐標系中定位自身的民族文化坐標。比如,《狼圖騰》在對蒙古族人圖騰崇拜與精神世界的刻畫上,由于對“他者”文化的誤讀,造成了蒙古族觀眾對“狼圖騰”說法的質疑。然而,該片正是試圖探尋文化“誤讀”中人類共有的生命意識與生命母題。影片通過陳陣的同源敘事,變換了姜戎同名小說中“狼”的敘事視角,正是沖破“自我”和“他者”壁壘的一次嘗試。陳陣與牧民之間于人類生命母題面前所形成的的精神共鳴正是其他民族走來與我們走入異質文化的關鍵一步,也是真正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重要維度。
結語
立足今天,回望昨天,是為了照亮明天。巡禮了蒙古族電影近70載的征程,也就從一個側面見證了我國文藝政策和審美變遷的歷程。對于內蒙古文藝創作,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新時代,希望你們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大力弘揚烏蘭牧騎的優良傳統,扎根生活沃土,服務牧民群眾,推動文藝創新,努力創作更多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優秀作品,永遠做草原上的‘紅色文藝輕騎兵’。”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內蒙古期間接見烏蘭牧騎隊員時指出:“烏蘭牧騎是內蒙古這個地方總結出來的經驗,很接地氣,老百姓喜聞樂見,傳承了優秀傳統文化。”蒙古族電影就要在“烏蘭牧騎精神”指引下,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繼往開來,不斷創新,在與我國其他民族和“一帶一路”成員國的電影文化互鑒中形成“美美與共”“大同和音”,創作出更多立得住、傳得開、留得下的精品,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深情獻禮。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