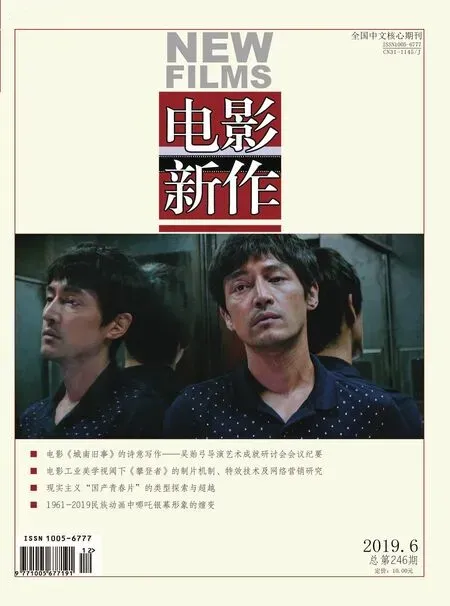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水形物語》:隱喻背后的現實投射
蘭繼洲
吉爾莫·德爾·托羅執導的《水形物語》是一部融合童話、情感與跌宕劇情的奇幻作品。該片一經問世,便獲獎無數,更在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一舉斬獲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重量級獎項,更因其瑰麗的想象與溫暖的故事內核,收獲無數觀眾的喜愛和業界好評。在溫馨感人之余,電影更將現實人物、現實背景做了微妙處理,巧妙地將現實元素通過隱喻投射到奇幻故事當中,對觀眾產生一定的啟發性和對現實的反思。其中現實元素在該片中的變形與投射集中體現在背景設定、心理元素,以及人物形象三個方面。本文從《水形物語》出發,通過探究現實元素在奇幻電影中的展現方式,給此類電影作品帶來新的創作與解讀空間,還原其背后的現實意義。
一、背景設定的現實投射
電影借由主人公的鄰居查爾斯的旁白展開,在這種略帶疏離感的敘事語境下,導演將整個背景安排在一個發生年代、地理都不可考的架空時空當中,凸顯出電影的“奇幻”屬性。而實際上,電影的時空背景卻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找到現實原型。而其中最明顯的現實隱喻是美蘇冷戰背景和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平權運動。
冷戰的現實背景是顯而易見的:電影設定為1963年的冷戰時期,人魚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實驗品出現在女主人公所服務的秘密基地內。現實歷史中,這段時期正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峙的白熱化狀態。彼時,這兩個霸權主義大國不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展開激烈競爭,也將冷戰的硝煙延伸到科研領域,甚至不惜展開太空競賽。而電影中人魚和秘密基地的出現,就成了兩國在科研領域角力的一個縮影。電影中一個重要的支線就是秘密基地的掌權人理查德與蘇聯間諜霍夫斯泰勒博士對人魚的爭奪。導演在處理這條線索時,并沒有將其處理成一出老套的諜戰劇,而是將故事的核心放在理查德與霍夫斯泰勒兩人對待人魚的態度上。理查德對非我族類的人魚充滿厭惡,雖然受命對其研究,卻毫無人性與科學道德可言;而霍夫斯泰勒雖然作為一個科學家,卻對人魚充滿同情,甚至不惜違抗上級予以救助。這條線索最大的懸念并非蘇聯與美國在這次較量中誰勝誰負,而是霍夫斯泰勒這個角色的人性覺醒。
對了解冷戰歷史的觀眾來說,故事背景中對冷戰的現實隱喻是不言而喻的,而這種隱喻投射在故事文本中,卻可以看到導演態度的微妙變化:一方面是對戰爭的無情嘲諷,另一方面又淡化戰爭本身的政治因素,轉而投向對故事中邊緣人物的人文關懷:影片的故事呈現中,不論美國還是蘇聯,兩者的權力斗爭在純粹的人性本善面前都達到了可笑荒誕甚至不可理喻的地步。電影中就這一時期的設定有非常多具象化的設計,在空間和情境中帶出了濃厚的時代感,強烈的現實背景借助于敘事的層層推進,通過對人性善的召喚無情諷刺和嘲笑了戰爭的荒誕。
對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國民眾來說,除了美蘇冷戰這的歷史事件外,在美國本土正發生著另一場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就是平權運動。對于這一現實隱喻的運用比冷戰的隱喻更為巧妙:因為這一運動比起冷戰,更具有文化意義。而在影片中的投射,從直觀的信息來看則更加隱蔽,主要體現在一些一閃而過的細節上;但從影片的終極訴求上,這一現實隱喻卻與影片的主旨高度契合:即對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物的同情與關懷。
從影片文本上來說,雖然電影對時代背景做了模糊化處理,卻在一些細節中讓觀眾得窺一斑:老畫家查爾斯某日與艾麗莎在客廳看電視,要求艾麗莎換臺時,電視里一閃而過的新聞正是發生在1963年的伯明翰事件,當時黑人要求平權的示威活動被警方強制驅散。
而現實中美國的平權運動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內容也不僅僅是黑人運動,還包括其他少數族裔、女性權利、不同性取向者不受歧視、不同文化的平等表達等等,而這些都在電影當中透過不同角色有所體現。而種族問題與女性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這個現實性的癥結在影片中則集中體現在影片的反派人物身上。
不論是黑人還是女性,他們在爭取平權的過程中,都有一個明確的訴諸對象,即被美國人戲稱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這些人掌握著美國的絕對政治話語權,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并且偏向保守和大男子主義,對其他種族態度并不友好。而影片中典型的WASP就是反派理查德,一個典型的男性美國白人。主人公艾麗莎與理查德的互動,以及與電影中其他女性角色的互動,集中反映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在社會活動中處于弱勢和被男性支配的處境。影片中秘密基地由理查德一手掌管,而眾多的女性則負責處理瑣碎事物和善后工作,在眾多女性當中,理查德儼然一副“大家長”做派,一邊享受女性的服務和服從,一方面貶低女性的價值,甚至影片中有相當篇幅展示理查德對女性的歧視態度:例如公然當著女性清潔員的面如廁,視女性如無物。而理查德這個典型的守舊派白人男性與女性的集中矛盾則體現在與艾麗莎的關系上,影片在交代艾麗莎日常工作時,有相當的篇幅展示了理查德對艾麗莎這個殘疾女性的欺凌與侵犯。而導演所表達的這種侵犯并非出于男性本能的沖動,而是男性權力的展示,這一點從選角上可以看出:因為艾麗莎本人并不具備對異性的吸引力,因此理查德的欺凌本質上更接近一種男子權力欲的發泄。導演在演員的選擇上,選擇了煙火氣十足的沙麗·霍金斯,避開了傳統通話中王子與公主的常見套路,甚至避開了灰姑娘的美麗賢淑形象。可見,在主人公與反派的人物對立中,導演有意識將性別權力與女性主義投射其中,而這也是美國當時時代背景中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
在通過艾麗莎展示女性平權的現實背景之外,導演還通過次要角色,將種族平權的社會背景帶入到故事當中。對種族問題的探討,比較明顯的是老畫家查爾斯。鰥居多年的畫家查爾斯原本與世無爭,甚至對社會運動避之不及,明哲保身,在電影當中,他甚至要求艾麗莎給電視換臺,不愿看到伯明翰事件的新聞。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性格恬淡的人,在看到自己暗戀的服務員趕走一對黑人夫婦時,毅然與之翻臉。查爾斯的轉變并非因為自己的愛得不到回報,而是服務員的表現徹底擊潰了查爾斯心中幻想的純真少年的形象,讓他看到自己苦苦愛戀的不過是一個狹隘的白人男性,而這個形象本質上與本片反派理查德別無二致。而在1960年代,轟轟烈烈的種族平權運動所控訴的,正是理查德這樣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這場運動中,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以非裔美國人為代表的少數族群,也影響到美國各個階層和民族,其中就包括查爾斯這樣的白人。
發生在上世紀的平權運動對美國近代歷史和思想影響深遠,也是當代美國人的一個共同記憶。《水形物語》中對現實社會運動的投射,也使得該片被冠以“政治正確”的稱號。雖然“政治正確”不過是一句不功不過的評價,卻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本片在觀眾心目中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二、心理元素的具象投射
除了前面討論的具體歷史背景在電影中的投射之外,電影還使用了大量的細節來觸及更深層次的人物心理經驗。在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導下,許多文藝創作也有意識地在電影中使用大量的隱喻來進行創作。比較知名的代表作有《香草的天空》《穆赫蘭道》等以夢境為主題的電影,這一類作品的顯著特征是,不再以故事內容對人物心理影響來探究人物的精神狀態,而是從人物自身的精神狀態和心理視角展開對故事本源的探索。創作者將人物的心理投射到故事當中,使得故事產生一種具有人物主觀色彩和精神特質的另類表達,而觀眾則通過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故事中的線索產生觀影之外另一重還原故事本相的娛樂訴求。這種通過主人公心理投射產生的另類敘事模式,更加普遍地存在于一些幻想類開放式結局的電影當中:即主人公在特定的精神狀態和現實環境下,創造出一個平行的非現實世界,主人公穿梭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現實世界的遭遇以及對主人公產生的影響會在非現實空間中體現,而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欲望和想法也會在非現實空間中產生變形和滿足。
《水形物語》的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早年間的成名作《潘神的迷宮》就是這樣一部開放式結局的電影:現實中的小女孩死于繼父的槍口下,而在非現實世界中,小女孩因為自己的善行回到了童話王國。而連接起兩個時空的,正是小女孩自身面對現實遭遇產生的心理變化在非現實世界的投射。
而《水形物語》作為一部奇幻題材的開放式結局電影,有著同樣的特質,并且在這樣的心理投射思想的下,本片則產生了另一重解讀:即人魚本身是艾麗莎人格的分身,本身并不存在,人魚的故事僅存在于主人公的主觀世界當中,是主人公在現實環境心理下產生的一個變形。首先,人魚這個形象本身與主人公的特質有太多相似之處:主人公魚鰓狀的傷疤,對水有著天然的喜愛、喜歡吃雞蛋、喜歡電影等等特征都在人魚身上有所體現,可以說,主人公喜歡的東西,人魚都會自然而然被吸引。人魚和主人公一樣,都不能正常發聲,用手語交流,而大多數時候,雙方的互相理解遠甚于手語交流程度。而這種生理上的失聲,同時也代表著主人公作為一個社會底層女性面對男性社會的權力失語,而這種失語也體現在人魚的遭遇,淪為人類的階下囚,完全沒有申訴和反抗的空間。其次,人魚和主人公的遭遇有許多的相似之處:來歷不明——主人公是孤兒,人魚來自雨林深處,都是被“打撈”到人類社會中的。在現實世界中,都收到了虐待,甚至來自于同一個人,即邁克爾·珊農扮演的反派理查德。甚至可以推測理查德的手指并非人魚咬斷而是艾麗莎所為,在電影中存在兩點暗示:一者是被人魚咬掉的手指由艾麗莎發現并歸還;另外電影有很明顯地表示過艾麗莎受到過理查德的霸凌和侵犯,而咬斷反派手指很可能就是在主人公受到侵犯時的過激行為,而在主觀世界中則被投射成為人魚的行為,在侵犯-反抗-咬斷手指-歸還手指這個完整的事件中,交錯成為主觀世界和現實世界敘事。
在這樣的解讀下,整個水形物語的故事便被還原成一個底層邊緣人逃離現實壓迫,并在腦海中構建出一個溫馨童話的現實故事,這與本片導演的早期同題材電影《潘神的迷宮》采用的是相同的手法。而在這樣的現實心理投射下,這個溫馨的童話包裹著一個現實的內核,也被導演注入了對邊緣人物的關懷。通過這樣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讀,可以認為:影片表面的故事文本下,隱藏的是一個更為慘痛和冰冷的現實。而這種相對的現實,在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中,則投射出了一種別樣的氣質,將原本悲慘的故事原型,柔化成大眾可以接受的童話故事,增添了溫暖感人的氣質,卻保留了對殘酷現實的隱喻。這樣的手法與《潘神的迷宮》如出一轍,卻更為隱蔽。除了心理元素對現實故事的隱喻之外,另本片呈現出童話氣質的,還有本片中對現實人物形象與傳統童話敘事范式中的照應。
三、經典童話范式下的現實人物創作
作為一部奇幻題材的電影作品,《水形物語》的敘事模式并未脫離傳統的敘事范式。從故事的整體結構來看,也未脫離傳統的童話敘事模式。在經典童話模式中,“善良戰勝邪惡”是最基本的故事模式和價值取向,借由普羅普的“行動范疇”和格雷斯馬的理論分析,《水形物語》并未脫離這一經典敘事架構:“愛情童話最基本的敘事單元可以分為:男女主人公相遇——二人相愛——壞人出現,制造危機——英雄在施惠者和幫手協同下解決危機——圓滿結局。《水形物語》在敘事主體基本符合這一固定結構的基礎上存在陌生化拓展”。
因此,《水形物語》的人物處理,依然可以套用傳統童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分析,而主人公本身形象就有著“小美人魚”“灰姑娘”等經典童話人物的影子和隱喻。但是在女性主義的立場前提下,導演處理對隱喻的本體又做了一定的變形:這個童話故事模板中,人類主人公變成了女性,非人類角色成為男性,而傳統的“王子與公主”的形象也被一定程度地被消去夢幻的光環,成為社會邊緣人(主人公艾麗莎)和怪物(雄性人魚)。不論是作為怪物的男主角,還是作為女主角的艾麗莎,都打破了人們對童話故事中王子和公主的固有認識,主角不再是光鮮明麗的形象;甚至這一對人魚戀的組合也顛覆了人們對標準愛情故事的期待。而對標準童話人物形象的變形,卻使得這部奇幻電影對觀眾產生了一般意義上的童話所無法企及的感染力,即現實人物在影片中產生的投射效果。
不同于傳統童話故事中營造的完美白日夢,王子和公主有著無可比擬的光環,占據著敘事的絕對焦點,《水形物語》中的主角并不完美,甚至帶有殘缺:女主角身材消瘦、面色蒼白甚至帶有病態,同時還是個不能發聲的殘疾人,生活上更是捉襟見肘,甚至與灰姑娘相比,她也缺乏對異性的吸引力;而男主角不僅沒有人魚的美貌,甚至自身也是人類的階下囚,大多數時間更像一個可怖的他者,處于待拯救的狀態而非能夠拯救主人公的英雄形象。在處理這兩個角色的過程中,導演將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所感受到的壓迫與無助代入到角色當中,而褪去童話故事中公主與王子的光環,進而將普通人的人格更多投射到電影角色。所以電影雖然是奇幻故事,而角色本身卻具有現實人物的影子。
可以看出,雖然人物的原型以經典的童話范式為起點,導演卻對童話人物的處理并非毫無保留地照搬:保留電影人物和童話原型的隱喻和對應關系,卻將人物塑造的重點落實在現實世界當中。這樣的處理一方面使得觀眾在整體的形象上迅速建立對角色的定位——現實版的小美人魚,另一方面通過對人物現實環境和現實命運的寫照,迅速建立起觀眾的情感——對自身現實的反思和對人物的深刻同情。
甚至在處理配角的問題上,也貫徹著現實世界的人物投射:如反派理查德對主人公殘疾的欺凌,獨居的鄰居老畫家查爾斯因性取向受到歧視和孤立,這些角色并非圍繞著主人公而存在的工具,本身就具備著一定的社會屬性和獨立人格。而這些具有現實投影的角色讓觀眾在身份和情感上產生認同與共鳴。
結語
《水形物語》雖然是一部奇幻題材電影,卻包含著現實的內核。導演通過大量場景的細節設計和隱喻化處理,以現實作為底色,構建出一個溫馨感人的童話故事,在奇幻敘事之外,表達了深切的現實思考和人文關懷,其中包含的現實元素更給本片帶來了豐富的思想價值。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