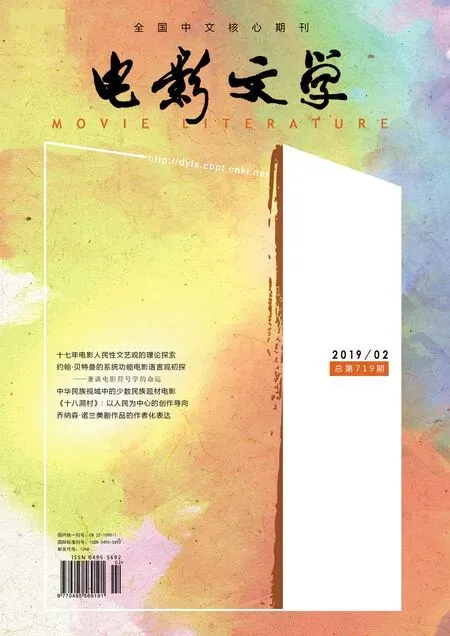類型與作者:文晏《嘉年華》的劇作內涵
楊會軍 (黃河科技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2017年《嘉年華》獲得多項國際大獎提名后迅速在國內引起討論風潮,許多批評實踐圍繞該片女性議題或者藝術性質進行討論,以現實主義來界定這種類似的群體美學,卻忽略了類型片中創作者與類型對話的語境,回避了《嘉年華》的類型身份以及文晏的類型劇作策略。本文從類型電影批評視角以及電影理論來探討《嘉年華》的劇作特點和作者表達,試圖揭示《嘉年華》的劇作內涵。
一、劇作定位:類型移植與隱晦表達
托馬斯·沙茨認為議題手法是電影把觀眾引入影院的有效手段,而政治片類型(the political film)則是一種將司法議題搬上銀幕并與觀眾對話形成觀影經驗與文本慣例的類型集合。這類影片二戰后法國意大利出現,之后發展為不同亞類型。學者魏英[1]從文學視野將《嘉》定義為東亞“反性侵”事件類型電影,但從電影發展與類型理論研究看,《嘉》包括韓國《熔爐》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反性侵亞類型電影。國內大多批評的問題也在于此,如果沒把握住政治片與該片的反性侵、現實性、性別、藝術性等特點的親緣關系,則很難解讀《嘉》包括韓國《熔爐》的公民審美的母體內涵。
政治片審美核心是公民美學。學者凌振元、郝建在界定政治片屬性時都強調用影片立場——即影片是否站在公民的立場去表達影片,來判斷政治片的類型。從阿爾特曼的身體情緒標準解讀,也可以理解為政治片滿足的是公眾對于司法體制監管的正義情感訴求。公民立場構成了政治片核心價值,也劃分了主旋律意識形態類型電影和政治片的不同。《嘉》以民間立場控訴司法黑暗,故事核心是女律師幫助兒童受害者和強權斗爭打官司,可以說該片的民間立場突破了此前大陸主旋律性質的法庭片、官司片的官方立場,從而為當下中國電影植入了嶄新類型。
國內影迷包括一些學者將此片與韓國同類電影并論并放進亞洲電影框架內探討,但從類型批評視野看這種美學潮流,其實是類型電影特有的風潮性與對話性在各國跨界移植的后果,問題也在于此:對比政治片在韓國、日本的跨界實踐,政治片在大陸移植中卻選擇了隱晦策略。中國趙作海的司法類事件層出不窮,但政治類型片卻沒有在體制、特權、階層等公共議題領域進行首秀,反在性侵事件這一性別色彩較強的議題率先表達。即便借助性侵亞類型,價值觀與形式上也有較大折扣。有資料顯示,該片有國際版[2]與國內改編版兩個版本,這兩個版本變動較大有兩處:第一處是郝律師把證據給警察后被黑幫追殺,而國內版則改為新聞發布會后郝律師就再也沒出現;第二處是小文做第二次檢查后得知作假于是跳樓自殺,而國內改編版小文則重新回到家庭。正如Screen Daily評論,國際版令人感覺“在這個扭曲的世界發現守護者就是掠奪者”[3];但在國內版本結尾卻給了觀眾如同嬰兒般依戀政府母體的鏡像快感。韓國政治片出現了關于職能機構作為反派的設計,但在前現代中國與文化壁壘語境里,同類劇作如《荒城紀》《藥神》,只能選擇與《嘉》類似的隱晦表達的策略。
二、人物關系設計:鏡像結構與作者身份
第74屆威尼斯電影節上《嘉》打出“主競賽里唯一一部由女性導演創作的影片”[4]的口號,所以說如果文晏用民間立場實現《嘉》類型移植而博得國內精英關注的話,那么用女性風格對《嘉年華》內容的詢喚則是文晏有意識地向以女性為主評審團的迎合和自我表達。從勞拉·穆爾維性別論推斷,在父權制度下政治片給予女性的只是一次強化父權制的再教育,即便政治片劇作的人物關系設計仍然是突出男性英雄幫助弱小女性的模式,女性主體仍無法脫離勞拉所說的敘事困境。但在《嘉》中,文晏在人物關系設計上利用性別沖突替代政治片中正義沖突的設置,大膽地將女性主體性推上銀幕。
在《嘉》性別二元對立結構中,幾乎每個女性都承受著男性的暴政。小文在學校受到小胖子欺負;莉莉被推向了老板座位,小米被小飛戲弄;小文媽受不了丈夫沉默離婚;即便是郝律師在職場上也受男警察牽制。把所有女性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片中不同女主人實際上是一個女人不同年齡階段的不同側面而已:或許小文離家出走成功四處流浪之后變成小米,小米如果辦不了身份證向環境低頭賣身成功或許就變成了前臺莉莉,前臺莉莉幾次被所愛的小阿飛玩弄之后,可能隨便找一個老實人生下孩子變成小文媽媽,小文媽可能有一天不想打麻將跳舞洗心革面最終變成了獨身女律師。文晏編導在《嘉年華》對女性人物關系的編排揭示了中國女性在父權秩序生存的艱辛不易。在一部大格局的大戲中,片子中人物關系互為鏡像,身份隱喻又互為阻力,人物關系結構顯得非常厚重。著名編劇李亞玲在博客中將這種人物關系的編劇技巧稱之為“鏡像理論”。這些人物互為鏡子彼此映射,揭示中國女性在不同命運階段面臨的困境,層層強化片子主題。
從性別視野看世界類型電影發展以及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以女性觀眾為主的電影類型家族中,研究者不會把政治片劃入其中;而在傳統政治片主流創作名單中,大部分政治片作者是男性。作為女性編導,文晏沒有像越南陳翠梅、中國香港許鞍華、印度米拉奈爾等其他世界女性編導一樣深耕家庭倫理片類型,而是巧妙地把女性身份和性別關系與類型形式結合在一起去突破政治片的性別障礙,擴展世界政治片家族類型的女性“意味”。
三、劇作結構:符號、色彩與神話
在海報、制作以及海外發行方面《嘉》使用國際化風格來吸引觀眾,其實更國際化的是文晏圍繞影片主題使用的文本表達。
首先夢露主題符號。文晏在采訪中提到所以創作現在劇本是因看到關于夢露雕像在廣西當地以有傷風化為名被拆遷的新聞。文晏在分享中被朋友以瑪麗蓮·夢露代表除了愛之外的一切的解讀所打動,認為“這個寓意與《嘉年華》的缺少愛、尋找依托”[5]的成長主題不謀而合,于是有了不同于傳統政治片的文本結構安排。按照理查德·戴爾等人的明星理論來看,夢露本身來源于好萊塢明星制下男性意識形態的國際化的女性形象塑造,這種符號的選用與類型雜糅凸顯了影片背后的國際電影節意圖。
其次構建女性神話的歷程。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指出好萊塢電影其實是千面英雄歷程,維多利亞·林恩·施密特從性別角度指出構建女性的歷程在電影劇作中是更具有國際化的表達方式。小米在影片中遇到多重困境:身份困境、階層困境、性格困境。小米多年流浪被社會所排斥,養成冷漠自保的性格,她沒想到被小飛哥所欺騙,只好接受命運的懲罰,可當她聽到案子新聞時便大膽出逃。如同施密特的女性英雄之旅,小米從多重困境到女性身份尋找過程中,經歷了覺醒、抗爭、絕望、脫胎換骨,最終重生為掌控人生的人。
再次人物塑造與色彩符號編碼。電影英文名字為AngelsWearWhite,意為白衣天使,色彩編碼暗含了整個劇作主題的文眼。在影片中著白色衣服的人物有小米、小文和夢露,其中小米的人物形象非常清晰體現了這點。開頭小米是白色校服的中學生;當回家被媽媽因性侵事件粗暴剪發,小文才意識到少女身份此后要被剝奪,離家出走后服裝就變成深色;小文與父親和好之后在家外修樹枝,此處又變成了白色,預示在父權幫助下尋回少女身份。從開頭白色服裝到性侵之后深色,再到父女關系和好之后白色,片子利用顏色編碼實現了小米形象過渡。
全球化電影傳播需要國際化的方式和文化主題。文晏的國際獨立制片經歷給了她廣闊的視野和手法,從而使得劇作在架構上從政治片傳統主旨變成了兩個女孩能不能尋找到“身份”的主旨,這種策略給本片政治片身份蒙上女性成長歷程意味,這也博得了世界影迷的贊許。正如國外評論Hollywood Reporter指出,“這是一部關于女性在中國難以定位的事情,這種戲劇暗示了女性在中國的困境”[6]。
四、劇作空間塑造:無聲底層與現代性書寫
劇作空間在電影中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第一是故事發生背景,這層空間是戲劇意義上的。盡管作者模糊了故事背景,但據“夢露雕塑像”這一線索不難發現廣西貴港的地理身份與片中背景高度吻合。不同于貴港官方網頁對于貴港形象的高端塑造,片中則展現兩個低端、另類的城市空間場所:暗地里進行賣春活動的旅館,各色人等在玩耍的海灘。這兩個場所將貴港塑造成了前現代中國縣城的典型。這與《無人區》的西部、《爆裂無聲》的礦區、《我不是藥神》的貧民窟一樣,它們共同繪制出前現代中國真實的底層符號,但在銀幕上卻無法命名。
第二種空間是類型片獨有的視覺空間。政府司法體場地在政治片中構成了政治片視覺特征,既是司法職能與法律權力的延伸,也是強權控制社會秩序之地。《嘉年華》有三個主要司法場所:警局、新聞發布會、醫院。警局代表著行政話語權、醫院代表著評判話語權、新聞發布會代表傳播話語權。這三個銀幕場所在中國現行體制語境下不但產生了權力黑幕,更重要還多次用場景手法揭示了底層話語權危機,影片的進步也在于此。
第一次在警局審訊。這場戲視聽語言風格以冷色調、手持、警察畫外音的風格編碼,表達公民對以王警察為代表的典型官僚主義的譴責,作為未被定性的小文則始終處在話語權危機中。
第二次在醫院復檢身體問題。這場戲中出現兩段長鏡頭。小文被醫生凝視,而醫生被觀眾所凝視。這場雙重凝視描繪的不是女性被占有的畫面,而是展示底層社會如何接受話語規訓,從而激起觀眾公民權利受到侵犯的正義感。
第三次在新聞發布現場。這場戲構成了整個劇作小高潮,揭示了中國當下社會“底層”與話語權的微妙關系。在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福柯“權力話語”理論里,社會頂端協會會長用權力控制社會司法體制,還通過新聞媒體控制著話語權;而處在社會低端的小文爸卻被司法體制當作啞聲人。
這部影片中無聲與有聲、話語與失語給觀眾營造缺席與在場的辯證圖景:警察、醫生、劉會長以畫外音的形式編碼但是控制著社會階層的話語權,他們是在場的缺席。而底層社會的小文、小文爸,雖然在現場但聲音沒被表達,最后如小文爸用暴力落得暴民罪。因此他們是缺席的在場。
五、結語
本文從類型批評視角揭示《嘉年華》的美學特征,經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嘉年華》以民間立場來控訴司法黑暗與不公,片中劇作元素如基本沖突、人物關系、空間選擇、主干情節共同構成了《嘉年華》政治片的身份,由此完成了從歐洲經典政治片母體到東亞政治——性侵這一亞類的跨界移植。為了平衡審查,文晏在劇作上選擇了隱晦表達,為了展現作者思考、迎合國內外觀眾口味,文晏呈現了文中所說的其他劇作策略。
當前商業電影氣候下很多影片其實都是類型外殼,但在批評實踐中缺少對類型電影美學的分析。中國當代電影批評發展,首先要擺正學者身份,不忘批判立場,同時立足本土類型批評,用這種批評方式回饋中國電影和電影美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