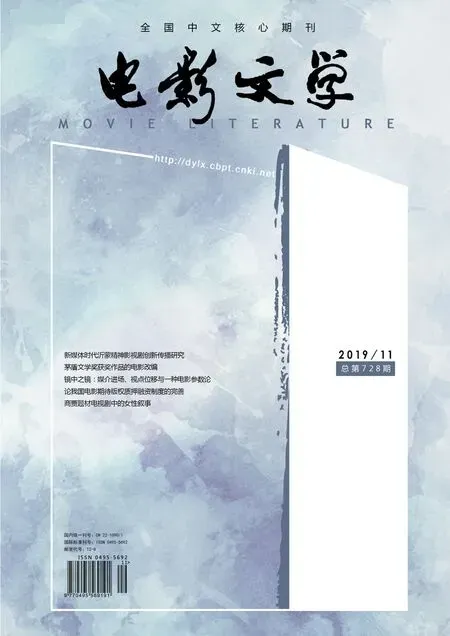世紀交接點上的光影祛魅
——論當代韓國電影與“中韓文化之爭”
李賽喬 龐 弘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一、世紀交接點上的“中韓文化之爭”
揮別20世紀的中國,正搭乘著互聯網的列車,在21世紀的軌道上奔馳。而就在此時,在中國文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疆域內,一種轉移正在默默地發生:面對以言情劇、電影、歌曲、服飾、餐飲為標志的韓國流行文化,多數中國人不再如20世紀90年代末一般沉溺其中、流連忘返,相反,他們開始了有保留地接受、警惕地審視,甚至是義憤填膺地譴責,而曾經被當作是時尚先驅的“哈韓族”也搖身一變,成為90后“腦殘”一代的“光輝典范”。仿佛是轉瞬之間,昨天才奮不顧身追逐“韓流”的人們,今日便開始痛斥韓國的種種“劣行”,恨不得高舉大錘,給“高麗棒子”狠狠一擊。
在世紀交替的關節點上,“韓流”的漸漸退去當然并非無因可尋:北京奧運、“和諧社會”、初等發達國家等社會主義國家允諾的美好前景,以及民眾在抗擊天災人禍的實際斗爭中所不斷升騰的患難豪情,從正反兩方面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蘇醒與國民凝聚力的提升;“超女”“快男”、《士兵突擊》等中國式的大眾節目和《欲望都市》、“哈利·波特”、NBA等“西洋快餐”齊頭并進,占據了本土受眾愈來愈多的生活空間;而各色流行文化的長期熏陶,也使一種更挑剔的消費心態在人群中逐漸萌生……不過,粉碎韓國在大陸公眾心目中“浪漫家園”形象的最直接因素,還要屬在21世紀愈演愈烈的“中韓文化之爭”。
2007年11月,韓國大學教授鄭在書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將炎帝、蚩尤、夸父等中華民族耳熟能詳的神祇追溯為韓國人的祖先,從而繼2005年韓國申報“江陵端午祭”為聯合國“非遺”項目,2006年自命為印刷術起源國,擬改“中醫”為“韓醫”之后,再一次將關于中韓文化起源與所有權的爭論推向了風口浪尖。實際上,與其將所謂“中韓文化之爭”定義為中韓兩國的文化角力,不如說,這更多是中國文化界對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文化行為所做出的單方面回應,而在后現代語境下的今天,這些回應又顯得格外駁雜多元。
除去廣大草根階層(如前文所述)的暴民式聲討之外,商業傳媒也紛紛鼓噪,采用“豪搶”“掠奪”“捍衛”等頗具震撼性的詞匯,在吸引眼球的同時也收獲了可觀的利益。(1)廣州《新快報》于2007年12月推出由《中國網民捍衛漢字專利》《7億,韓國搶奪端午根》《韓國“豪搶”中華文化名人》等六篇報道組成的“中韓文化之爭”專題,在社會上一度引發熱烈反響。而主流輿論更是不甘寂寞:無論是對文化產權的真正歸屬進行考據式的挖掘,還是對韓國的“歷史隆胸”行為表示理解,抑或追問中國政府對傳統文化保護的不利,均大有人在。(2)在隸屬于《人民日報》的主流網絡平臺“人民網”上,此類文章時常出現,如《比傳統節日“申遺”更重要的是什么?》《可笑!韓國人發明了漢字?》《“為歷史隆胸”一樣值得尊重》等。當然,也有論者指出 “中韓文化之爭”只是一個偽命題而已,新聞媒體的煽風點火,平民百姓的憂郁憤慨實屬無事生非、庸人自擾。(3)于德清于2007年12月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是誰在臆造中韓文化之爭》一文,對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夸大其詞、捕風捉影加以抨擊。這一切的一切,宛如一大鍋觀點的雜燴,冒著渾濁的氣泡,叫人迷惘而又無奈。
二、作為文化心態之鏡像的當代韓國電影
或許,可以從這樣的混沌中提煉出三個關鍵:首先,無論如何,韓中兩國長期以來的親緣關系都毋庸置疑。如有學者便談道,“在地圖上,韓國很像是長在中國東北角的一塊手指甲或腳指甲,也有人說朝鮮半島就像中國懷中的嬰兒”。[1]在文化上,朝鮮更是自三國以來便努力向中國靠攏,明代以后甚至以“小中華”自居,視自己為漢文明的正宗。這種地理與文化的雙重血脈在今天仍無法割斷。其次,德國學者加達默爾曾提出,理解絕非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行為,相反,在意義解讀的過程中,主體總是被先在的情趣、秉性、立場和境遇所左右,總是帶著形形色色的“前見”(prejudices)來打量周遭的世界。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國際交往中,前見的存在同樣屢見不鮮。無論有著怎樣親密關聯的國家,彼此間仍不可避免地隱含著深層次的、來自文化基底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前見滋生的樂土。在雙方(或多方)帶有歧異目光的相互審視下,諸如“文化之爭”一類問題的產生也就在所難免。最后,在加達默爾看來,前見絕非需要設法彌合的鴻溝,而是主體得以存在的本體論必然,正是在前見的驅使下,“我們把自己置入他人的處境中”,進而實現“向一個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這種普遍性不僅克服了我們自己的個別性,而且克服了那個他人的個別性”。[2]因此,前見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一個契機,它將推動交往者達成一種揚棄彼此局限、不斷向共通性和普遍性提升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在此,主客雙方的相互理解、彼此溝通成為關鍵。同樣,困擾于“文化之爭”的當代中國,或許只有以前見為依托,竭力切入韓國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用“換位思考”的姿態努力捕捉其文化精神的核心,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至少是盡可能減少)文化交流中的差異和悖論,使真正的坦誠溝通(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實現。
那么,在跨越文化語境的前提下,如何實現對他者之民族性格的確切把握?無疑,讓每個人漂洋過海,身臨其境地領略韓國的文化生活是不現實的。那么,是否還存在著一種替代,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凝聚著韓國文化精神的象征符號?于是,正在慢慢淡出人們視野的韓國大眾文化再次成為理應關注的對象,而在其中,一度在中國乃至世界舞臺上風起云涌的韓國電影又格外引人注目。誠然,電影所具有的廣闊涵蓋面和強大表現力,使之常常能觸發主體精神世界的強烈共鳴,并促使人們感知潛藏于社會表象下的深層次脈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便以獨特的取材、個性化的影像、大膽多樣的敘述手法而備受好評,從而使韓國文化的風神氣韻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王德威曾提出“小說中國”一說,即近現代中國小說有助于人們領會近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3]同樣,作為國人觸手可及的視覺資源,當代韓國電影也恰如其分地充當了一面鏡像,它將有助于研究者窺探斑駁的韓國文化精神圖景,并不斷洞悉韓國民族心態在當代的演繹與延伸。當然,跨文化的“他者”身份往往會制造認知的障礙,但這也減輕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惶惑,增添了一分由“距離”所產生的客觀。
按照新歷史主義的見解,歷史與文學在構造方式上存在著異曲同工之處。其實,被帕索里尼譽為“詩”的電影同樣蘊含著“從比喻上把握世界”[4]的潛質。電影在反映社會真實的同時,也承載著謀取商業利益、宣揚民族形象、傳遞思想意涵等使命,故而,諸多刻意為之的加工、修飾與改造也將充斥其中。如此一來,對韓國電影的解讀也便成為一次“祛魅”(Disenchantment),這種祛魅不同于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現代性對遠古神話的消解,而是要求人們揭開光怪陸離的光影面紗,不斷反轉悖謬、填補裂隙,以抵達內在的深度真實。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的不僅是立足于文本的細致勘探,不僅是一種持之以恒的批判姿態,更在于對原初歷史語境的還原與重構。
三、多重制衡下“半島性格”的光影演繹
自誕生伊始,韓國便因半島的地理位置而處于多重力量制衡的境遇。半島地形使韓國兼具大陸和海洋的雙重空間,正因為如此,自古以來,韓國便扮演著一種“跳板”的角色:大陸國家為自我保全或是向海洋擴張,需要以它為橋梁;海洋國家出于抵御大陸進犯或是朝大陸延伸勢力的目的,也渴望占據這一難得的“中轉站”。這樣的狀況,致使韓國長期以來受到來自大陸與海洋的雙重擠壓。如果說,來自外民族的壓制是困擾韓國的一個歷史問題,那么,今天的韓國則更多陷入朝鮮民族自身分裂的紛爭之中無法自拔。朝鮮半島擁有陸海相接的優越戰略位置,因而被美蘇兩大帝國視為爭奪亞洲霸權的重要關節點與理想突破口。在兩大勢力的介入、扶持下,以北緯38度線為界,原本具備高度統一性的朝鮮民族被迫分裂為受不同意識形態熏陶,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水火不容的兩個世界。足見,從外部到自身,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韓國都處于多重力量制衡所帶來的復雜、深刻的矛盾之中。鑒于此,李御寧在論及韓國的地理條件時,才會將其比作一只“小蝦”,用“鯨之爭蝦脊裂”的諺語來形容朝鮮半島不可擺脫的歷史宿命。[5]
多重的力量制衡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精神氣質。韓國歷史學家李元燁曾緊扣韓國的半島特征,將韓國的“國民性”歸納為“半島性格”。[6]所謂半島性格,并不單純是一種焦慮、躁動的“急性子”風貌,而更多喻指植根于韓國獨特的半島地形,經由漫長的歷史演進,在諸多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種以“國家行為—民族選擇”為核心,旁涉文化精神的諸多層面,且打上了深刻“韓國”烙印的民族心理趨向。首先,面對多重的外來沖擊,韓國并沒有選擇魚死網破的“自殺式”反抗,而是始終維系著一種異常堅韌的姿態,在諸多力量的縱橫交錯中耐心斡旋。具體到國家行為,便是它總能審時度勢地選擇依附最強大的一支勢力,從而確保國家、民族的存續。其次,表面的“無作為”并不代表韓國完全喪失自主性,相反,在面對強勢文明的施壓時,韓國也常常化被動為某種程度上的主動。這體現在它能夠借臨近先進文明的條件,盡可能多地吸收、借鑒,從而將自身的不利處境轉化為騰飛的契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之所以能締造轟動亞洲的“漢江奇跡”,便與主動向西方現代文明靠攏的務實性不可分離。最后,一味跟隨并非韓國文化精神的恒態,一旦步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它便會以自身的國家實力與文化底蘊為依托,竭力擺脫曾經被打上的異域文化烙印,從而使自身的民族特性得到最鮮明的彰顯。(4)這一點在朝鮮文字的使用上尤顯突出。長期以來,朝鮮一直樂于使用漢字并視之為東亞文化的正宗,隨著國力的增強,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朝鮮在15世紀創制了自己的文字“訓民正音”并逐步推廣,最終大大削弱了漢字的影響。總之,這種半島性格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包容性,同時也不乏堅毅的民族個性,正是它見證并推動了半島的風云際會。邵毅平先生認為朝鮮半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應戰其地緣環境之挑戰的歷史”,指出“抵抗與利用的巧妙平衡,才是應戰的真正意義之所在,也才是應戰的根本智慧之所在”,[7]其實正點明了半島性格的關鍵所在。
在當代韓國電影這一鮮活、生動的場域,半島性格從如下三個層面得到了意味深長的演繹。
首先,在時間層面上,韓國電影同時體現出對“現代”與“傳統”這兩個向度的熱切追尋。作為一個弱勢國家,韓國長期被迫承受西方現代性的壓抑,同時又試圖借助其地緣優勢,盡可能將這種現代性化為己用。在《我的野蠻女友》《向左愛,向右愛》《誰都有秘密》等書寫都市生活的影片中,咖啡店、西餐廳、街心公園、汽車旅館、地鐵、商業街等現代符號得到了頻繁的、近乎夸張的炫耀性展現,隱含其中的現代性訴求也由此而可見一斑。同時,由于歷史原因,韓國是一處異質文明交錯的場域:流行的美國文化,依舊保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明,外加短時期內難以清除的日本元素,構成了一塊混雜著各種色調的“文化拼盤”。“多重文化雜糅共生所帶來的必然是民族精神在漂泊、茫然之余對傳統尋根的更加強烈的要求”,[8]故而,在韓國電影中,又時常體現出對傳統民情風俗的濃墨重彩的渲染和描畫。無論是《丑聞》中的華美服飾,《王的男人》中的錯落樓臺,《春香傳》中的青綠山水,《醉畫仙》中的放浪形骸,都可被指認為某種重塑民族精神的刻意為之的視覺策略。
其次,在空間層面上,韓國電影對與之休戚相關的異域形象做出了耐人尋味的修飾、加工和改造。縱觀當代韓國電影,三類異域形象最引人注目。其中,中國形象往往呈現出“在肉體上被韓國人戰勝”和“在心理上對韓國人屈從”的套路,前者以《武士》《天軍》《雛菊》等暴力電影為代表,后者以《白蘭》中對韓國浪蕩子一見傾心的柔弱中國女子為典型。上述視覺定式,反映了韓國在獲得文化優越感之后,在中華文明面前重塑自身尊嚴的渴望。美國形象在“極愛”和“極憎”兩極間來回搖擺。在大量韓國電影中,隨處可見對美式生活的追捧與炫示,但同時,在部分影片中,美國形象又以詭譎、可怖、充滿攻擊性的姿態出現——《漢江怪物》中那個散發著后工業時代氣息的畸形怪物,便是典型例證。這樣的矛盾態度,暗示了韓國對強勢文明的親近、依賴與眷戀,同時又流露出某種憂患意識和戒備心理。較之前兩類形象的定型化傾向,朝鮮形象更多呈現出一條從“尖銳”到“柔和”的演進軌跡,從《生死諜變》中陰森冷酷的朝鮮特工,到《共同警備區》中褪去神秘面紗的朝鮮士兵,再到《南男北女》中歷經波折終與韓國男子修成正果的朝鮮女孩。上述形象的嬗變,所折射的是韓朝兩國在半島地緣格局中的微妙角逐和試探。這些斑斕駁雜的光影演繹并非純然的娛樂,而是蘊藏著復雜的權力糾葛與深切的文化—政治沖動。
最后,在最直觀的生命體驗層面,韓國電影在“肉體的張揚”與“肉體的限定”之間輾轉反側。自世紀之交以來,大量書寫個體涌動之情欲的影片紛至沓來,不僅打碎了人們對韓國電影“浪漫”“純情”的固有印象,同時也將含蓄、持守、克制的傳統價值觀撕扯得支離破碎。無論是《漂流欲室》中絕望男女的靈肉掙扎,還是《美人》中的等待和嫉恨、背叛與堅守,無論是《撒瑪利亞女孩》中女高中生和嫖客之間的肉欲與拯救,還是《愛的色放》中性愛、青春與政治的曖昧糾纏,往往都帶給觀看者無以復加的視覺沖擊和精神震撼。上述影像文本所昭示的,是西方激進理念(尤其是女性主義理念)在韓國文化中掀起的波瀾。不過,“現代”與“傳統”始終是韓國文化的雙重基座,故而,在縱情擁抱西方式的情欲解放時,東方式的道德綱常依然是韓國電影中難以違逆的律令:其中包含著對欲望的節制(“發乎情,止乎禮義”),包含著對家庭之穩定性的尊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時也包含著對女性之微末地位的指認(“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落實到影片中,盡情滿足感官欲求的主人公并未在“離軌”的道路上愈行愈遠,相反,在短暫的瘋狂過后,他們往往面臨難以解脫的困境:要么尷尬退出,要么眾叛親離,要么死于非命,要么則陷入無止境的困頓與迷惘……足見,韓國電影一方面熱情洋溢地謳歌肉體的張揚,另一方面又無可遏制地表露出對這種現代身體觀的反躬自省式的限定,以上兩種姿態的對峙,無疑將構筑更錯綜復雜的影像世界。
上述光影演繹雖未能窮盡韓國電影的全貌,卻無疑為研究者對當代韓國文化精神的探析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視點。總之,我們的目標,是以世紀之交的韓國電影為鏡像,從中透視半島語境下半島性格的基本面貌,從而建構起關于跨文化“他者”的更立體、豐滿、生動的形象。同時,作為高校的一線教學科研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我們也希望以此研究為契機,助力公民視覺素養的不斷完善,并逐步使青年一代(尤其是在校大學生)擺脫網絡時代偏激、躁動、盲目的心理癥候,在眾聲喧嘩的“中韓文化之爭”中保持客觀、公允、理性的觀照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