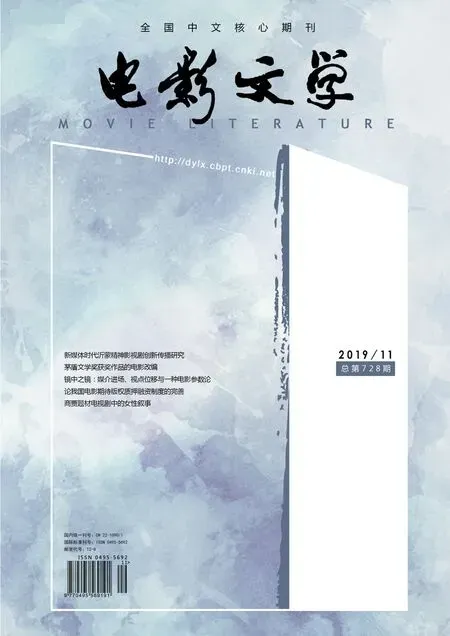后情感視角下國產IP電影的新女性凝視
林 筠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福建 廈門 363105)
一、新女性凝視與國產IP電影
張藝謀早期的電影《紅高粱》(1987年)、《秋菊打官司》(1992年)等以描寫女性為題材的中國電影作品幾乎從未淡出觀眾視線,2010年以來出現的一批國產電影更是塑造了一批新時代新女性形象,其中IP電影現象尤為突出。“2010年起至2018年3月13日國產電影內地票房的前60名電影,發現其中國產IP電影共有36部,占比60%,票房超過10億的共有14部,其中以喜劇和愛情電影居多。另外,發現國產電影內地票房的前10名電影均為IP電影。”[1]可見,IP電影成為國產電影這個階段的寵兒和行業主力,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潤。IP即為知識產權,最初是一個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專業術語,但在文化產業中IP則“可以是一個故事、一種形象、一件藝術品、一種流行文化,也可以指適合二次或多次改編開發的影視文學、游戲動漫等,IP背后成千上萬的狂熱粉絲和他們不容小覷的消費能力是重要的影響力體現”。[2]以此為延伸,IP電影就是以粉絲熱度和商業價值為基礎,由原創性優質版權內容改編而來的電影作品。IP電影熱潮興起的背后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那就是女性觀眾數量的增加。根據《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2006—2015)數據分析,在此10年間,女性觀眾的比例持續上升并最終遠超男性觀眾,主要構成群體18~30歲人群的比例也在持續上升,中國電影觀眾正在呈現女性化、年輕化的發展特點。年輕女性觀眾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推動了國產電影產業“她經濟”時代出現,以新時代女性理解為核心、凸顯新女性自由和價值的電影創作順理成章受到更多追捧,集中表現在大量以都市女性勵志題材為主的電影,從《杜拉拉升職記》(2010年)到《失戀33天》(2011年)再到《七月與安生》(2016年)等電影塑造了眾多醒目且經典的新女性形象,倡導用女性的新視角去審視社會生活、兩性關系和人生意義,反映了新時代新思想、兩性文化特點的新變化和未來趨勢,這種電影聚焦稱為“新女性凝視”,從女性觀影喜好出發又回到女性觀眾本身的這種機制呈現了一種電影對女性、社會對女性、女性對自身的凝視,“如何形成凝視”就是本文研究的要義。
二、新女性凝視與空間感知
(一)新女性與情感空間
情感空間主要是指作品中所呈現的新女性如何自我凝視,在兩性關系或同性關系處理中通過哪些情感塑造人物,傳遞給觀眾以產生感染力。2010年以來的國產IP電影以塑造年輕女性為主,其中一大類是以暖傷青春為情感基調的校園愛情電影,所塑造的典型形象通常是:初戀失敗的女高中生或女大學生。《致青春》(2013年)與《匆匆那年》(2014年)均改編自網絡小說,影片延續了原著中的暖傷,表面上看緬懷的是80后青春戀情,難以忘懷的初戀象征了女性對情感的執著,林林總總的失敗道出了當下女性的愛情憂傷,在這樣一個情感紛亂的世界如何找回和找到那顆純愛的初心。《山楂樹之戀》有些與眾不同,將青春愛情與社會歷史相結合,回望的是70后所遭遇的青春,但手法也與以往以“文革”為題材的電影不同,突出純愛和傷感的浪漫基調,而非沉重的反思。回望網絡小說改編IP電影的發端,2000 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講述的也是一個傷感網戀故事,作品中的女主角是身患絕癥的青春少女,傳遞的是對生命中絕望處的美好情感寄托。
另一類則相反,以治愈系情感為題材,如《七月與安生》(2016年)、《閃光少女》(2017年)等,多描述的是群體像或多人像,呈現了當下90后少女的情感世界,友情與愛情相伴相生,“相愛相殺”成為一個高頻詞匯。《小時代》成為國產電影中成功續寫四部的經典IP,根據郭敬明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四位從小感情深厚,卻有著不同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90后女生,在經歷了友情、愛情、親情和職場生涯中轉變的情感關聯。《七月與安生》也講述了兩個性格截然不同卻又相互吸引的女生,她們原以為友情會彼此陪伴一生,卻不知不覺被愛情的紛擾隔閡,最后相互和解,但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并非愛情,而是女性的自我追尋、成長和超越。
(二)新女性與社會空間
社會空間更關注的是新女性與社會關系的互動及境遇,無論是所謂小妞電影還是其他,都更為強調女性作為獨立的生命個體應該如何多關注自身需要,而不是由傳統責任和義務來分散她們的注意力。根據2017年《女性生活藍皮書》中《第12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調查報告(2016年度)》顯示,42.6%的女性對工作感到滿意;17.0%的女性工余有兼職工作;女性認同工作意味著“經濟獨立”“生活更充實精彩”“精神面貌更好,交際圈擴大”“有機會發揮潛力實現人生價值”“人格獨立”“家庭地位上升”等,并有86.1%的女性感到工作壓力大。[3]這些都在2010年以來國產IP電影里得到表現。第一類形象是白領商務精英的代名詞:杜拉拉。《杜拉拉升職記》(2010年)改編自一本熱賣的同名職場小說,更是由女性導演執導的電影,講述杜拉拉如何從職場菜鳥成為職場精英,愛情雖貫穿始終但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苦苦追尋,而是職場女性如何拒絕辦公室性騷擾、潛規則,以及當愛情離開的時候不停止追逐自己的事業,最終迎來事業愛情雙豐收。杜拉拉是職場女性電影中的經典形象,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人格魅力,尊重自己的價值,但也需要兩性關系的和諧,而不是對抗或分崩離析,代表了當下中產階級女性觀眾的現實境遇和職場夢想,她們沒有背景卻有良好的教育,靠個人奮斗取得成功。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二類平凡女性的形象:黃小仙。《失戀33天》(2011年)改編自鮑鯨鯨的同名人氣網絡小說,故事用時尚又幽默的方式講述了快餐時代的愛情,只用了33天就從失戀走出陰霾。主人公黃小仙是當下大多數女性的寫照,平凡的自由職業,大齡未婚少女,姿色平平,家境一般,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一口刻薄言辭和對世界滿腔的盲目樂觀,她和男友長達七年的戀愛無果,卻看見男友和自己的閨密走到一起,她只能默默寫著失戀日記直到愛上自己的男閨密王小賤。對于網絡文學改編的電影來說,《失戀33天》是一個標桿,作品緊扣時代來描寫人物,誕生了“男閨密”這樣的熱門詞匯,解讀新型兩性關系和情感理解。相比之下,改編自網絡小說作品《請你原諒我》的電影《搜索》,表面上寫的是互聯網時代的新生產物“網絡暴力”,實則讓女性處于不堪一擊的傳統柔弱中,以致毀滅。
第三類可謂切中社會熱點形象,在社會上游走的利刃和資本可能不僅僅是才華,還有身體姿色和情感夢想,代名詞:文佳佳。《北京遇上西雅圖》講述了一個獨自赴美生子的小三如何在國外揮土如金,遭遇經濟變故后如何自食其力,在與老鐘組建家庭后又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坐標,最后毅然獨立帶著孩子開創事業和生活。文佳佳的身份設定有三個典型性:自由職業者、小三、單親媽媽,這個社會無法留給女性的往往都是以問題呈現出來的。母親是女性獨有的特殊身份和狀態,對于女性而言, 生命的新生不僅指肉體的生命, 也意味著精神生命的新生,正如克里斯蒂娃提出,新一代女性主義者正在經歷一場精神的“反抗”:“意義和沖動相互回溯, 從而揭示出記憶、讓主體的生命重新開始。”[4]文佳佳就是此類女性的代表,她從一個拜金女成長為獨立堅強的單身媽媽,在沒有婚姻和丈夫的情況下反而不困于世俗,靠自己的才華重新創業,爭取到對愛情、婚姻和事業的權利,這不可不說是一部新女性的勵志片。
(三)新女性與歷史文化空間
歷史文化空間是一個參照系,常常把新女性形象與傳統女性形象作為一個對比。“仙女”是最經典的女性IP,國產IP電影尤其熱衷,《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電影作品改編自同名仙俠玄幻小說,講述了青丘帝姬白淺和九重天太子夜華經歷三段,代表著前世、今生、來世因果循環永生不滅的愛恨糾葛,終成眷屬的絕美仙戀故事,是傳統且典型的專一婚戀觀念。電影作品頗受歡迎,其官方微博有近200萬粉絲,在電影上映前后更是發布了近500條微博。尤其是主人公白淺受到歡迎,其實集合了許多經典女性形象IP,如輪回中愛戀的白娘子、清純專情的小龍女等,也植入了更新的時代精神,比如白淺產子后,因為對愛人的傷心欲絕而選擇縱身躍下誅仙臺,又為忘記夜華主動飲下忘情藥等,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女性的主動權。但此類女性角色終究是對浪漫鐘情的呼喚和表達,是最傳統的女性情感寫照。相比之下,改編自流瀲紫小說《后宮·如懿傳》的電視連續劇《如懿傳》則更為優秀,作品講述了烏拉那拉·如懿與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歷一生從恩愛相知到迷失破滅的婚姻歷程,故事看上去著實精雕細琢地反映了清朝,但人物性格設定、情節發展走向、人物關系和成長弧光等都映照當下的男女婚戀和家庭關系。如懿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女性光芒令人看到了身為女性的一種力量,不再是《甄嬛傳》一般在男性主義視角下的后宮女性宮斗,而是凸顯女性自身力量和精神價值的歷史劇。
另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中國歷史中問題女性的改編和續寫,比如2015年馮小剛導演新作《我不是潘金蓮》還未上映,網絡上就出現了《潘金蓮就是我》《我不是你的潘金蓮》《誰是潘金蓮》《到底誰是潘金蓮》《誰殺了潘巾蓮》等,其中《誰殺了潘巾蓮》借著正版電影宣傳的熱度,在網上點擊率早早就突破3000萬,可見引發大家興趣的并不只是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講述了一個被丈夫假戲真做而離婚,還被污蔑為“潘金蓮”的普通農村婦女李雪蓮,堅持不懈十幾年申訴為自己的清白討公道,從鎮到縣,從縣到市,又從市到省到首都,一個農村女性一路與形形色色的男人斗智斗勇。許多人將《秋菊打官司》(1992年)與這個作品相比較,表面上都塑造了執拗的農村婦女,都要的是一個理,然兩部電影的重點和時代精神并不相同:《秋菊打官司》把較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女性人物身上,這個女性是為了自家男人的利益去討公道,一路執拗最終落筆還是回到了一個女性與男性相協調的世界,帶給人們深深思考的不僅僅是女性,還有人性中的法、理、情;而《我不是潘金蓮》則強調了女性與男性的不可調和、分道揚鑣,在李雪蓮身上發生的故事也并不僅僅是農村的事情,為了分房或生二胎而“假離婚”結果弄成了真離婚,因為自身的清白受到了男性污蔑而無法在熟人社會里抬頭挺胸地活下去,女性要為自己去要說法證清白。而在這個討公道的過程中,電影表述的重點則遠遠超越了一個女性主角,直指社會體系,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潘金蓮”這個女性IP也僅僅是一個標題黨的噱頭,喚起關注,試問在電影內與外又有幾個男人是真正關心李雪蓮的清白,李雪蓮也只不過是個引子,社會自身問題才是電影的折射聚焦。還有由經典名著改編的奇幻電影《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和《西游記之女兒國》(2018年),孫悟空是近年來被改編續寫次數最高的中國英雄IP,同樣的還有《西游記》中的女性人物。其中,《三打白骨精》對白骨精的設計可謂煞費苦心,在原著中她武藝高強,變化多端,三觀盡毀,典型一個反派女性人物臉譜,而在電影里卻讓白骨精的形象更加豐滿立體,不僅交代她成為白骨精的前因,還增加了國王一角以點明危害人間的不僅僅白骨精,更洗刷了觀眾的三觀,設定白骨精想吃唐僧肉的后果,是因為她參悟了人性之惡后只想徹徹底底成為一個“價值觀堅定”的永世妖精。這些歷史空間語境下的女性描寫、續寫、改寫和關注,有對傳統女性精神文化的審視和繼承,但更多是對時代賦予新女性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呈現。
三、后情感主義視角下的新理性
社會學者梅斯特羅維奇曾在著作《后情感社會》明確到“當代西方社會學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擬想的情感成為被自我、他者和作為整體的文化產業普遍地操作的基礎……不僅認知性內容被操縱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產業操縱了,并且由此轉換成后情感”。[5]后情感問題的實質是發現由影像轉化而來的情感,“是一種‘類情感’,不是傳統意義上自發的、真實的情感,而是一種新的‘被智識化’‘機械化’,由大眾媒體生產的社會情感形式”。[6]國產IP電影中通過情感空間、社會空間、歷史文化空間三個空間的塑造實現對新女性的凝視,在一定程度上書寫了新時期城市女性形象,具有新時代的審美號召力。然而,細觀這些女性電影形象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卻有極大的局限性,相比電影中光彩亮麗的職場女白領精英,楚楚可人最終得以收獲愛情的小三兒,追求愛情輪回忠貞不渝的仙女,還有男性視野中為自己的貞潔洗白的農村婦女,“新女性凝視”應將視野開闊至社會的廣闊天地。在當下社會變遷女性打工者進城,還有農村空巢老年婦女滯留家鄉,特別是“全面兩孩”政策提出后的女性職場性別歧視等,有大量的女性問題亟待電影去直視,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有待電影去塑造。事實上,女性研究最先也是以一種問題形態出現:女性解放問題、女性自我意識、女性就業等。另外,這些IP電影往往誕生于女性觀眾所熱捧的網絡文學,更加重了作品的女性浪漫和審美想象,甚至一些頗受歡迎的中國式小妞角色塑造更將消費文化描繪得五光十色,將女性暴露在情感空洞的虛偽想象中。《小時代》1~4部卷走高達13億元票房,力證影片所呈現的夢幻性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無論多少嚴厲抨擊作品浮華失真拜金主義價值觀的聲音,作品貌似以女性為中心,實將女性放置在紙醉金迷的虛幻夢境中。這種美和浪漫是危險的,因為在以“視覺”為主導的電影作品中,女性身體是最易引發消費者性體驗“行走”的景觀,“女性作為被看對象有其歷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在當代消費社會的背景中,在形象資源的不斷爭奪中,女性形象的消費者不僅僅是男性,女性本身也是重要的消費者”。[7]因此,“新女性凝視”中對美的感受應是較之以往更理性,是對現實生活中女性形象的更全面的把握和反映,若失去了寶貴的現實主義精神,僅僅靠“虛偽和騙取來的經驗,令人類在現代整體性地損失了真實的、現實的經驗”。[8]這種對新女性凝視的感知應是通過電影中新女性形象表述出來,引導女性粉絲黏合度之高的大量觀眾理性思考,建立對新生活“新感受力”的新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