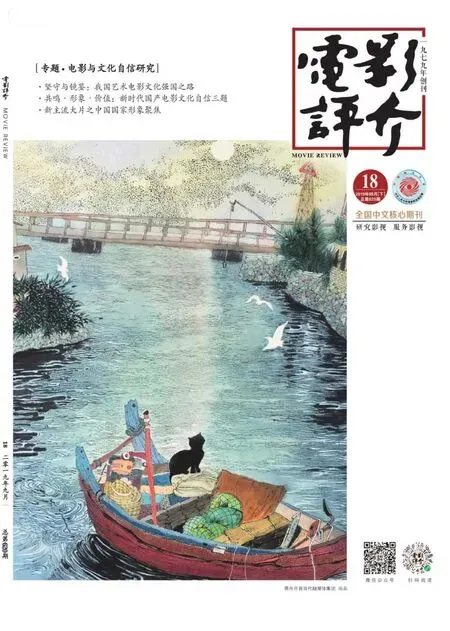后革命時代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的話語建構
——基于電視劇《偉大的轉折》的敘事學考察
蘭東興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央視綜合頻道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展播38集電視連續劇《偉大的轉折》,講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后的那段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歷史。觀看之后讓人明白,這段歷史并未塵封,它已融入中國共產黨的血液。
一、敘事原則:當代背景下的歷史書寫
關于長征題材的影視已有很多,人們關于遵義會議的故事也不陌生,而要用影視作品將一個熟悉的話題再度創作,達到吸引觀眾的效果,需要解決很多問題。
首先,客觀存在的歷史不能改編,卻要實現內容創新。
中國古代對歷史小說創作有精辟的論述,可觀道人在《新列國志敘》中說:“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80多年前召開的遵義會議,其原因和結果,主流歷史已記錄得非常清晰。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和地點、參加會議的人物、會議作出的決議等,都有當事人的回憶和文獻記載,任何文學藝術作品都不能隨意編造。在這部電視劇中,對重大史實、重要人物、無爭議的時間和地點、有定論的觀點,創作者均未作改動,這既是對基本史實的尊重、對主流價值的尊重,也是對觀眾的尊重。
但是,從影視觀眾的心理而言,對自己熟悉的歷史信息往往缺少繼續觀看的興趣,對形成刻板印象的認知也不愿意接受簡單的改動。就影視劇創作而言,不能僅僅停留于對歷史簡單的視覺呈現,對故事、情節和人物關系等的創新,幾乎是其根本屬性和本能的沖動。從敘事學理論而言,認為歷史是對過去發生的客觀事實的表述,表現為文本,客觀事實本身不是歷史。正如克羅齊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敘事,不存在敘事的地方就沒有歷史。在他們看來,歷史的真實看似是事件本身的真實,其實是表述者秉持客觀的態度,恰當運用符號,對發生的事實所做的記錄。正如海登·懷特所說:“敘事的客觀性是通過所有敘事者的關涉物的不在場來定義的。”[1]“不在場”,不是敘事者不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而是對所敘之事保持距離。該劇在文獻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錄之外,補充了歷史人物的活動細節,增添了中共貴州地下黨組織的材料,展現紅軍基層官兵的精神狀態。這不僅沒有削弱該劇的客觀性,沒有妨礙其歷史劇的性質,而且使過去扁平化的歷史書寫變得立體,使過去單線索敘述歷史的手法變成多視角。
其次,不違背對歷史的基本評判,卻改變了敘事重點。
關于話語的意義,敘事學從來都不認為只停留于語義,有的人以說什么或怎么說來判斷,有的人通過話語間性去分析,還有人從敘事的結構和節奏去觀察。既然觀眾知道歷史上召開過遵義會議,該劇就把重點放在引導觀眾去思考為什么召開遵義會議;既然觀眾知道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那就通過詳細敘事陳述為什么能成功召開遵義會議;既然觀眾知道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那就側重于敘述遵義會議為什么能貫徹執行。遵義會議作出的結論則被一筆帶過,語義就蘊藏于敘事的詳略取舍之中。
其三,不改變影視劇的敘事傳統,卻巧妙運用畫面語言。
該劇以湘江戰役失敗開篇,與其說節省了影視劇拍攝戰爭場面的經費,不如說是創作者不愿意把血淋淋的慘像呈獻給觀眾。該劇的創作主旨不是為了表達革命曾付出巨大的流血犧牲,而是指向中國革命的初心、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第一集從中央紅軍轉兵湖南通道開始敘事,接著敘述到貴州黎平后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然后敘述到貴州甕安猴場后再次召開會議,再敘述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確立,黨和紅軍出現了歷史轉折,開啟新的征程。
在以時間為線索的敘事中,觀眾直觀地看到毛澤東的建議從被拒絕到被采納,他從權力的邊緣一步步進入領導核心。而轉換一個視角又會發現:毛澤東的地位變化不只是因為長征中敵我形式的變化所致,關鍵是中共領導層對長期執行的路線在認識上發生轉變,是集體的覺悟。
一方面,無論小說、戲曲,還是影視紀錄片和故事片,都很忌諱創作者直抒觀點。中國古代有一位筆名為“蠻”的評論家在《小說小話》中說:“最忌攙入作者論斷,或如戲劇中一腳色出場,橫加一段定場白,預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某人之實事,未必盡肖其言。”[2]該劇的創作者沒有直接提供觀點,觀眾通過細膩的敘事,隱約體會到遵義會議本身不是黨和紅軍的歷史轉折,而從敘事情節中認識到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成功召開,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付出高昂代價換來的,是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拋卻私心和堅守初心的結果。遵義會議之所以成為黨和紅軍的歷史轉折,是因為在革命的大熔爐中經受血與火的洗禮之后的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另一方面,電影或電視和其他文藝作品一樣,都離不開意義表達。在意義表達時,“表演不是主要的,意義是在上下鏡頭的聯系中產生的,不同的畫面可以組合在一起,并產生隱喻”[3]。該劇充分運用影視畫面的組接來表達意義,畫面中紅軍在遵義會議前后的精神面貌、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言行舉止直接傳達意義,畫面的構圖和組合間接表達意義。該劇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獻禮片,對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紅軍生存狀態的敘述,對中共中央高層領導艱難抉擇的鋪敘,對四渡赤水酣暢淋漓的記錄,“既是一種表達方式,也是對事實的解讀”[4]。觀眾從這部電視劇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錯誤的路線和決策會斷送革命成果,英明的領袖會使領導集體迸發出巨大的能量,健康的組織是決策得到貫徹的保障。
二、敘事策略:國家敘事主導下兼顧民間敘事
正如特里·庫克所言:“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生活在后現代社會里。”[5]后現代社會是價值觀多元的社會,反對一切形式上的元敘事,關注“他者世界”和“他者聲音”。也有人把現在所處的時代稱之為市場時代或“后革命時代”,社會階層分化加劇和社會功能多層化,“文化越來越聽從市場邏輯的支配,而不聽從先驗理論邏輯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對文化市場的掌握權的同時,也在失去對歷史敘事的特殊解釋權”[6]。文學藝術作品表現出多元敘事占據主導地位,敘事策略轉向以市場為主導的消費性書寫,影視劇不乏對紅色文化以消費性視角來建構主題。甚至有人認為“后革命”時代的“后”,一方面是在革命歷史及革命的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之“后”,另一方面是對革命的歷史及其意識形態的反思甚或批判,敘事中的反思抑或批判革命的話語占據主導地位。[7]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發生在80多年前,今天的人們了解那段沒有留下影像的歷史,只能借助于傳說、口述、文獻記錄、珍貴的照片和實物。當年留下的會議決議和實物只是客觀事實;傳說、口述、回憶錄和照片都是用符號對當時事件的意義建構,它盡管在時間上與這部電視劇建構意義有先后,但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創作者在今天制作這部電視劇,不可能只滿足于對那段歷史用光影重現,它表現出來的人物形象、敘述的長征故事其實在建構意義,是當代人與那段往事相遇時的表述。從理論上講,“當人與某個未知的、危險的、以前非常遙遠的東西狹路相逢的時候”“人、地方和經歷總是可以通過書本而得到描述,以致書本(或文本)甚至比它所描述的現實更具權威性”[8]。但是,描述總是帶著時代烙印的描述,即使最接近真相的歷史描述也在建構描述者的主題。
該劇第一個原則就是堅持主流敘事,回應民間多元價值。創作者為何要再現這段往事?再現往事選取哪些片段?用什么線索把片段串起來?這就建構了意義,形成了自己的話語。
該劇在敘事中更多地觀照了民間態度,屏幕上的博古(秦邦憲)等“左”傾路線推行者不再是曾經描述的那樣冷血,他們對紅軍戰士一批批倒下也心痛如絞,他們在革命巨大犧牲之后也在反思和糾正錯誤。從劇中看到毛澤東等偉大領袖積極努力促成遵義會議,還看到曾經的“左”傾路線推行者不斷放棄教條主義,他們都有共產主義信仰,都有同樣純潔的初心。該劇敘述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指揮土城戰斗失敗,還原了真正的歷史,無損毛澤東的形象。中央沒有因為毛澤東指揮一次戰斗失敗而輕易撤銷其職務,足以說明遵義會議作出的決議的嚴肅性,足以證明黨中央嚴格遵守會議決定。創作者淡化遵義會議本身而對會議召開前后詳細敘述,采用了既符合主流價值又符合平民認知的敘事策略,兼顧了消費傳播的大眾心理。
今天已進入后現代社會,對革命的認識置于后革命時代成為常態。中國進入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發展階段,社會高度商品化,社會生活高度娛樂化,社會思想高度平面化,影視作品就不可無視當下的消費風潮。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革命歷史無法改變被消費、想象、改寫的命運,革命的資源與回憶以被改編的方式搬上屏幕不可回避,在消費主義籠罩下就會孕育出“后革命之花”。文化無法完全超脫市場邏輯的支配,不能完全受制于先驗理論邏輯的支配,國家敘事在失去對文化接受者絕對掌控權的同時,就要俯身靠近民間敘事,改變對歷史敘事的傳統策略。近幾年來,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國產大片和電視劇不斷推出,展現出“后革命”時代的影視敘事特點,為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敘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徑。該劇借鑒了很多后革命敘事的歷史影視劇的經驗,仍關注歷史本體,一如既往地在主流意識形態下對歷史文本重構,同時兼顧個人化和民間化的歷史敘述,對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成功召開、遵義會議的決議之所以能得到貫徹執行作出了富有時代特征的敘述,從而賦予了共產黨人新的面孔和遵義會議新的意義。其敘事策略總體上仍沿襲國家主流話語敘事,對偉大的長征堅持嚴肅主題,偉人的氣質、紅軍的精神、蔣介石和地方割據勢力的軍隊的形象基本上定格在傳統的框架之中,觀眾沒有看到顛覆性的形象。又巧妙地融入當下民間話語,改變曾經的“一元化”單一的革命敘事模式,兼顧對革命歷史書寫的社會價值的多元性。在刻畫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時,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紅軍官兵的內心世界用平民視角觀察,從平民的價值取向去體察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情懷,使觀眾在消費性收看中結合自身去感受革命道路探尋的艱辛。
該劇另一個原則就是采用顯性的國家話語與隱性的民間話語的雙重敘事,表現崇高的同時,滿足文化消費時代影視娛樂性。在對遵義會議歷史的處理和表述中與當下的政治建設耦合,真實人物與虛構情節相互交融。
作為歷史正劇,在失去了戲劇化效果的可能之后,世俗化、平民化的敘事至關重要。在觀眾不必牽掛人物命運和紅軍前途的觀看心理下,必須實現劇中人物和觀眾的情感認知雙重同構效應。該劇突出中共領導人物與環境的沖突、領導層之間的沖突、影響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人物內心世界的沖突。這些沖突增加了作品的藝術效果,這些沖突在糾纏中緩解和化解,促成了遵義會議召開,達成了遵義會議決議。這些充滿“后革命”時代的敘事特色,完成了革命歷史崇高品質的再現和“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歷史世俗化的重構。一方面為觀眾重新揭開遵義會議歷史的面紗,另一方面加大了我們探討那個歷史時期黨和紅軍命運、共產黨人初心、長征精神的政治想象空間。
在雙重敘事的彌合下,通過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干部政治理想和個人情感、黨的路線和現實處境疊加,深刻地演繹人情、人性和黨性的關系。這種手法增強了歷史的沉重感,拉近了歷史與當下的距離。在劇中,觀眾看到了殘酷的革命斗爭和尖銳的黨內路線斗爭以及領導人物內心的思想斗爭。該劇塑造的形象都胸懷大局,都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他們只是在探索革命道路時對國情和革命形勢認識上的不同,他們都可敬可愛,都有溫度。在宏大的敘事中不失微觀敘事,在國家敘事不失民間敘事,在表現崇高時不失世俗觀照。黨和紅軍曾經發生的歷史不容虛構,觀眾對結果已無懸念,但是在微觀敘事上強化各種沖突的展開和化解,照顧到了媒介消費時代的審美趣味。
三、敘事技巧:外視角敘事中包含內視角敘事
選擇以遵義會議為電視劇題材,一開始就使創作者面臨四個難題:第一,觀眾對基本史實清楚,結果幾乎失去懸念;第二,只能做成歷史正劇,不可戲說,創作空間小,增加故事性和趣味性不容易;第三,以會議為核心要素,沒有戰爭片宏大的場面和視覺沖擊力;第四,將已有定論的歷史以影視的方式呈現,需要突破卻又存在風險。
為了克服這四個方面的困難,該劇在敘事視角上作了精心設計。視角被西方批評家認為是敘事的規定性特點,[9]因為處在故事與讀者之間的是敘述者,他敘事的視角決定著講什么和讓人怎么看。
該劇的題目為“偉大的轉折”,轉折點是遵義會議。轉折只有在前后比較中才能充分體現。所以創作者沒有急于對遵義會議直接記錄,而是從紅軍在湘江戰役失敗后開始敘事。以此作為敘事的起點,一是因為稍有歷史知識的觀眾都知道最終結果卻未必知道細節,通過增加細節以滿足觀眾的心理期待;二是通過突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和“左”傾路線推行者之間的矛盾,從而形成觀眾的情感和劇中殘酷的生死存亡之間的對立。中國古代小說敘事有“百折千回法”,讀者越是急于了解就越是故意延宕,令人心癢難熬。該劇在講述中央紅軍遵義會議之前那段慘痛歷史的時候,創作者以觀眾之外的視角敘事,刻意使用非常緩慢的節奏:紅軍湘江戰役后從8萬多人銳減至3萬人、李德無視紅軍將士的犧牲仍固執己見、博古沒有勇氣沖破教條束縛而面對現實一籌莫展、毛澤東機警睿智卻沒有決策權、周恩來和朱德等紅軍將領明知不可為而只能為之、廣大官兵慷慨赴死卻做著無謂的犧牲。觀眾希望劇情快速推進,而鏡頭卻幾乎滯塞凝固。這種刻意制造出的劇情和觀眾的心理在觀劇的過程中形成沖突,使觀眾既想跳出劇情卻又深陷劇情之中。觀看劇情的心里憋屈與中國革命這段憋屈的歷史奇妙地達到高度統一,由此而使觀眾在昏沉的畫面觀看中深刻理解革命先輩在危急時刻的艱難抉擇。當劇情推進到紅軍占領遵義城的時候,觀眾的心情如釋重負,期待電視劇最核心的部分出現。當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創作者又敘述土城戰斗失利,毛澤東再次陷入輿論漩渦,觀眾對結果又產生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就是創作者站在觀眾之外特意設置的。
評判一部影視作品是否為歷史正劇,主要根據兩條標準:必須忠實于客觀事實;對待歷史必須用嚴肅的態度。嚴肅的態度本質上是敘事者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又是通過敘事來實現的,表現為劇中當事人看待事件的立場、處理人物關系的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手段等。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持否定態度、彭德懷拒絕接受最高軍事指揮官李德決定時怒罵、劉伯承提醒紅軍戰士砍伐當地老百姓楠竹后記住留下銀元、第三軍團參謀長鄧華犧牲后許多中央領導都眼含淚水……這是長期以來國家敘事的立場,具有外視角敘事特征。博古聽到各軍團上報湘江戰役犧牲人數后痛哭、張聞天和王稼祥等人不遺余力促成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也不能確定最后的結果……這是今天民間敘事假設身處其中的歷史描述,具有內視角敘事的色彩。
該劇最核心的內容是遵義會議,采用外視角敘事便于調度觀眾情緒。在講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歷史時,故意延宕情節以蓄積觀看的期待心情,一方面消解觀眾對故事性的挑剔,另一方面也可增強觀眾對結果的探知欲望。觀眾尋求劇情答案的急迫心情和對革命前途焦慮的情感相互交織,模糊了影視劇與客觀歷史的界限,情緒隨著劇中主人公的態度、人物之間關系的微妙變化而起伏。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穿梭于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周恩來游走于博古和毛澤東之間,朱德糾結于最高軍事長官李德和廣大紅軍將士之間,博古徘徊于黨員初心和當前處境之間,觀眾也漂游在電視創作者營造的藝術氛圍與自己觀看電視劇的現實環境之間。把對會議作出決定的敘述轉變成對會議之前核心人物關系的敘述,會議的決定因此如水到渠成。觀眾的歷史知識儲備已經知道遵義會議的基本內容,通過該劇了解會議召開前的細節,獲得填補信息短板的滿足感。
在外視角敘事中,又總能看到內視角敘事的影子。每一個中共高層領導都在經受靈魂的拷問,都在堅守黨的組織原則和直面殘酷現實的矛盾中掙扎。中央政治局書記博古尊重集體意見,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建議在會上總結湘江戰敗的問題。因為張聞天與周恩來極力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博古服從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人意見,同意更改議題。周恩來深刻剖析自己執行“左”路線的錯誤,彭德懷直言不諱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損失,張聞天和王稼祥客觀回顧過去,朱德正視目前的嚴峻形勢,劉少奇、陳云等同志都把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放在第一位,他們立體塑造了共產黨員的群像。作為電視劇,不可能把這次會議轉化成宏大場面;作為尊重歷史的電視劇,不應該杜撰違背基本史實的人物沖突迎合觀眾的淺層次心理需求。創作者用當代眼觀重新審視這段早已定性的中共黨史,用內視角書寫人們熟悉的這段中國革命史中人物的思想情感,開啟了歷史與現實、老一代革命家和當代人的對話。在對話中重溫歷史、審視歷史,并從對歷史的重溫和審視中實現觀劇的娛樂、信息獲取、思想引領等傳播效果耦合。創作者把觀眾帶入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之中——遵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并取得具有轉折意義的結果,充分說明當時黨的政治生活依然健康,黨的集體初心仍在。這種敘事技巧符合歷史,又沒局限于已有的歷史敘述框架。
遵義會議之后的歷史,今天很多人只知道黨和紅軍有了毛澤東的領導,中國革命從此轉危為安,但是并不清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確立還經歷了一個過程,更沒有冷靜思考遵義會議的決議能夠得到貫徹的深層原因。該劇詳細地講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確立,又經歷了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階段。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確立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總司令朱德與政委周恩來才是真正的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后下決定的負責人。毛澤東策劃的四渡赤水擺脫蔣介石和軍閥“圍剿”,他的軍事才能更加彰顯,在周恩來提議下,博古欣然同意由毛澤東領導全局。這在表面上是外視角敘事,其實在引導觀眾以內視角去思考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實現轉折的歷程。
今天,我們能夠從電視劇中看到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形成有一條清晰的政治邏輯。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戰役失敗,黨和紅軍需要從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力挽狂瀾,毛澤東經過革命洗禮成為黨的核心是時代的選擇。毛澤東指揮土城會戰失敗,中央沒有因為一次戰斗的損失而改變遵義會議決議,最終成就了毛澤東軍事指揮四渡赤水的杰作,觀眾能夠從中真切理解復雜的形勢需要靈活應變,更能從中深刻理解黨的決議的嚴肅性。在這部電視劇中,觀眾不僅看到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而且從該劇細微的鋪陳中體會到這一結果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從未動搖的宗旨作思想保障,離不開黨的組織原則作制度保障。“敘事的超真實”才是影像創作者追求的真正的“真實”。[10]
對每一位中共領導人細膩的敘述,觀眾仿佛感受到共產黨人一直堅守初心的溫度,從而認識到遵義會議成功召開是一個必然結果,間接地給出了遵義會議決議之所以得到貫徹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