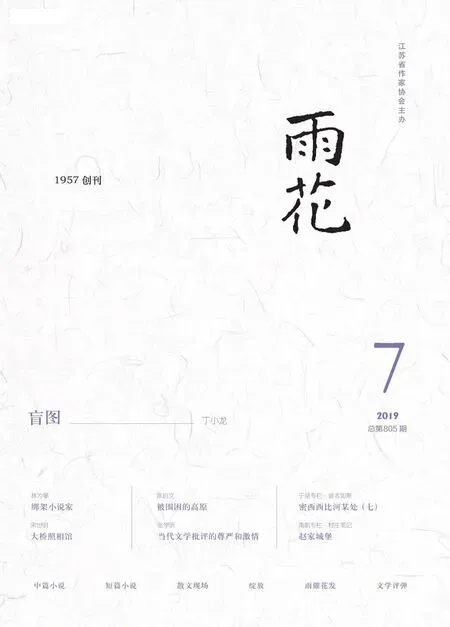誰的鐘表壞了?
——讀范小青短篇小說《現在幾點了》
子 川
現在幾點了?尋常語境一句尋常問話,被提溜起來做了小說題目,竟生發出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張力。2019年第1 期《雨花》雜志尚未寄至家中,我就在主編朱輝的微信上讀了小說《現在幾點了》的電子版。線上匆匆讀過,通過微信轉給了幾個文友,事情似乎還沒做完,就又把小說下載到電腦,用WORD 文檔打開,再細讀一遍。小說的故事看似簡單,讀了卻有點化不開。真所謂篇制不長,張力不小。
小說用“現在幾點了”這句話做引子:
“老人坐了下來,手臂擱在桌子上,她以為他要開始訴說自己的病情,等了一會兒,老人說了一句,現在幾點了?”
“她回答的時候,看了老人一眼,她是有經驗的,所以已經有了一點預感。果然,老人又說,現在幾點了。”
現在幾點了?明明是一個關于時間刻度的問題。梅新作為一個有經驗的醫生卻“基本判斷出來了,老人其實并不是在提問,或者說,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問什么。”
“阿爾茨海默癥。”梅新醫生以確診口吻表述老人的癥兆。確實,阿爾茨海默癥會導致病人出現時間定向障礙。“老人指著自己的胸口,明天我這里有點悶。”“前天會不會下雨。”很顯然,“時間概念已經完全混淆或者丟失了,”根據醫生梅新的判斷:“這至少是到了中期的病癥了。”
小說開始于對時間刻度的詢問,然后又通過提問者的“阿爾茨海默癥”消解了詢問的意義項。然而,時間作為小說揭示的主題,卻始終在小說情節線中顯現,帶著一些不太明晰的意義項。
“老人皺著眉,十分焦慮地說,我來不及了,我來不及了,我沒有時間了。”一個八十歲的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有此癥兆,不奇怪。在語義項層面,“沒有時間了”符合一個八十歲老人的邏輯。
接下來,護士小金也為時間糾結:“她們正說著話,小金的手機響了,小金一看來電,還沒接電話就叫嚷起來,哎哎呀,我差點忘了——哎呀呀,現在幾點了?”
這還不算,小說中輪番出場的人物,幾乎都在時間節點上打絆兒:
“排在第一個的是一個面帶怒氣的中年男人,他正在嚷嚷,醫生也不看看現在幾點了,跑到外面瞎聊天,浪費我們時——”
“她趕緊說,讓我先看吧,我馬上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哇啦哇啦哇啦——我時間來不及了——”
“那婦女說,你不是心疼時間嗎,你要是死了,時間就全沒了——她忽然叫喊了起來,啊呀,現在幾點了?啊呀呀,我不量血壓了,我來不及了!”
“周醫生很懊惱,一直說,怪我,怪我,那天我約了要去看房,時間太急了,我沒有仔細看,我那天時間來不及了,我要是時間來得及,不會這樣粗心的。”
“老太太在旁邊嘀咕說,你這樣的,不用來麻煩醫生,自己到藥店拿醫保卡就可以了,來醫院還耽誤別人的時間。”
小說讀到這里,才知道原來作者想說的并不是“阿爾茨海默癥”,或者,“阿爾茨海默癥”只是一個影子。影子周遭,滲透的全是時間,時間。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環境下,時間,時間。仿佛冬日危機,四處呈現。
漢斯·梅耶霍夫曾經說過:“問人是什么,永遠等于問時間是什么。”(《文學中之時間》)的確,生命在時間中展開,生命其實是一些不同的時間刻度,而且是一些可以消耗殆盡的刻度。小說中的“現在幾點了”,不再是一句簡單問話,它似乎還多出幾個意義項:時間不多,已進入臨界狀態;時間所剩無幾,再不什么什么就要來不及;一種與時間相關的焦慮普遍存在著。
如果用四季劃分生命的時間刻度,冬日應是生命的最后一個時間段。現在幾點了?在一個“阿爾茨海默癥”患者那里,語義層面無意義,但在生命周期上,這一提問的潛在意識卻是對所剩無幾的時間的焦慮。
因此,一個小說未提及的字詞出現了:時間焦慮。小說中這樣一些對話,讓人時時感受到這種焦慮:
“老師說,喔喲,張阿爹你急得來,急著去上班啊?”
“張阿爹雖然咳得厲害,嘴巴仍然蠻兇,說,難道不上班的人,就不要時間了嗎?”
“老師說,好了好了,不和你說時間了,人都這么老了,還時間時間的——”
“脾氣不好的男人又不高興了,說,你時間來不及?就你忙?現在誰不忙?再忙也有個先來后到,不要不講規矩。”
再看看這組對話:
“梅新說,那個,她急著量血壓,要去趕車?”
“趕個魂車,趕火葬場的車吧——她要買彩票。”
“咳嗽的老人一邊咳嗽一邊還忍不住插嘴說,買彩票急什么急呀,到晚上也可以買的。”
結論是:“她們都覺得自己的時間很緊。”
梅新醫生之所以從大醫院降職到社區醫院,也與時間有關。她要去接外地過來的妹妹,而她先生的時間概念有瑕疵,據她估算“妹妹大約八點二十左右到達地鐵出口。可時間已經八點十分,丈夫居然還沒有出門,”于是,她只好自己請假去接人,而偏偏這個時間里,出了醫療事故。小說寫到“丈夫的手機里卻傳過來電視機里的聲音,丈夫‘咦’了一聲,隨口說,現在幾點了?”
“現在幾點了?”在這個短篇小說中被不同的人重復使用。
小說中,時間焦慮并非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的單一癥候,當小說中的人和事,都與時間掛上鉤,時間焦慮似乎已經是一個全民性癥候。于是,小說并未提及的似乎是全民性的時間焦慮癥,顯現在讀者眼前,在讀者心中引起震撼。
這病始發何時?病根是什么?小說家沒有說。小說家不是醫生,雖然她寫到了醫生與病人。這里留有大片空白。這里的空白由讀者自己去填寫。
筆者在讀小說時,突然閃回幼年的生活。那時,大人們經常“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輕輕松松謀生活。如果要說當時的人不如今天的人進取,似乎也不讓人信服。別人且不說,僅我父親早年也就是做個三分利的小生意,竟可為八個子女蓋下八處房產,用時下流行語去形容,還真是夠拼的。可他依舊能癡迷于琴棋書畫,悠哉游哉過日腳。后來,時代所迫,琴棋書畫玩不起來,他干脆給我二哥四個小孩起名:張琴張棋張書張畫。回憶起來,當年并非他一個人如此,印象中,街坊鄰居,大都這樣從容、寫意地生活著。
為何到后來就一個個活得疲于奔命了?不好深究。應當還不是所謂“現代化并發癥”,與現代不現代似乎毫無關系。去國外旅行,看瑞士、丹麥、芬蘭這些國家,周末商場無一例外關門打烊。街面上,許多地方看不到人,唯有咖啡館、休閑場所滿座。時間上,這些國外人群與我們同處一個刻度,空間上,我們前人與我們同處一個緯度,為何他們都能很悠閑地生活,我們就不能?
難道真是我們記載時間刻度的鐘表出了問題?
小說安排了兩個似夢非夢的夢境,來討論鐘表。應當說這是小說最值得注意的細節。
“老人重新坐到了梅新的桌子前面,跟梅新說,醫生,現在幾點了?我的表壞了,時間找不到了……”這似乎是寫實。只是后來,“老人從口袋里取出一張紙,塞到梅新手里,說,時間在這里。”讓人覺得有點夢幻。再后來,“梅新正想把那個奇怪的紙單掏出來看看到底是什么,就聽到有人咳嗽了一聲,把她驚醒了。”
“原來是個夢。”卻好像又非夢。
一個周末,在家里整理衣物的梅新,無意中在很久未穿的舊衣服口袋里發現“一張修理鐘表的取貨單,上面有鐘表店的店名和地址:梅林鐘表行——梅長鎮梅里街十一號。”
“她想起了那天中午的那個夢,這明明是夢里的一張紙單,怎么會真的出現在口袋里?”
接下來是梅新回家鄉梅長鎮,去看望父親,去找梅林鐘表行。“正如她所猜測,梅里街已經不是原先的梅里街了,雖然門牌號還都在,但是十一號不再是鐘表店,而是梅里街居委會。”
遇到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鐘表行所在。有一個大叔似乎認識她,但一說話她又覺得不對,“那大叔說,好久沒見你回來了,好像你父親去世以后,你就沒有回來過?”
“梅新忽然意識到,這大概又是一個夢,夢是荒誕的,她應該從夢中醒來。”
其實,似夢非夢只是想用一種模糊方式來表達:表壞了。表壞了,沒有修好或修好了沒能取回。
什么表壞了?這讓人們在時間面前變得不那么對付。而事實上人的生命始終與時間相關,時間刻度不對,人的生存質量與生活品味就都出了問題。
或許與社會價值取向有關。記得當年有一個豪邁口號:“超英趕美”。這對中國人影響極大,對我個人也如此,后來發現并不是我一個人,我們這代人都有“躍進”情結。到了新時期,許多東西都回撥了不少,唯獨這“躍進”勁頭絲毫不減,只不過“躍進”方向與指向的內容有不同。這時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時間與金錢,效率與生命,劃上等號,等號后的答案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這些歷史背景或許與今天的時間焦慮有點關系,應當還不是病根。病根應該出在文化上。如同自然植被被破壞會造成沙塵暴與霧霾,文化植被遭到破壞,社會環境自然就出現若干的文化癥候。時間焦慮是其中一種。
有一個叫俞敏洪的大V 說:焦慮的根本原因,是你守不住自己的節奏,太急于收到回報,看到改變。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在于,他把全部看成了個別。如果是一個人的焦慮或一部分人的焦慮,他可以這么說,一旦所有人都焦慮,那就不是個人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顯然,文化問題這口子不能開,說透了需要著一本大書。不過,從前人的價值觀那里,我們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那么,文化上的問題又出在哪里?《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管子的“四民”劃分,與后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樣,都是在價值取向上向務虛層面傾斜。為何把最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商”排在末位?為什么要去強調“百無一用”的讀書人?這里其實有一個精神高于物質的價值本旨。而這本旨始于“以人為本”的理念。的確,人如果沒有精神了,人還是人嗎?
以人為本,還是以別的什么為本,一定意義上直接影響人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還是《管子》,“霸言”篇中,管仲對齊桓公陳述霸王之業,有這么一段言論:“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以人為本,就是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重視人格和個性的發展。古人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于是我們在能讀到的幾乎所有歷史典籍中,讀不到“商”人什么事,包括那些掙快錢的人,工于應用的那些人。不能說社會發展與進步與他們沒有關系,但最終,錢與物質都是生命的附加值,人的尊嚴、人格和個性才是價值本身。今天社會價值取向怎樣(不展開評說)只看所謂“上流社會”有多少老板即知。這里可以把大V 的話用在這里:“太急于收到回報,看到改變。”當價值取向傾斜于物質至上,人們怎么能不急功近利?因此,別太強調致用,男女老少,都務點虛行不行?
事實上,人的尊嚴和價值,人格和個性發展,都不是金錢所能換取。當“一切向錢看”了,當“時間就是金錢”了,確實有一個鐘表壞掉了。“現在幾點了?”是小說中的提問,小說外也有一個令人心顫的疑問:“誰的表壞了?”
還是回到小說。根據醫生梅新的判斷:“這至少是到了中期的病癥了。”
還是那個“阿爾茨海默癥”患者。“老人重新坐到了梅新的桌子前面,跟梅新說,醫生,現在幾點了?……你能不能幫我修修表。”
醫生,能不能幫我們修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