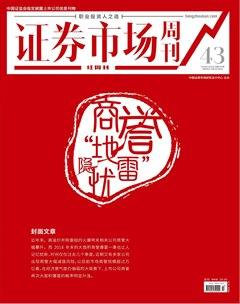恒譽環保大客戶依賴現象明顯疑為上市“人為創造”好業績
胡振明
濟南恒譽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恒譽環保”)原本是一家在新三板掛牌的有機危廢處理設備企業,其從新三板摘牌后于近日披露了在上交所科創板上市的招股說明書(申報稿),擬募資約6.33億元。
招股書披露,恒譽環保報告期內(2016年至2019年1~6月)大客戶集中度非常高,對前五大客戶銷售占其當期主營業務在報告期內基本都處在100%的情況,而在大客戶基本保持不變的背景下,恒譽環保卻在近一年半時間里,營業收入規模和利潤業績卻出現了大幅增長,讓人對其經營數據的合理性產生興趣。
大客戶依賴現象明顯
招股書披露,恒譽環保在2006年成立之時的注冊資本為100萬元,經過10年時間的發展,公司到2016年時的營業收入已經達到3812.79萬元、凈利潤529.84萬元。從其十年發展歷程看,這十年里的發展還是相對平穩的,并未出現明顯的大起大落。然而到了2016年以后,營收增速“突然”加快,營收規模由2016年末的0.38億元突然增至2018年末的2.52億元,年度同比增速分別達到了188.61%、38.71%和375.59%。
“報告期內公司主營業務收入持續增長,主要受益于國內環保政策趨向嚴格所帶來的相關下游行業需求持續穩定增長,以及公司在研發、生產、管理等方面的累積優勢的爆發。”對于近兩年經營規模的大幅增長,招股書給出的解釋看似合理,但理由似乎有些寬泛,因為招股書披露的相關信息與該解釋還是出現了明顯矛盾。
《紅周刊》記者發現,恒譽環保在2016年時還只有一名客戶順通環保,而到了2017年也不過五名客戶,其中向前兩名的銷售占比超過了88%。2018年,客戶數量雖然超過了5名,但在2019年上半年,又回落至5名客戶。報告期內,順通環保穩居第一大客戶,其為恒譽環保營業收入的增長提供了較大的推力,各年對其銷售收入占恒譽環保當期營業收入的100%、66.07%、64.45%和66.84%。由此不難看出,恒譽環保對順通環保是存在明顯大客戶依賴的。
一般情況下,在企業發展初期,經營上高度依賴大客戶對企業的快速發展是利好的,但隨著企業發展的逐步成熟,若仍依賴某一大客戶就存在一定劣勢了,因為大客戶的采購變化情況往往決定著公司的業績變化,而這一點從恒譽環保毛利率變化也體現出來。報告期內,公司主營業務綜合毛利率分別為57.73%、53.22%、46.12%、44.18%,呈逐年下滑趨勢。對此,恒譽環保在招股書解釋稱:“公司主營業務綜合毛利率顯示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主要系公司重點發展大客戶,對于重點項目或大型項目給予更高的資源和成本投入所致。”
除了經營上過于依賴大客戶之外,恒譽環保的供應商集中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報告期內,恒譽環保向前五名供應商的采購額占比達到了73.44%、71.47%、48.42%和60.43%,尤其是前兩大供應商采購占比明顯高于其他供應商。值得一提的是,委托外協供應商加工的定制設備及定制件金額占公司采購總額的比例也分別為89.91%、79.22%、80.82%及90.65%,這意味著加工并非恒譽環保的主要業務能力,主要是通過建造合同業務獲得收入,而這一點就必須高度依賴于供應商的支持。
以上種種跡象說明,恒譽環保目前在業務的獨立性及其能否獨立發展方面仍偏弱,假如IPO能順利完成,并投入募資用于擴大經營規模,則目前的主要客戶及主要供應商結構情況能否適應其規模的變化是值得深思的。而更為重要的是,分析其經營業績持續增長的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收入數據,可發現這些數據存在為沖刺上市而“人為創造”業績的嫌疑。
有“人為創造”好業績之嫌
恒譽環保的主要產品為工業連續化廢輪胎裂解生產線、廢塑料裂解生產線、污油泥裂解生產線及危廢裂解生產線等有機廢棄物裂解裝備,然而其營業收入主要是建造合同收入。報告期各期,建造合同收入分別為 3760.68萬元、5236.44萬元、25050萬元及13334.35萬元,占各期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98.63%、99.01%、99.59%及99.84%。
讓人感到的蹊蹺是,恒譽環保的營業收入在報告期的后半段突然大幅增加,特別是臨近IPO申報的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在客戶數量沒有明顯增加下,營業收入卻呈現出數倍增長,那么,如此突增的數據是否合理呢?
招股書披露,2019年1~6月,恒譽環保的營業收入為13356.13萬元(如表1所示),由于今年4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從16%下調至13%,從月均收入的角度并結合各月份的稅率情況,可以測算出其銷項稅額有1936.64萬元,進而也推算出公司2019年上半年含稅營業收入達到了15292.77萬元。
表1 營業收入相關數據(單位:萬元)

同期的現金流量方面,2019年1~6月“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有3664.92萬元,與此同時,期末預收款項4092.98萬元相比期初的10932.53萬元減少了6839.55萬元,這相當于以前期間流入的現金流量在本期確認了收入,屬于本期收入相關現金流量。因此,綜合起來,2019年上半年有10514.47萬元現金流入與營業收入相關。將現金流入的10514.47萬元與同期含稅營業收入15292.77萬元勾稽,有4788.30萬元含稅收入沒有收到現金,理論上,這將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為應收款項有相同規模的增加。
可讓人奇怪的是,2019年6月末恒譽環保應收賬款為2814.94萬元,同時還有壞賬準備148.15萬元,沒有應收票據,幾項綜合結果相比期初相同項目的合計金額不但沒有增加,相反還減少了2185.83萬元。在一增一減下,可以發現有6974.14萬元的含稅營業收入既沒有獲得現金流入,也沒有體現出相同規模的新增應收款項變化。
同樣的邏輯,我們進一步分析2018年的營收數據,可發現這一年數據若從財務勾稽角度看,偏離值就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正常的。
在2018年,恒譽環保的營業收入有25151.99萬元,考慮到該年5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從17%下調至16%,結合平均每月營業收入情況,可知當年含稅營業收入有29260.15萬元。同期,35253.27萬元“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在沖抵預收款項增加額8587.79萬元之后,與營業收入相關的現金流量達到了26665.47萬元。同時,2018年年末應收賬款及壞賬準備合計5148.93萬元比上一年年末增加了2335.29萬元。將現金流量和應收款項結合起來,理論上能夠支持29000.76萬元含稅營收,與真實的29260.15萬元含稅營業收入相比,僅差了259.39萬元。
同樣的分析邏輯,2017年營業收入與相關財務數據之間的差異也是不太明顯的。
既然報告期內2017年和2018年的營業收入都能得到財務報表相關數據的支持,可為何唯獨臨近招股書申報稿披露的2019年上半年卻出現了差不多7000萬元數據異常呢?如此異常情況,若恒譽環保不對此補充披露更多相關信息,則很難讓廣大投資者排除其有臨時“人為創造”好業績的嫌疑。
成本數據存在異常
進一步測算并分析恒譽環保的營業成本、存貨成本與采購的情況,還能從另一個方面印證其為達到IPO目的而“人為創造”好業績的嫌疑。
2019年1~6月,恒譽環保采購總額為5303.24萬元(如表2所示),比同期主營業務成本當中的直接材料金額6931.78萬元少了1628.54萬元。也就是說,上半年采購并沒有滿足同期的生產經營所需,還需要動用庫存原材料,即今年6月末的庫存情況理論上應該比期初(即上一年年末)有相同規模的減少。
表2 營業成本與存貨成本相關數據(單位:萬元)

6月末的存貨中,原材料有549.54萬元,跟期初447.51萬元相比出現了102.03萬元的增長。這種情況說明,為達到庫存減少目的,則存貨中其他項目的原材料成本理應出現相應的減少才合理。
招股書披露,2019年6月末的存貨當中,半成品有434.97萬元,而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結算資產有7640.85萬元,兩項合計有8075.82萬元,跟期初相同項目的合計金額相比較,增加了5055.08萬元。雖然招股書沒有披露這兩個存貨項目所包含的原材料成本是多少,但考慮到已完工的產品占絕大部分,并且成本結構跟主營業務成本基本相同,因此,《紅周刊》記者采用直接材料占主營成本的比例93.12%來測算這兩個存貨項目所包含的原材料成本。測算出,新增的5055.08萬元存貨中包含了4707.29萬元的原材料成本。
考慮存貨成本的變化之后,結果就很明顯了,理論上6月末的庫存應該比期初相應減少1628.54萬元,可實際上存貨當中的原材料卻出現了增長,而且半成品、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結算資產也出現了增長,一減一增下,采購與營業成本、庫存成本之間出現了6437.86萬元的差異。
當然,上述分析中只是采取了估算的方法,出現一定的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如何,所得到的估算結果不應該跟實際披露的數據有太大偏差才合理,可實際上基于慣例及招股書披露的信息分析可發現,數據偏差竟然超過了6000萬元,很顯然,這么大的偏差是需要解釋的。
值得一提的是,《紅周刊》記者用同樣的方法分析2018年的采購與成本數據,并沒有發現有太大的差異。在2018年,恒譽環保采購總額13863.48萬元比同期主營業務成本的直接材料12413.16萬元多1450.32萬元。同時,2018年庫存中,存貨當中的原材料減少了28.71萬元,半成品、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結算資產合計3020.74萬元,比上一年年末增加了2039.78萬元。在此也用直接材料占主營業務成本的比例91.97%來估算這兩個存貨項目增長額中包含的原材料成本,可知增加了1875.99萬元。綜合起來,庫存變化中涉及的原材料部分合計增加了1847.28萬元。這跟上述1450.32萬元相差僅有396.96萬元。若考慮估算方法中可能產生的誤差,這個規模的差異還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用同樣的方法分析2017年相關數據,也僅存在14.33萬元差異。
綜合2017年至2019年上半年分析結果,可發現前兩年的差異都是比較小的,而到了申報招股書的2019年上半年,卻出現了數千萬元的差異,而其上半年的營收也出現異常,如此的“巧合”,還是希望恒譽環保方面能夠在上市之前給出合理解釋。
令人疑惑的異常支出
除了上述疑點外,《紅周刊》記者進一步分析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的采購數據,發現也有異常。
恒譽環保主要采購裂解器主框架、取料裝置等定制設備及定制件,2018年的采購總額為13863.48萬元(如表3所示)。結合2018年5月1日增值稅稅率從17%下調至16%情況,以平均每月采購額來測算進項稅額,可知全年的含稅采購總額有16127.85萬元。
表3 采購相關數據(單位:萬元)

對于這個規模的采購,恒譽環保支出了多少錢?財務報表顯示,2018年“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為18713.59萬元,比同期含稅采購額多出2585.74萬元。在此可看到,所付現金比含稅采購額多,這種情況說明除了本年度采購所需款項之外,還償還了以前年度所欠賬款。若是如此,應付款項、預付款項的金額變化必有相應的體現,可能是應付賬款出現相同規模的減少,或預付款項有相應的增加。
然而,2018年年末應付賬款1009.82萬元相比于上一年年末而并沒有明顯的變化,上一年年末的應付賬款為1008.34萬元,也就是說,2018年應付款項增加了1.48萬元。那么,預付款項又是否有大規模的增加呢?
財務報表顯示,2018年年末預付款項945.04萬元的確比上一年年末的113.76萬元增加了不少,但是此處所增加831.28萬元仍遠遠不足同期含稅采購總額與現金流量之間的2585.74萬元差額。綜合起來,2018年恒譽環保除用于采購支出外,還多支出了1755.94萬元現金。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在建工程等項目的增加,沖抵在建工程轉入固定資產或者轉入無形資產等各項目之間的結轉之后,增加額與同期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大致相同,并無太大出入,這一點也不太可能對上述采購分析結果造成較大影響。
同樣的分析邏輯,可以發現2019年1~6月的采購數據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含稅采購總額6072.21萬元之下,上半年“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有4439.21萬元,同時應付賬款增加了1990.45萬元,兩項合計達到6429.66萬元,已經超過同期含稅采購總額。若進一步考慮到預付款項比期初減少的637.75萬元影響,則2019年上半年多支出了995.19萬元現金沒有獲得相應采購。
雖然我們可以考慮到2019年上半年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長期資產購建對現金流量、應付款項可能形成的影響,上述近千萬元的差異將縮小至數百萬元,基本可認定2019年上半年采購數據是合理的,但2018年多支出的1755萬元卻是缺少相應數據支持的,這一點還是需要公司做出進一步合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