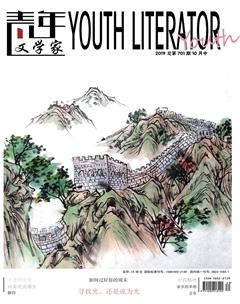家鄉的米粉
作者簡介:馮三四,本名馮詩斌,廣西博白人,研究生學歷,作家,詩人。
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家鄉水。
每當觸碰故鄉這個柔軟、纏綿的話題時,相信很多人滿腔都是割舍不了的思鄉情愫,因為那里的親人,那里的山水和那里的草木。對我來說,還有一樣東西深深地牽著我的思鄉情愫,那便是家鄉的味道——米粉。
小鎮窩在兩座大山之間,呈東西走向,只有兩條街道,分別長500米,一條是公路,自古攤販擺滿路邊;另一條是背街道路,居民家家戶戶開門做買賣。
印象中,最初只在街道中部有七八家粉店,每間粉店面積不過20平米,品種不外乎是叉燒燙粉、鮮肉煮粉、卷筒粉。隨著時代發展,現在的米粉店已遍布小鎮的街頭、街中和街尾。
小鎮每隔三天是一個街日,以前客流不多時,米粉店街天才開門,后來因來往的行人增多,生意火爆,便天天營業。而店主們跟著掙脫了土地的束縛,搖身變成小市民,專門干起了賣粉的營生。
每天早上五點,小鎮還在夜色中沉睡,米粉店的老板們便忙碌起來了,劈柴、生火、熬湯、備菜,菜刀剁砧板的聲音響徹小鎮一隅。老人負責生火和洗鍋刷碗,年輕人負責劈柴、蒸粉、切粉,大家分工合作,然后虔誠地等待客人們的到來。
家鄉的米粉分兩種,一種是湯粉,一種是卷粉。湯粉是把蒸好的粉塊用刀切成條,再二兩或三兩地放到碗里,配上肉菜,澆上骨頭湯,再添點蔥花和青菜,一份可口的佳肴即可端上臺面。熱天時吃得滿頭大汗,冬天時吃得渾身暖和。
至于卷粉,就是把米糊勻到一面竹篾里,放進一個蒸鍋,蓋上罩子,待蒸熟了以后,再撒上叉燒等配料,卷成條狀,最后從外面澆點醬油和山茶油,便可以大快朵頤了。卷粉的配料除了肉末,通常還有豆芽和花生,入口滑溜而香脆,深受鄉親們喜愛,也引來過路游客駐足。經常有外地車輛路過小鎮時,一群人呼啦啦擠進粉店,吃個痛快才腆著肚子離去。
我時常在想,家鄉的米粉為什么總讓人念念不忘?理由大概是一個“土”字。它是由一群土生土長的人,用土生土長的大米、泉水和菜蔬,通過土辦法精制而成的。比如說,山外的餐飲業早就用上了煤氣和電,唯獨家鄉的米粉店至今保留著用木柴當燃料的傳統,難怪有人說“柴火蒸熟的米粉,味道更地道”。
不論你是誰,只要走進家鄉的米粉店,店主就會滿臉堆笑地迎上來,用家鄉話熱情地詢問你想吃什么粉。如果你聽不懂,他們會改用蹩腳的普通話跟你交流,話不一定好聽,但粉一定包你滿意。在你站櫥窗外等待叫號的間隙,會看見慈眉善目的老人坐在灶前,拿著竹筒鼓著腮幫朝著爐子吹風。為了一碗粉,全家齊上陣,這大概是家鄉米粉店才有的特色。因為在他們眼里“顧客就是上帝”,他們得全心全意做好了,才對得起那碗粉的錢。
家鄉米粉給我的印象,是五六歲時留下的。一天,爺爺說我頭發長了,要帶我上街理發,父母考慮再三終于同意了。老家離鎮上有七八公里,那年月還沒修通公路,爺爺將我背一段走一段。
爺爺知道我天生頑皮,不肯老實聽從理發師的調度,于是想到一個妙招:來到街上,帶我直奔粉店,買了一碗三兩的米粉,然后爺孫倆津津有味地分著吃。那是我第一次嘗到米粉的美味,理完發回家前又央求爺爺買了一碗米粉。
這件事讓爺爺嘆為觀止,過后逢人就說:“我的孫子這么喜歡吃米粉,將來是要走出這山溝溝的。”意思是說我志向高遠,不會甘心守著家鄉的一畝三分地。
確實,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家鄉的一碗米粉一度成為孩子前進的動力。比如,有些大人在鼓勵孩子讀書時,往往會說:“這次考試你考好了,我就帶你上街吃兩碗米粉,放多多的肉。”
也許這句話很有魔力,自從跟爺爺上街嘗到了米粉的味道后,每次上街必吃一碗米粉成為了我的心愿,而一輩子吃米粉更是我努力讀書的目標,因為在山里人看來“吃飯喝粥的人都是干農活的,把米粉當飯吃的人才是擺脫農門的象征”。這也是每個鄉下趕圩人心里的小算盤,如果趕一次圩沒吃粉,相當白趕了一次圩,那是不完整的。
可惜,我還在讀高中時爺爺就離世了,后來我考上大學,回到省城工作,一路走來還算順利,遺憾的是爺爺沒有見到這一切。
爺爺生前到過最遠的地方是縣城,如果他老人家活到現在,我一定把他接到省城,讓他分別品嘗天南地北的米粉,再聽他對這些不同味道的米粉作出什么評價。
關于家鄉米粉,還有一個傳奇色彩更濃厚的故事。有個抗戰老兵,因戰功卓著,解放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由于父母舍不得離開土地,一直不愿去城里跟孩子同住,老兵年輕時隔三差五都會回家探望父母。他每次回到鎮上,便是直奔粉店買一碗粉痛快地吃起來;每次離家前也會買一碗米粉痛快地吃完,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隨著年邁的父母先后離世,老兵年紀漸長,回家的次數也少了起來。最近一次回家時,老兵一邊吃著米粉一邊掉眼淚,嚇得隨行的兒子趕緊問父親怎么了。
老兵說我以后回家的機會少了,這碗米粉或許就是最后的一碗家鄉米粉,大都市里什么都有,唯獨少了家鄉的味道。
與老兵自帶神圣光環不同的是,我那些外出打工的鄉親們也十分癡迷家鄉米粉的味道。我不止一次聽到他們說,走南闖北多年,吃過的米粉數不清,但還是家鄉的米粉最好吃。每次啟程外出打工前,他們必定先吃一碗米粉;每次回到鎮上,第一個要去的地方也是粉店。
如此說來,盡管身份和地位不同,但家鄉米粉銘刻在鄉親們心坎里的深度是一樣的。
家鄉的米粉是樸實無華的,在廣西它沒有桂林米粉、螺螄粉或老友粉的名氣大,但它凝聚著爺爺的慈容,流淌著鄉親們的汗水,寄托著一份鄉愁,更重要的是儲存著一份溫暖和牽掛,這些意義是任何東西承載不了,也替代不了的。
我想這就是我們念念不忘家鄉米粉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