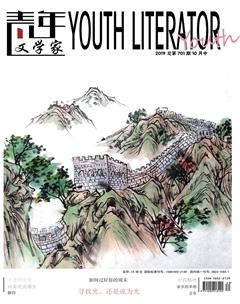從世情小說《金瓶梅》看明末清初女性意識的蘇醒
摘 ?要:世情小說為我們真實地描繪了明末清初的人情人性,晚明物質欲望的舒張帶來了女性的享樂意識,人欲的合理性被肯定,女性開始追尋自身價值。《金瓶梅》是世情小說聲譽最盛的一本,主角潘金蓮就是晚明社會被夸張化的典型人物,她的身上既有女性主動追求幸福、舒張性欲的一面,也有極端縱欲、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的一面。從潘金蓮的身上我們可看到女性自我解放、自我獨立意識的朦朧蘇醒,但是這種自我追求卻是通過對生命的恣意揮霍和自我摧殘表現出來的。作者否定了潘金蓮的“淫”,提出要將女性欲望轄域化到“理”的范圍內。
關鍵詞:世情小說:女性價值:欲與理
作者簡介:曹露,女,生于1998年6月,漢族,江蘇蘇州人,江蘇大學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師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9-0-02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確立了中國古代小說類型劃分的基本框架,他把明清描述“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的小說分為“世情書”[1],其類特點在于寫“人情”,重“人性”,作者對人物的描寫往往建立在對人的本質深入思考的基礎之上,形象自然化,以求達到“描寫世情,盡其情偽”[2]的效果。晚明世情小說為我們真實地展示了社會的動蕩與變革,在個性解放思潮下,女性形象較之以往突破了禁欲主義的藩籬,《金瓶梅》中突破了古代小說以男性形象描寫為主的創作傾向,塑造多個諸如潘金蓮這樣豐滿立體的女性形象,她張揚自我,力圖通過對肉體欲望的狂熱追求來實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她的形象集世情小說中女性主動追求幸福、舒張性欲、潑悍嫉妒為一體,從潘金蓮的身上我們可看到女性自我解放、自我獨立的意識和要求。
一、女性意識蘇醒的社會背景:物質欲望舒張與女性解放思潮
潘金蓮誕生于晚明,這個時代正處于歷史轉換的交叉點,王朝如大廈將傾,京城彌漫著反禁欲和個性解放思潮氣息,在李贄解放人性的宣揚下,女性開始審視自我地位,開始脫離封建三從四德的統治,開始下對生命意義的有了新的看法。
1、資產階級的萌芽與享樂意識的濃郁
晚明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經商不再為人們所恥辱,金錢至上的觀念形成,士人重視物質享受,《金瓶梅》中更是“人人皆商”,商品經濟的發展首先帶來了物質生活的富庶,各種奢風侈俗開始形成;人們的價值觀也由傳統的守財節儉變為享樂至上,當時普遍的社會思潮就是“好貨好色”;財欲與色欲向來是分不開的,金錢的恣意揮霍定義了享受快樂的生活理念,而這種享受的生活理念反映在色欲上就是縱情聲色。以《金瓶梅》為例,物質的富足帶給潘金蓮享受生活的條件,享樂之風又帶給她縱欲的理念,女性意識的蘇醒與資產階級的萌芽關系緊密,兩者幾乎是同時展開。
2、人欲的合理性與對女性價值的認可
晚明時期,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哲學的腐朽性逐漸暴露,陽明心學取而代之,成為社會上較為認可的價值觀,其后李贄倡導“童心”說,承認和肯定人欲、私心、私利,公開宣揚縱欲、利己的人性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把人欲提高到了“天理”的位置,為女性追求自由提供了理論支撐。雖然李贄并未倡導男女平權,但其對女性價值的肯定已經較程朱理學有了突破,社會出現了“率性而為”的文風,出現了一批追求個性與自由的文人,創作出杜十娘、賀秀娥等一批追求浪漫自由愛情的反叛形象,意圖借“女子之名教,澆內心之壘塊”[3]。但是,對人欲的不加控制導致了如潘金蓮等女性的任情縱欲,這種縱欲是對道學禁欲的極端反抗,也是對傳統婚姻關系、家庭生活的突破,潘金蓮的出現雖然另類,但也得以在壁壘森嚴的男權社會取得了自己的位置。
二、潘金蓮形象的典型化:愛情的追求者與墮落的縱欲者
潘金蓮的形象堪稱晚明社會夸張化的“典型人物”,她無疑是個淫婦,但是也是為性愛、情愛煎熬的女性形象,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女性的形象開始呈現復雜性,既繼承了傳統倫理思想的因素,又具有新時代的精神因子。一開始她是封建婚姻制度和倫理道德的犧牲品,正值青春被嫁給了“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后來她是封建禮教的反抗者,對武松展開追求;但在和西門慶勾搭之后,她化身毒婦與潑婦,害死了武大郎,在嫁給西門慶之后更是沿著縱欲和墮落的人生道路一直走下去。潘金蓮敢于沖破道德枷鎖追求愛情,但她的結局又在告誡我們,沒有理的束縛,過分的縱欲只會使人步入歧途。
1、禮教的反抗者:愛情的追求者
在《水滸》中,潘金蓮的命運不能自主,但是在《金瓶梅》中,她選擇追隨愛情。本來可以嫁給陳經濟遠走高飛,但是當她得知自己喜歡過的武松找到王婆,說愿意娶自己的時候,還是“舊心不改”,選擇冒著風險相信武松,迫不及待地對武松說:“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并且流露出戀愛的喜悅:“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里![4]”潘金蓮的愛與癡情展露無遺作者對她的縱欲和殘忍無疑是持否定態度的,其結局也是被武松剖腹宛心割頭祭奠了武大郎,但是從她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出她為自己感情的努力與爭取。
在故事的開始,潘金蓮被嫁給了武大郎,如同鸞鳳配了烏鴉,她無疑是不幸福的,如果不尋求改變,她就要永遠壓抑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以迎合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羅德榮在《金瓶梅三女性透視》中說道:“(潘金蓮)如不去偷情,就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舊時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現了偷情的潘金蓮,而在于制造了無數屈從命運,安分守己,漠然死去的中國婦女。”[5]
這個時期的世情小說中,女性開始試圖擺脫男權從屬附庸的地位,開始追求作為人的權利,《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杜十娘以投水自盡來表達對封建男權社會的抗爭、《紅樓夢》中尤三姐自剛殉情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些都體現了女性人格的升華,表現出女性渴望恢復自我人格的努力;其次,女性要求性情的自由表達,追求自由婚戀,如《金瓶梅》中的李瓶兒、《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都含著女性對自我應有權利的爭取;并且女性開始主動追求幸福、反抗禮教,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白素貞不顧勸阻,不惜水漫金山來追求自己的愛情;《王嬌鸞百年長恨》王嬌鸞以自縊的方式回復周廷章的變心,這類小說總體上都體現了女性的欲望和自然人性的舒張。
2、本我的蘇醒:墮落的縱欲者
潘金蓮的女性意識不僅體現在她對愛情的追求上,更直接的反映在她縱欲的一面和對性欲的追求上。欲望的蘇醒實際上是“本我”的覺醒,現代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的覺醒,也就要從她們身體的覺醒開始。”[6]對于潘金蓮來說,“性”的幸福與情的幸福一樣重要,性功能成為其擇偶的標準之一,但無論是“鼻便添涕”“尿便添滴”[7]的張大戶,還是“身不滿尺的丁樹”[8]般的武大郎,對她來說都意味著欲望的壓抑,等到遇到“狂風驟雨”[9]般的西門慶,難怪意圖獨占他的性生活。性功能之上的擇偶標準直接導致了潘金蓮婚姻生活中“本我”的放縱,肉欲成了主宰她生命的唯一源動力,她先后與張大戶、西門慶、琴童、陳敬濟、王潮兒等多人有過奸情,缺少理教的束縛,潘金蓮沉湎于淫欲的追逐中不能自拔,直至最后喂給西門慶過量的春藥,致其精盡人亡。
對性欲的追求,是女性以自身行動來對抗社會規范、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表現[10],正如伏波娃在《第二性》中所說:“性行為和母性義務所涉及的不僅是女人的時間和體力,而且還有她的基本價值。”[11]通過對抗,女性的家庭地位已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身為奴婢的潘金蓮借此才得以與主母吳月娘分庭抗禮。
世情小說中如《二刻拍案驚奇》等多描繪這樣的縱情女子,意圖滿足性欲者頗多,不論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龐春梅,還是《肉蒲團》中的瑞玉、瑞珠,他們都大膽地追求欲的滿足。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女性開始追求作為人的權利,試圖擺脫從屬附庸的地位,并且有意識無意識地反對禁欲主義,對男權社會倫理道德進行了抗爭;但同時她們也走向了禁欲主義最極端的反面,由反禁欲扭曲成了極端的縱欲,這種女性主義人性的舒張是以生命的恣意揮霍和自我摧殘表現出來的,是以一種摧毀生命的自棄的快樂與痛苦表現出來的[12],《金瓶梅》既寫了長達八十回的縱欲,又在結尾二十回處強加了說教的意味,既寫了女性的個性舒張,又給了潘金蓮腹宛心割頭的結局,小說并非全盤否定情欲、物欲,而是否定對欲的放縱與執念,否定女性的縱欲與墮落。
三、女性意識的合理舒張:“理”之下的“欲”
潘金蓮的縱欲帶來了生命的自我摧殘,不僅如此,縱欲形影相伴的還有極端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因為想要獨占西門慶,她變得潑悍、善妒,因為她的妒忌,間接導致了官哥、李瓶兒的死亡,她通過排擠、陷害他人來達到追求個人幸福的目的,這是縱欲下的道德墮落。作者無疑是否定潘金蓮的縱欲與善妒,但卻表達對女性合理欲望的肯定,從《金瓶梅》中主要女性人物的結局及其因果可以看出,孟玉樓等女性雖然改嫁,想要追求自身幸福,但其并未紅杏出墻,保持道德標準,因此依然得以嫁得李衙內,夫妻偕老;而春梅則是因其縱欲、與陳經濟私通等染上骨蒸癆病,二十九歲便死在周義身上。
作者按照每一個人的行為按照因果報應的標準,安排了一個善惡有報的倫理結果,這種因果報應的觀懲治了縱欲的罪惡,褒揚了對合理的情的尊崇。《金瓶梅》的作者意圖把女性的自然之行引導到“理”上去[13],“理”便是對人欲、身體的控制,失去“理”,便會迎來人性的縱欲與放肆,因此小說最后還是通過因果宣揚了“理”的回歸,將女性欲望轄域化到“理”的范圍內。
晚清女性意識的覺醒,是朦朧的、不成功的,她們生活在一個文化轉型、斷裂的時代。他們既受到人欲舒張的影響,被張揚自我、放大個性的思想觀念所感染,又擺脫不了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桎梏,也意識不到封建制度才是束縛她們的根源,潘金蓮這個典型形象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漫漫歷程,即使她們的行為受倫理文化的制約和整體地位及自身素質的局限,頗有偏失,但他們想要掙脫封建制度下的重重枷鎖,找回本真,追求自我解放、自我獨立的意識和要求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1][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
[3] 孟超.《金瓶梅》人物[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7][8][9]蘭陵笑笑生.金瓶梅[M].山東:齊魯出版社,1991.
[5]羅德榮.金瓶梅三女性透視[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
[6]張岸冰.女權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10]呂珍珍.“本我”的發現與“自我”的覺醒——《金瓶梅》女性角色意 識的文化審視[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
[1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12]姜家君.“尚情”思潮的生命審美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2014.
[13][美]道格拉斯· 凱爾納.后現代理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