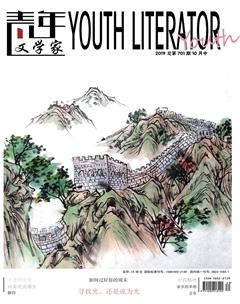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楚辭·九歌》與楚文化的關系研究
摘 ?要:本文以屈原的《楚辭·九歌》為例,從文學形式、創(chuàng)作內容及與楚地民間詩歌的比較中,闡述《楚辭·九歌》與楚文化的關系,展現(xiàn)我國古代獨具楚文化色彩的千古傳誦的優(yōu)秀詩歌創(chuàng)作。
關鍵詞:楚辭;九歌;楚文化
作者簡介:張蕊(1984-),本溪市衛(wèi)生學校, 講師,研究方向:語文課程與教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9-0-01
楚文化在地理、物產、風俗、民情、服飾、制度、語言、音樂、禮儀等方面都有異于中原文化,它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成就最高,它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為總體特征。作為一種詩體,楚辭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它被稱為“楚辭”,就是因為它“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具有異常濃厚的地方色彩。《楚辭》與楚文化背景緊密相連,保存著古代楚地民風民俗和民間傳說的一些素材和影子,這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參考的依據(jù)。
一
《楚辭·九歌》是古代楚文化的一個縮影,是屈原在楚地民歌、巫歌和民間傳說的基礎上改作加工,再創(chuàng)造的一組個人抒情詩,是詩人創(chuàng)作個性和民間文學風格的完美統(tǒng)一。屈原《九歌》與楚地民歌、巫歌之間有著不可割舍的淵源。
從文學形式行看,首先,《楚辭·九歌》保留了很多楚地的方言。例如:《湘君》中“邅吾道兮洞庭”中的“邅”是楚方言,是轉彎,改變方向之意。《湘夫人》中“搴汀洲兮杜若”中“搴”是楚方言,是摘取的意思。還有,《湘君》中“蹇誰留兮中洲”中的“蹇”,《東君》中“羌聲色兮娛人”中的“羌”均為楚方言發(fā)語詞;其次,語氣詞“兮”的運用是屈原《九歌》的一大特色,而且每句都有語氣詞“兮”“這可能是從楚地民間文學中吸取討來的一種新形式”[1]。另外,楚地民歌有注重對偶的特點。例如,著名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就是受楚地民歌的影響,《九歌》中也有很多對偶,如《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等。
從創(chuàng)作內容看,《九歌》的寫作內容與楚國巫風之行密切相關。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也指出:“昔楚國南鄭之邑沉湘之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充分說明了楚國民間巫風盛行的情況。《九歌》共十一篇,所祀諸神分別是:天神(《東皇太一》)、日神(《東君》)、云神(《云中神》)、水神(《湘君》、《湘夫人》)、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河神(《河伯》)、山神(《山鬼》)。而《國殤》是唯一祭人鬼、悼陣亡將士的樂歌,因主題的傷痛,歌頌方式與其它諸神大不相同。其中,有些神是楚國的地方神,像“湘君”、“湘夫人”是楚地湘水的配偶神,“山鬼”是楚國土生土長的山神,“河伯”本是黃河之神,但由于中原文化與荊湘楚文化的融合滲透,他便具有代表楚地水神的性質,成為“楚化的水神”。而第一篇《東皇太一》是祭祀的迎神曲,最后一篇《禮魂》則是祭祀結束后的送神曲。《九歌》再現(xiàn)了楚國民間祭歌的基本風貌。
《九歌》所描寫的祭祀場面、對自然神的禮贊和歌頌,或是對神靈之間、人神之間悲歡離合的愛情描寫,充滿著有聲有色的楚風楚韻。我們讀之,仿佛親臨古代楚國祭祀的場景,目睹楚人歌舞娛神的虔誠,還能感受到在原始宗教色彩濃厚的古代楚國,人們對自然現(xiàn)象的某種理解和想象。《湘君》、《湘夫人》、《山鬼》等“戀歌”中表現(xiàn)出的對純潔愛情、幸福生活的贊頌和向往,其中不乏原始宗教“人神雜糅”的一種遺留。正如蕭兵先生所說“(《九歌》)是屈原的獨立創(chuàng)作。但是沒有特定的文化和民俗背景卻產生不了《九歌》”。[2]
二
《九歌》本是楚國的民間祭歌,屈原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加工和再創(chuàng)造,因此,它既有詩人的個性風格,又有民間創(chuàng)作的特色。《九歌》來源于民間創(chuàng)作又不同于民間創(chuàng)作。《九歌》與先秦時期其他詩歌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九歌》保留著民間詩歌創(chuàng)作自然、清新活潑的特色。例如,《湘君》中“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湘夫人》中“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少司命》中“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山鬼》中“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等詩句,富有民歌情調,質樸自然、清新活潑。
二是《九歌》帶有濃厚的楚文化色彩,經(jīng)過詩人在民歌、巫歌基礎上的的再創(chuàng)作,具有詩人的創(chuàng)作風格。一方面,屈原的《九歌》在語言風格上華實并茂。屈原在《九歌》中大量使用華美的詞藻,唯美浪漫。如《湘君》中“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東君》中“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等。另一方面,屈原用質樸本色、剛勁堅實的語句形成詩的內在靈魂。例如,《國殤》中“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的詩句,頌悼楚國將士為國捐軀的高尚志節(jié),歌頌了他們的英雄氣概和愛國精神。《東君》中“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等詩句烘托出日神的尊貴、雍容、威嚴、英武,很好的表現(xiàn)了太陽神的特點。
三是祭祀場面的描寫風格不同。受不同地域文化影響北方受儒家約束較大孔子講“中庸之道”用禮來約束。南方受這種影響較小,人們的思想更自由想象力更豐富。這里以《詩經(jīng)》中《周頌·雍》與《九歌·東皇太一》為例作以比較,《周頌·雍》中祭祀場面“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九歌·東皇太一》中祭祀場面“揚枹兮拊鼓,疏緩節(jié)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詩經(jīng)》中表現(xiàn)為祭祀場面莊重威嚴極其肅穆,而《九歌》則是場面活潑熱鬧,不拘一格具有很強的虛幻性。
參考文獻:
[1]張家英 《屈原賦譯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頁。
[2]蕭兵 《楚辭的文化破譯》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