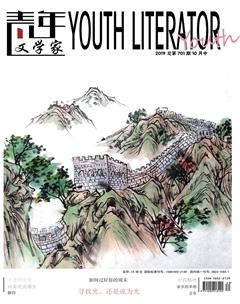欲待曲終尋問取
王智嘉
摘 ?要:宋朝出現的艷科詞是宋朝歌妓文化興榮的文學產物,在這樣濃烈的文化環境和創作氣氛中,蘇軾也在艷科詞上做了極大貢獻,而歌妓詞則是這些詞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學者對蘇軾的近四百首詞進行過研究,其中約有近半數首詞寫到歌妓。本文通過研究蘇軾的歌妓詞來深入了解蘇軾與歌妓的交往情形以及情感意蘊。
關鍵詞:蘇軾;歌妓詞;歌妓交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9-0-02
研究蘇軾的一生,他在“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調弦于茶房酒肆”的滿是燈紅酒綠的都市生活中,無論是聲名顯赫還是窮困失意,都未曾放棄過美人和美酒帶給他的愉悅。蘇軾本人也并不隱瞞他與歌妓們的往來,他就曾在《蝶戀花·送潘大臨》中說:“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余名字。”而透過蘇軾的歌妓詞,我們也不難看到蘇軾與歌妓交往的情形及情感意蘊。
1、交往情形
對于詞人一家而言,詞人會因為他的社會名聲和生活習慣而選擇與什么樣的歌妓交往。而在宦海沉浮又極愛山水的蘇軾,他與歌妓的來往大多或是在官府聚會或是攜歌妓縱情山水。
1.1卻來官府聽笙歌
宋代歌妓分官妓、家妓、私妓三種。官妓從屬樂籍,他們既然依附于各級官府,也就為各級官府的官員獻藝、服役。但政府規定地方官妓向州府提供的服務,僅限于歌舞表演及侑觴勸酒,不得侍寢。家妓往往歸屬于某一主人,他們的活動范圍,也局限于在其主人家內,而與之相交往的自然是他們的主人及主人的賓客。私妓多是聚集在歌樓、酒館、平康諸坊和瓦市等處,他們除了賣藝之外,也兼賣身。
在官宦生涯中漂泊不定的蘇軾,所交往的歌妓自然以官妓為主要對象。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蘇軾任杭州通判。在這三年里,杭州三易知州。當這三位知州先后離任時,蘇軾都為他們送別,送別時分,還有歌妓到場。這些歌妓本來就是官府的官妓,平時與官府里的官員相處就熟。因此,蘇軾在這種場合也就兼代歌妓言情,以歌妓的身份向離任官員表示惜別之意。這在蘇軾那時的詞作中很多的反映。如《菩薩蠻》(娟娟缺月西南落)的“詞序”寫明“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中所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交往方式:華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個東西,應思陳孟公。宋代官妓與官員的接觸不允許侍寢現象。蘇軾與官妓的交往,自然以歌舞相樂為內容。如有書載:“東坡在黃岡,每與官妓侑觴。群妓持紙乞歌詩,不違其意而予之”。蘇軾在公務之余與歌妓詩酒相樂可謂常事。李之儀的《跋戚氏》文,對蘇軾與歌妓相樂并應歌妓之請而寫詞的經歷敘述得很詳細。
1.2且攜歌舞到園亭
除了官宴以外,蘇軾所寫的歌妓詞多是攜手美人共游湖光山色,盡興詩情畫意。他在《約客湖上》中記載:“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哺后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江神子·江景》一詞: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菜,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跨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云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當詞人與佳人有著一場充滿“云”與“水”的邂逅,湖上陣陣古箏傳來佳人的情思,詞人和佳人透過樂曲變成彼此的知音,瞬間迸發出的火花使詞人沉醉迷戀。然而詞人“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因而詞人最后只留有濃濃的惆悵。蘇軾將這場驚艷的相遇安排在寧靜清新的山水中:綠波、山風、晚霞、搖曳生姿的芙菜、自由歡快的白鷺……兩人的情誼在山下被見證。這樣的恬靜浪漫,自然秦樓中的風流是不同的。
2、情感意蘊
蘇軾與歌妓交往的情感意蘊,用曾覿的話來說,便是“新詞佳麗見情通”。這情通的具體表現:一是詞人對歌妓頗多同情;二是視歌妓為知己。
2.1天涯同是傷淪落
在“天涯同是傷淪落”中,蘇軾對歌妓的情感則是憐憫和尊重。更可貴的是蘇軾對歌女的同情和尊重常常化為實際的行動。《賀新郎》的小序曾說過它的寫作背景是一名叫秀蘭的歌女因為赴筵遲到,對于主人的嚴厲苛責而傷心哭泣。蘇軾心生憐惜之情,為了免除秀蘭的斥責而寫了這首詞作。
而蘇軾出于對歌妓的憐憫,有時還會行使他的“特權”。即無論他在何處做官,只要他看到有官妓想要從良,就一定會鼎力相助。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九說: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過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當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于坡,欲為脫籍。坡許之而終不言。及臨別,二妓復之船所,懇之。坡曰:“而當持之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是“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
蘇軾之所以能答應歌妓的請求,解除他們的妓籍,是因為他在平時的交往過程中,對歌妓有了較深的了解。在此基礎上,詞人有時還會進一步認同歌妓。他們常從歌妓的身世聯想到自己的遭遇。蘇軾在《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中有句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也指為一名叫周韶的官妓脫籍之事。
2.2莫愁前路無知己
將歌妓引為知己,古來詞人皆有之。唐白居易《琵琶行》有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晏幾道在其《采桑子》詞中也曾這樣寫道:“知音敲盡朱顏改,寂寞時情。一曲離亭,借與青樓忍淚聽。”蘇軾有一首贈歌妓柔奴的《定風波》: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據《曹溪漁隱叢話》后集引《樂皋雜錄》說:這是蘇軾題贈王定國的歌妓柔奴的。王定國因蘇軾“烏臺詩案”的牽連而貶謫賓州監酒稅,歷時三年而還,路過黃州,這時蘇軾貶滴黃州也已經過了四個年頭。柔奴是隨王定國的家妓,復姓宇文氏,家世居京師,得王定國喜愛隨同南行北往。在作者看來,嶺南一帶荒蠻不堪,王定國受貶于此,一定極其委屈,誰知卻安于患難,不以為意。在一次酒宴上。王定國讓歌妓柔奴出來勸酒。蘇軾試問她:“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答道:“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聽之深受感動。不錯無論天涯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同樣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且樂觀以對的蘇軾,無疑將柔奴引為了知己。蘇軾后來頻繁調動,晚年被貶于嶺南,在艱難困苦中仍保持著這種樂觀的情緒。
與柔奴相比,無論是在蘇軾的精神生活還是實際生活中,朝云更可稱為蘇軾的“紅粉知己”。王朝云因家境清寒,自幼淪落在歌舞班中,為西湖名妓。朝云時年十二歲便于蘇軾相識于西湖,盡管朝云年幼,但她卻很聰慧機敏。朝云對于東坡先生的才華十分仰慕,而且與蘇軾夫婦的關系極好,由于自己與蘇家緣份深厚,她便決定跟隨東坡先生左右。雖然朝云的地位與蘇軾之妻王閏之不能相比,但是她在文學審美極高,比王閏之更能了解蘇軾的精神需求。據《東坡筆記》所述: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東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云曰:“學士一肚皮不合入時宜。”坡捧腹大笑。說東坡滿腹智慧,固然也對。但蘇軾在新舊兩黨執政時都遭受排擠,所以確實由于他一肚子都是些古怪的思想。這也難怪東坡會捧腹大笑,還把朝云當做知己。蘇東坡感嘆作一首《朝云詩》贈之她:“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對蘇軾來說,朝云可謂是一位真正的“紅顏知己”。
蘇軾一生與歌妓有著不解之緣,或是在官府觴宴,或是在山水之間。蘇軾與歌妓歌舞相樂的過程中也滲透著自己的情感。或是尊重同情,或是引為知己,蘇軾與歌妓之間的情感早已超越了階級與身份的藩籬。他們相樂相惜,共同奏響了詞曲文化的交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