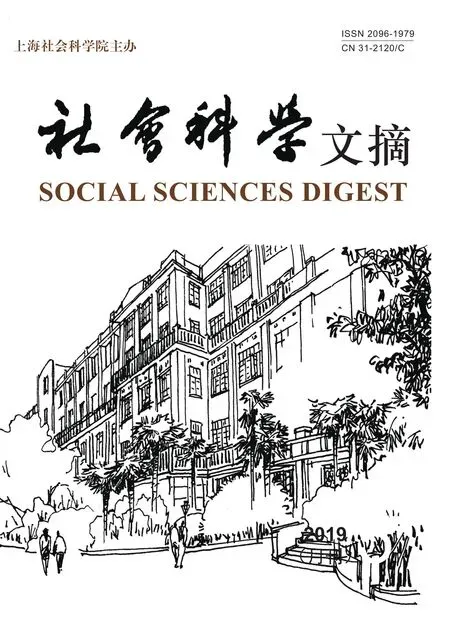漢唐洞窟志怪的文化史研究
——以文學性的生發為線索
洞窟小說是漢唐志怪的獨特題材,始于《列仙傳》“邗子”,終于晚唐裴鉶《傳奇》中的“許棲巖”。其后的洞穴故事多是對這一時期作品的祖述與改寫。在漢唐時期的地理書、道教典籍、詩文以及志怪書中都可以看到有關洞窟的故事傳說。這類流傳了幾百年的小說,是漢唐志怪中的一個題材類型,以其流行程度而言,可以視作一種文化史的現象。從中可以尋繹出志怪小說虛構敘事的生發,以及志怪中人對白話小說人物形象的影響。
文化史視野中的洞窟志怪
漢唐間約出現了二十余篇洞窟志怪小說,見于道教典籍、地理書的各類洞窟傳說尚不計算在內。其中六朝洞窟小說約有十幾篇。六朝志怪類型化的傾向比較明顯,很多故事是重復的,似是不同記錄者造成的結果。唐代的洞窟小說,因其道教色彩濃厚,故在質樸的故事框架上,生發出了華麗的藻采與臆想。漢唐洞窟志怪成為后代詩詞、小說、戲曲反復書寫的素材與故事原型,它們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引入了悵望青山、慕戀神仙的心靈維度與空間。
這些洞窟故事在唐宋就引起了文人探究和考察的興趣。現代學者對洞窟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洞窟小說的現實依據;(2)洞窟小說傳播的時代;(3)洞窟小說的主題。洞窟傳說被分成“遇仙”和“遇隱”兩條主題線索。洞窟故事主要在南朝以前流行,劉宋以后,洞窟傳說很少能在小說中再見到了。劉宋時代,山中道館興起替代了修道的洞窟,這與南朝洞窟小說的衰歇不應只是巧合。
中古時期,志怪與史書、宗教文獻與地記等都屬著述性質,并非獨創性的文學虛構敘事。從文化史的角度能夠從更多面的視角觀察志怪的性質及其演化過程的細節。志怪在漢唐時屬于“史部雜傳”,宋代之后被歸入“子部小說”,在古代的學術體系中,都是具有一定的知識性和客觀性的著述,這一點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此情形下,我們試圖將中古時期人們的知識系統與信仰世界作為一個重要維度,引入到洞窟小說的研究之中。綜合史學、宗教、地方地理與文學的文化史視角,能夠為志怪小說的研究帶來新視野。
首先是時段問題。洞窟小說的流行跨越了漢唐。把漢唐間這些洞窟小說作整體性考察,更能突出其淵源與屬性的某些線索。如洞窟小說主要以人物名字和地理標志命名的現象,顯示了這個時期志怪小說的性質頗同于史傳或地理書。以人物命名者,類史部雜傳模式;以地理標志命名者,類地記。從其命名方式就可以看到,漢唐時代志怪在“史部雜傳”與“子部小說”之間的游移和不同的發展方向,它們為洞穴故事帶來不同的質素與面目。
其次,志怪與其他著述的關系。洞窟志怪與魏晉地記、道教文獻的密切關系,提示著志怪作為社會文本歷史的公正性質。志怪文本在宗教文獻、地理書中的共用與流動,顯示了它們在中古時期具有知識性和實錄性的特點。魏晉六朝,地記中的洞窟記載,既包含著志怪的雛形,也有情節完整的傳說。因其數量眾多,故能在整體上清晰地展示出神怪傳說在形成中的各階段的形態。
再次,文學因素的生發與影響。從魏晉志怪的粗陳梗概到唐代刻畫細致的洞窟小說,在志怪的基本模式中,藻采與意趣等文學性因素潛生暗長。同時,洞穴故事的現實依據,也使我們注意到故事講述者的問題。“遇仙”和“遇隱”固然代表了魏晉人的信仰主題,但在這兩類主題之下,都有一個凡人“遇險”的現實經歷。他們是進入洞窟的凡人,其身份是山民、獵戶以及被推墜到洞穴中的人,這些幽閉昏暗空間中的生還者也是洞窟志怪的敘述者。從本質上說洞窟小說是歷險故事,但在敘述者口中都成為“遇仙”“遇隱”的神奇經歷。這樣的洞窟志怪是如何生成與變化的?通過洞窟志怪生成語境的還原,我們看到洞窟小說的本質是對中古知識與信仰的志怪化書寫,通過各種故事和傳說建構起對知識與信仰的認同。
“遇仙”故事與文學性的生發
洞窟“遇仙”故事本多方士夸誕之言,包含文采與臆想的質素。唐人洞窟小說借助道教的夸飾性修辭,使志怪更具敘事的虛構性。《列仙傳》的“邗子”是中古洞窟故事的序曲,緊隨其后的《博物志》《拾遺記》《玄中記》《搜神后記》《異苑》《幽明錄》和《殷蕓小說》都涉及類似題材。其中以陶潛《搜神后記》故事最為集中。《搜神后記》“卷一”一共出現了六個洞窟故事。在稍早的王嘉《拾遺記》“卷一〇洞庭山”中,就有了采藥人入靈洞,獲邀入璇室,飲瓊漿金液事。這些遇仙故事讓神秘洞窟更令人神往。
雖然在魏晉,大部分志怪還停留在口傳階段的粗略梗概上,但無論是王嘉《拾遺記》那般的方士浮夸,還是《搜神后記》文人式的質樸清新,都具有了超出日常敘事的文采。在原本樸野的敘述中,增加了更多的細節描寫成分。文學之優長在于給普通的故事延伸出想象的空間與心靈的感染。如遙望山上的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永無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其家筒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這類訴諸感官的細膩文字是經過結晶、提煉的文本,在事件的怪異之外還給更多讀者帶來具有個人感受的親切意味。
類似的文學性想象在唐人洞窟小說中繁茂滋長,覆蓋了志怪原本粗陋的框架。這時的社會已脫離魏晉六朝地理地貌大發現的時代,洞窟志怪不再是具有實際生活價值的知識性傳說,而是出于文本的祖述與個人的想象。試舉兩個例子。其一是皇甫氏《原化記》之“采藥民”。其二是《博異志》中的“陰隱客”。唐代的這兩篇洞窟小說通常被稱為仙鄉小說。因為除了模仿前代志怪的情節或祖述道教典籍的洞天想象外,魏晉六朝洞窟志怪中僻遠、深險一類的地質特征大為淡化。小說中的洞窟帶有很大的虛擬性,有些沒有確切地理方位上的實體,洞窟多在人居左近。研究者將魏晉六朝道教典籍中位于山、島、洞窟之間的仙府,看作其時寒門、寒士為追求個人價值與身份而在人間邊緣地區虛構的太平世界。如果說魏晉六朝時代對門閥制度的絕望是建構虛幻世界想象力的源泉,那么這種絕望的感染力在隋唐時代已經被夸示性的金碧輝煌與腐化的肉體享樂誘惑所取代。《采藥民》里,采藥的凡夫貪顧玉皇左右數百玉女,還有“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對此粗鄙的凡夫倒也不以為忤,反而諄諄誘導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早期洞窟小說那種樸素的仙境描寫蕩除幾盡,唐人在洞窟中構筑了物質與欲望的空間。
“遇隱”故事的寄托與演化
陶潛《搜神后記》中的“桃花源”是最著名的“遇隱”小說。這類志怪寫凡人通過深山洞窟進入一個封閉、不為人知的人間世界,卻最終失卻,茫然不可復得。從古代就有了各種考證武陵桃源的文字。這些史實考論在厘清《桃花源記》之紀實性質之外,也涉及了志怪小說的紀實成分。魏晉志怪的洞窟小說中,寫洞窟遇隱主題者,以《搜神后記》記錄的“遇隱”故事最集中,顯示作者有較明顯的寄寓隱居理想的傾向。
以魏晉戰亂頻仍,南方很多地區處于加速開發進程之中的情況而言,位于政權政治秩序之外的深險之地存在的一塊塊封閉、自治的區域,不單是各地方的堡塢、“依阻山谷,與越相雜”的華夏舊民,還有蠻、僚、俚等族分布于廣闊的未知區域。這種地曠人稀的時代,地勢險阻,洞窟小說那種入山穿穴,“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為世業”的情形,有著相當的紀實成分。
南朝各類地記也有類似“桃花源”的故事,顯示在魏晉南朝的特定時代與地域中,這類傳說的普遍性。這些被山險阻隔于王化之外的“人世”之所以成為怪異,只是特定的時代與區域現象,離開了那個時代就失去了現實的土壤和意義。因此,洞窟“遇隱”只是一個階段性的主題。
唐代洞窟小說中沒有“遇隱”故事,洞窟經歷被普遍仙化。唐人把《桃花源記》中的人物,也看作神仙。在很多唐人詩歌中,桃源和仙鄉是一個意思。桃源與仙人、仙客、仙宮的意象粘合在一起,顯示在唐人眼中桃源就是仙鄉的別稱,洞窟志怪的主題自然只有遇仙一種。唐人常以“神游蓬島,洞入桃源”對舉,將蓬萊島和桃花源視為神仙世界。從唐人的桃源圖畫中也可以看到一派仙鄉景色。唐代舒元輿《錄桃源畫記》,記四明山道士葉沈所藏“桃源圖”古畫,完全是道教的仙境想象。這一點還可以從蘇軾的話中得到印證。蘇軾《和桃花源詩序》稱:“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雞乎?”胡苕溪云:“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蘇軾的這種見解在當時可稱洞見。蓋不但唐代詩人將桃源成為仙鄉,唐代小說家也以此為題材,將隱士神仙化。
唐宋之世,隨著王朝對疆域內地方統治縱深層面的控制,王化之外的世界基本不存。這時的文人學者再看桃源,就完全忽略了它們的現實依據。宋代葉夢得對前代洞窟小說頗為神往,并一一考據。葉夢得曾考察鎮江茅山和華陽洞,言鎮江茅山“不至大,亦無甚奇勝處”。華陽洞“才為裂石,闊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混康嘗得入百馀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除了地理開發變遷之外,此亦宋人對魏晉道館起于山中的歷史隔膜無知造成的。
瞿佑《剪燈新話》之《天臺訪隱錄》,模仿《桃花源記》,言徐逸入天臺山采藥,見水中巨瓢,沿溪入石門,見到茅屋石田的村落以及衣冠古樸的老者。這位老者生于宋理宗時,宋末避亂入山。老者雖自稱“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不言而喻,這些長生不老的逃民也已成了神仙。小說雖名“訪隱”,卻是洞窟“遇仙”故事的翻版。
文化史的解讀與志怪的文學影響
從文化史的角度解讀洞窟志怪,為我們探討志怪書寫方式及其文學影響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從文化史的角度講,不論是洞窟“遇仙”還是桃花源中的遇隱,這些主題都是以怪異化模式書寫的歷史與風俗。通過還原不同志怪背后的歷史與知識,可以對志怪的書寫模式有更深入的理解與把握。以洞窟小說而論,求仙與遇隱的一類令人向往的奇遇背后,極有可能是古人艱辛的人生與殘酷的風習。在將這些艱難與殘酷視為人生不可免除、無需訴說的宿命的一部分后,才有了各種神奇與怪異的慰藉故事。民俗學者對各地棄老風俗的田野調查與研究,為闡釋洞窟小說的主題和人物形象提供了啟發。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湖北各地都發現了很多老人洞,據民俗學家與考古學家的田野調查,這些洞窟應屬古代“寄死窯”的遺存。但是這些陰暗的歷史很少有文字記載,倒是一些志怪故事留下了些許的印痕。唐代薛用弱《集異記》中的“李清”是頗為有名的唐代洞窟小說。這位主人公自愿墜入洞窟尋仙的舉動,似乎透露了中古洞窟小說的某些消息。民俗學者將李清入云門山穴故事視為古代“棄老”習俗的體現。棄老這個話題本不在本文的探討范圍內,但是李清的洞窟尋仙使我們注意到洞窟小說被掩蓋的一面——洞窟故事的本來面目是邊緣人群的被棄或者歷險。我們可以試從兩個方面來看。
首先,洞窟小說的主人公是處于下層的百姓。這些人物的共同特點是社會地位的邊緣化:一類是處于社會階層的邊緣;一類是處于年齡上的邊緣。這些邊緣化的民眾能夠在洞窟中遇仙得道,符合道教宣揚的人人可以成仙、處處皆有神仙的思想。但是這些下層小民進入洞窟是迫于生計的冒險、是被棄之后的無奈。他們對山脈洞穴的認識、對“仙人”的描述是出于貧乏的頭腦和恐懼心理的想象,而宗教與民間傳說恰為他們的心理提供了自我合理化的途徑。
其次,“遇仙”情節的神奇掩蓋了主人公因身份低微所遭遇的艱險苦難。這些進入洞窟的人,大都是因為身世的不幸。《列仙傳》“邗子”在洞窟中見到“故婦主”,也就是去世的女主人,則可知其為仆從的身份。這個懵懂的仆人闖入山穴,經“十余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才見到臺殿宮府。對他來講,這是一種絕望掙扎的經歷。今天的讀者可能會問,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他敘述是否可靠?雖然志怪小說中并沒有不可靠敘述——這類精細的講述技巧,但是到了洪邁《夷堅志》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對于志怪經歷者的身份、智力的貶抑,卻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所志之“怪”的懷疑與否定。
我們從洞窟小說的表述方式,略窺志怪小說對古代敘事文學的影響。概括說來有兩點最為突出。
首先是對怪異之事的選擇與表現的方式。志怪者記錄怪異。什么是怪異,則取決于當時的知識背景與文化認知。洞窟故事大多屬于道教的仙話,所以“遇仙”是整個故事的神奇之處,而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命運遭際被按壓在怪異事件的背后。志怪這種追求奇異,而對人物的命運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交代不足的特點,與其“小說”性質有關。所謂“叢殘小語”“街談巷議”,很多內容是抄輯書籍、文獻以及口頭流傳的故事成書的,脫離了原文上下語境和豐富的意涵,只是撮取大意而已。志怪以怪異為題材與主題,對中國敘事文學的影響深遠。嗜奇喜怪的民間審美,成為敘事文學的底色。從這個意義上說,志怪小說不但為后世文學性小說留下了豐富的題材庫,更因其審美方式而影響深遠。
其次是志怪中的人物設置對小說人物性格設置的影響。那些掙扎在洞窟之中的歷險者,他們的凡俗形象、限知性的視角,構成了志怪故事中特殊的力量配比——神仙鬼神高高在上,凡夫俗子匍匐于下。凡人軟弱被動的性格,不但是在魏晉、唐宋以及明清的志怪是慣常的設置,受志怪影響的很多白話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具有某種軟弱的共性。志怪故事中,凡人與仙道、鬼神打交道的模式化書寫方式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以洞窟小說為例,這些歷險故事的主題并非講述英雄的抗爭,而是意外的好運——“遇仙”“遇隱”。這使得人物不需要強梁的個性、精明靈活的心計或者積極進取的精神,只需要凡人的本能反應即可。所以,志怪中的人物大多面目模糊,只有身份符號而缺乏個性的辨識特征。主人公本身都只是一個視角與媒介,通過他們傳遞“神道不誣”的觀念。有這樣的志怪傳統,就使得小說作家很難敷演出人神之間勢均力敵、英雄氣魄的史詩級的抗衡和戰斗。
總之,從文化史的多元角度進行解讀,更符合志怪作為“子部小說”的知識性、龐雜化的著述性質。由此,也能夠更清晰地認知其文學性的生發與影響。此即漢唐洞窟志怪研究帶給我們的初步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