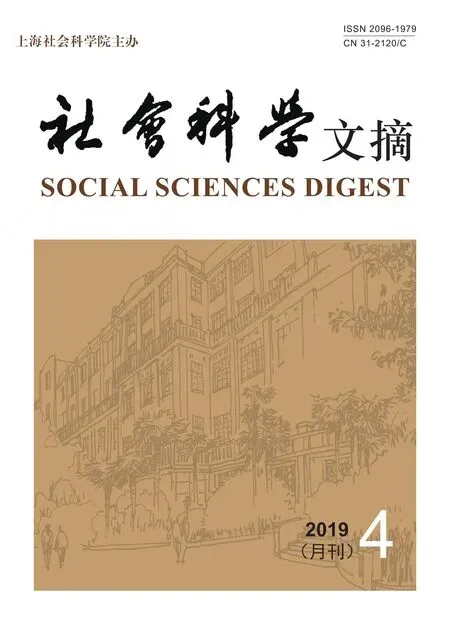新民主國家的再分配理論:歐洲新民主國家的收入差距
民主能否減少收入差距?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研究認為,民主要對大多數人負責,民主應該帶來更大的收入平等。弱勢群體在民主國家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為他們可以將數量的多數變成政治優勢,從而要求實現再分配。現有的研究還發現,從專制政體過渡到民主政體后社會支出會顯著增加。這些增加了的社會支出主要流向了多數人那里(主要是窮人)。因為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需要建立比專制統治者更強大的聯盟來獲勝,所以,他們選擇用公共政策來換取贏得選舉的籌碼。
盡管有這樣的理論預期,本文的研究卻表明,新民主國家在轉型之后并不具有顯著的減少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實踐觀察結果也表明,歐洲大多數新民主國家都保持著原先的不平等水平,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平等水平還有所增加。為什么一些新民主國家沒有實現收入平等的理論預期?本文在新民主國家存在沒有改善窮人生活、減少不平等、兌現其經濟承諾的現象后,再試圖去分析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
民主并不能減少不平等,主要在于,窮人在選舉過程中的低參與度和新民主國家政黨的弱制度化。兩者使得執政黨在進行國內資源分配過程中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工會、商會等這些有著很強組織能力的團體,自專制政權時期起,他們就與新民主國家的執政者之間關系密切。在建立民主政權后,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刺激政府,使得政府推行有利于他們的社會政策。一方面,窮人由于缺乏公民社會所需的各種能力而導致政治參與不足;另一方面,政黨對這些高投票率的社會團體的依賴程度又進一步增強。這就使得分化的社會政策日益有利于富人階層,從而導致收入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
本文研究的意義有三點。首先,它有助于我們理解民主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文章對現有文獻中關于選民投票率和穩定的政黨制度化的理論假設進行了重新考慮,提出了中間可能選民理論(Median Likely Voter Theory)來修正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y)。其次,文章強調并分析了新民主國家政黨制度波動的影響,說明了高度波動是如何導致更多經濟不平等的定向性政策產生。最后,文章在綜合了民主化、社會政策、收入不平等和政黨體系制度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解釋了為什么向民主過渡會導致更大的不平等。
民主與不平等
再分配是政黨追求最大化選舉機會時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它通過稅收和社會政策的形式把資源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轉移。為了贏得選舉,作為執政者和選票追求者的政黨作出了選舉承諾,并進一步導致了他們提出傾向于中間選民(median voter)的政策主張。平均收入(mean income)和中間收入(median income)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再分配水平。如果中間選民的情況相對較差,那么,政黨則傾向于分配更多資源給中間選民,以縮小差距。唐斯(Downs)以中間選民的均衡為基礎,運用他的再分配理論來解釋民主政權和專制政權在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差異。其論點的前提有兩點。首先,專制領導人需要精英階層的支持,他們需要滿足精英的利益以維持權力。這使得他們不太關心窮人的福祉。其次,與專制政權不同的是,民主國家堅持多數主義。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在議會中占多數以實現掌權。因此,民主國家的執政黨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中間選民作為目標,并為之爭取更多的再分配資源。這樣就會促使政黨實施更多旨在縮小中間收入(median income)和平均收入(mean income)之間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向富人征更多的稅,以重新分配給窮人。由于這種再分配政策,民主國家才可能產生減少不平等的預期。
然而,本文對31個民主國家基尼系數進行了對比,對比的結果卻發現新民主國家中不平等的增長情況非常嚴重。在1975年到2005年間,與已建立的民主國家相比,新民主國家的不平等分值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明顯違背了民主應該減少不平等的傳統預期。本文需要對這些差異進行解釋。
中間選民理論與中間可能選民理論
中間選民理論是解釋新民主國家政黨運作的重要框架,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它首先假設的是所有人都投票的狀態,從而認為重新分配有利于中下階層。在所有人投票的假設下,政黨將制定社會政策,以回應處于中間收入水平的選民的再分配要求。
然而,與中間選民理論中的假設相反,民主國家的調查表明,窮人在選舉中投票的可能性遠小于中產階級,窮人對執政精英施加的壓力相對較小。貝拉門迪(Beramendi)和安德森(Anderson)在對經合組織國家的研究中表明,中等收入以下的選民選舉棄權率非常高。很多學者也持類似觀點:選民投票率不成比例的下降來自窮人的退場,而資源分配率的下降又進一步削弱了窮人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窮人的低投票率是這一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還沒有關于新民主國家窮人投票率的經驗數據。本文使用了2002年至2006年間進行的三次歐洲社會調查(ESS)的所有數據來分析這些國家的窮人和富人在投票率上是否存在差別。
在使用所有“歐洲社會調查”(2002 ~ 2006年)的數據后,本文發現:不論是新民主國家還是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都存在窮人不同程度的棄權現象。除了英國、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國,無論是新民主國家還是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窮人都占不投票人數的很大部分。如果我們考慮收入群體的投票概率,可能選民(Likely voters)的相關人數將會更加充裕。因為考慮到了窮人和擁有較強組織能力的群體的投票水平的差異,新中間選民理論在社會支出分配方面相對現實。中間(可能)選民的政策偏好更有利于富人選民,而不是窮人選民。因為富人對政黨有著強大影響力,他們除了投票選舉和游說等活動之外,作為有組織力量的群體也不斷對政府施加影響力。而窮人不積極投票也不熱心于通過組織的力量去影響政府。這樣就減少了收入再分配的可能。
其次,中間選民理論假定執政黨對重新分配給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團體沒有偏好。這一假設忽略了政黨和工會、專業團體、小企業主等這些公民社會組織團體之間的先前關系。在專制時代,執政精英通過團結不同的組織團體來鞏固政權,而親民主聯盟則通過與各種組織團體的結盟來挑戰專制政權。所以,掌權后的政黨會通過偏向這些組織團體的社會政策,以獲得他們的繼續支持。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公民社會的強勢群體利用與政黨正式和非正式的關系,對政府政策施加更大的影響力。
最后,中間選民理論假定政黨存在并運作在一個穩定的政黨制度之中。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而言,選民可以收集有關政黨政策立場的信息,反對黨也有相對穩定的選民基礎。但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政黨都是在高度動蕩的選舉環境中運轉,這就增加了政黨為了選舉利用社會政策的可能性。發達國家現有的政黨體系具有低度波動性。這些政黨建立在深刻的社會分裂之上,是具有穩定性的選舉組織。他們成立一黨執政的政府或長期聯盟的政府,已經磨合了幾十年。新民主國家政黨在政府和議會中的存活率很低,執政黨更替頻繁,很難預測哪一政黨將組建政府。在1945年到1995年期間,歐洲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有48%的政黨獲得連選連任,而拉丁美洲只有32%的政黨在此期間獲得連選連任。后共產主義國家中在1991年至2006年期間只有16%的政黨實現了連選連任。新民主國家政黨的競爭非常激烈,即使是執政者也同樣面臨著生存挑戰。
波動對社會支出和不平等的影響
社會政策的高度波動性會產生一些影響。
首先,波動性給執政黨帶來了選舉的不確定。為了在動蕩不安的政黨制度中生存下去,政治家們很可能借助政策工具來實現選舉機會的最大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用社會政策來獲得自己黨派選民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政黨還需把那些并非其權力基礎、但組織良好的選民群體作為爭取對象,為這些關心社會政策并且投票可能性很高的選民群體制定政策,以獲得他們的選票支持。
其次,學者鮑恩(Bawn)和羅森布盧特(Rosenbluth)認為,“長期”聯盟組成的單一黨派政府和“短期”聯盟組成的多黨派政府具有不同的選舉問責機制。與一黨政府相比,多黨派政府的公共支出更高,即使這兩個政府都代表同一個群體。與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相比,新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或)政黨更替率更高,社會政策壽命相對短暫。他們在制定社會政策時,優先考慮歷來投票率高的群體的利益。如果是聯合政府,那么其存活時間可能更短,政黨有著更大的壓力將公共資源分配給聯盟伙伴的主要支持者。總而言之,隨著政黨制度的波動加劇,政黨更可能偏離惠及窮人的綱領性政策,并傾向于其自身的基礎選民和具有較高組織能力、有可能幫他們贏得選舉的群體的利益。
窮人選民的低投票率和政黨制度的高波動性,兩者影響了社會支出的使用,使社會受益比例相對較小。投票率越低、波動越大會導致更多的定向支出。政黨需要向支持他的組織群體轉移資源,以維持并鞏固其選民基礎。如前所述,窮人的低投票率、政黨制度的不成熟、現有政黨和選舉結果之間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窮人在分配國內資源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教育和衛生等非定向支出資源被削減或針對窮人的定向支出被削減,這些群體的社會流動將日益困難。政府傾向于忽視窮人,他們的政策有利于那些組織良好的投票群體。隨著定向支出水平的提高,再分配的低效率將進一步加劇新民主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數據方法和結果
(一)數據方法
我們把歐洲作為研究對象,構建的數據模型包括定向支出和不平等兩個變量,但定向支出也是不平等模型中的一個關鍵自變量。兩個主要自變量是投票率和選舉波動性。主要的因變量是基于基尼系數中可支配收入來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數據結構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由于缺乏數據可用性,數據范圍限于從1980年到2003年31個國家的數據。
(二)數據結果
1. 收入不平等對定向支出的影響
對新民主國家而言,選舉波動、政府意識形態對定性支出具有積極的影響效應;而投票率、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則對定性支出具有消極的抑制作用。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促進了政府定性支出,而隨著選民年齡的增長,會對定性支出起到消極影響。因此,投票率上升,這意味著以前低動員的群體(如窮人)將參加選舉,迫使當事方轉向扶貧的立場,選民投票率的水平會緩和波動對定向支出的影響。
2. 定性支出對不平等的影響
總體來說,模型結果支持定向支出對平等有不利影響的結論。定向支出在統計上顯示了不平等的滯后影響。定向支出的直接影響是積極的,但統計上不顯著。在控制其他變量時,定向支出的增長會增加不平等。定向支出增長了1個百分點,不平等將增加0.09個百分點。如果增長了12%,那么不平等的變化就是1%。
調查結果還顯示,納入(滯后的)定向支出對這些工業化民主國家的不平等沒有統計意義。這可能是因為勞動力市場覆蓋率高,公共資金支出通過養老金、失業和其他福利覆蓋大部分人口。這些國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都很高,這表明每個人都受益于定向支出。總體而言,這些結果支持了本文的觀點,即對新興民主國家不平等的研究必須考慮定向支出的增加。
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來說,只有落后的不平等會對不平等水平產生持續的顯著影響,其他變量影響不大。另外,通貨膨脹和城市化會加劇了不平等,經濟增長則可以減少不平等。經濟表現的改善,對新興民主國家的收入分配可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根據庫茲涅茨曲線,新民主國家經濟發展對不平等的影響呈曲線狀。
結論
本文采用大樣本跨國分析的方法,試圖闡明歐洲第三波新民主國家在向民主過渡之后經濟持續不平等的原因和方式,并進一步解釋了歐洲新民主國家無法產生收入平等的原因。對學界而言,有以下幾點貢獻。
首先,理論和實證結果挑戰了民主會減少不平等的傳統觀點。中間選民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窮人在選舉過程中會有更多的發言權,迫使執政者重新分配資源給他們,直到實現中間收入向平均收入靠攏。然而,這一理論仍無法解釋新興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政治。中間選民理論需要被完善修正。實證研究結果否定了以下觀點:即從專制政權向民主政權過渡,由于增加了選舉權和獲勝聯盟,將導致更高水平的公共產品。本文也反對布瓦(Boix)的觀點:作為對大眾公共產品和政策的需求回應,民主帶來了更多的公共預算。模型研究結果表明,公共部門更關心為富人制定和執行政策。窮人政治的低參與度扭曲了新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然而,如果窮人動員起來并參與其中,情況可能有所不同。這樣一來,即使在極端不穩定的選舉環境下,也可能實現對窮人公共政策再分配的轉移。
其次,本文修正了梅爾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rd)提出的中間選民理論,提出了中間可能選民理論。中間選民理論忽略了歷史、意識形態和公民社會組織化的利益團體與政黨之間的組織聯系,而中間可能選民理論看到了窮人低投票率、政治制度高度波動性的事實。它為認識新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政治提供了一個更現實的圖景。
第三,本文的研究豐富了由基弗(Keefer)等人發起的討論,認為新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信譽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將促使公共政策處于從屬被利用的地位。各大政黨在選舉中缺乏有特色的政黨綱領,社會政策處于從屬地位,往往被用作爭取另一黨派選民的重要工具。政黨選民基礎日益趨同,這對公民福利和民主質量有一定影響。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認為,政黨選民基礎的趨同減少了選民的福利,而分歧可以增加福利。但政黨選民基礎的趨同,增加的是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團體的福利和政黨核心支持者的福利,對窮人來說卻并不如此。
總之,本文研究揭示了新民主國家出現了不平等這一令人費解的現象,并提出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本文分析僅限于歐洲,本文的理論,特別是組織化的公民社會團體與政黨、選舉波動之間的關系,可能也適用于其他新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