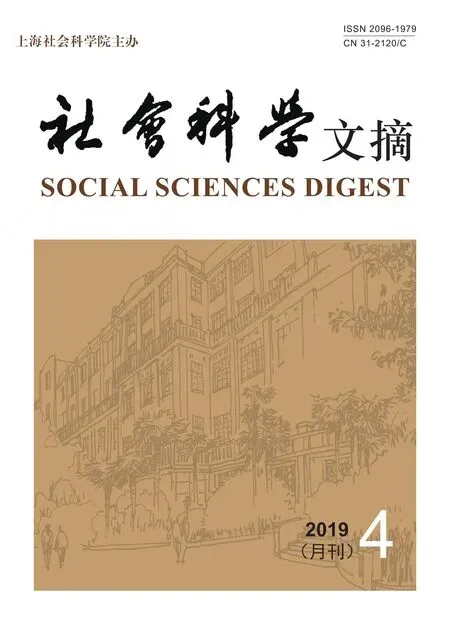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徑
自筆者的明清 “帝制農商社會”說提出以來,其與葛金芳先生以唐宋時期社會經濟為考察重心的“農商社會”說、林文勛先生以唐宋以降中國社會主導力量為考察中心的“富民社會”說一起受到關注,促使筆者對該說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徑做出學理自查和說明,以便同仁進一步評析。
問題的由來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李洵先生指導下從事明清史學習與研究。先生關注的根本問題是“明清社會結構”,其核心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關系或者生產方式,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當時國內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研究的基本理念一致,都主張明清時代是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時代,分歧在于資本主義萌芽的具體表現、程度,以及如何解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最終沒有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我嘗試沿著學術界的主流方式考察下去,發覺把前輩們發掘出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證據加在一起,能夠確證明清中國經濟領域充滿活力,在變化、發展,但不能確證這些發展已經匯流成為一個確定的走向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或過程。至于有關資本主義萌芽未能發展成資本主義大樹原因的分析,當時的研究都屬于對推論必然發生而又沒有發生的事情的解釋。歷史學研究已然之事,對未然之事雖可推測展望、連帶思考,不可能用實證方法考察。所以,討論中國為什么沒有自發展開資本主義社會接近于在探討理論,從歷史學意義上說,這遠不如討論明清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更有意義。
80年代,我梳理了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亞細亞形態說、東方專制主義說,以及理論家的相關論述。這時發覺3個相互關聯的情況。
第一,參與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多數學者沒有注意區分“資本主義”是被作為一個社會體系,還是經濟體系的問題。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大多傾向于經濟決定社會的其他方面,因而覺得二者區分的意義不大。但如果那樣,就落入了單向決定論。這種思維不適合討論復雜系統,而社會歷史的形態演變就是復雜系統。生產關系領域的雇傭勞動關系萌芽現象只表示出現了在性質意義上與資本主義經濟契合的情況,不表示已經發生了在歷史趨勢意義上向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演變過程。如果“資本主義”被視為一個被抽象化的經濟類型,那么雇傭勞動關系就可以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這種萌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
第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者的方法論都立足于人類社會五種形態依次演進的學說。馬克思表述過兩種社會形態概念系列,一是三大形態系列,一是五大形態系列。其中,三大形態系列是邏輯和歷史的統一;五大形態系列是邏輯的,不是歷史的,而且馬克思的五大形態是指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五種“生產方式”,與中國學術界習慣表述的不同,也從來沒有表述過五大形態是作為世界普遍規律的表現而依次遞進的。我們習慣表述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依次發生、前者孕育后者的模式是蘇聯理論家以斯大林名義表述的說法。
第三,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現代歷史學,都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論證指向是求證中國歷史發展符合世界歷史普遍規律,然而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需符合歷史的經驗事實,按照中國在人類歷史中波及的空間范圍、人口占比、文明表現,如果中國歷史與“普遍規律”不符,該規律就不普遍。所以,我們原不應該提出中國歷史是否符合人類歷史普遍規律這樣的問題。
90年代在加拿大求學期間,我在學習史學理論、社會史、世界史以及西方明清史研究情況的同時繼續思考,主要心得是: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特殊話題,西方學術界不使用這個概念,其認真對待的問題,是現代性在中國發生的歷史過程,以及是否存在本土文化、社會、歷史依據的問題——這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很大不同。世界歷史上只有西歐的歷史接近于斯大林圖式的五形態遞進歷程,其他地區、民族、國家皆非如此,所以五形態依次遞進不是定律。文化差異對于理解宏觀歷史演變,尤其是文明的推演,具有根本性意義,而我們以前思考社會歷史時對文明視角過度忽視,接近于把歷史演變當作經濟帶動的過程。然而人類歷史演變中的普遍邏輯和共性并不能嚴格規定各文明、文化、社會自身歷史演變的道路。西方學術界也沒有關于明清中國社會結構與歷史趨勢的現成答案,相關的研究能夠帶來很多啟發,但并無定論,且可見較強的歐洲中心主義。中國歷史演變必須通過歷史的方法即考察已然歷程的方法來認識,不能用演繹的方法來認識。后現代批評思潮已經揭示出“現代社會”存在種種局限,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人們都需要繼續思考社會合理性的建構問題。
研究范式的檢討
如果要研究一個涉及面很寬而又有許多前賢研究過的問題,就需對前人研究的范式進行剖析,已有各種相關研究范式在我的梳理中大致呈現為下述情形。
(1)中國學術界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偏重強調經濟因素必然帶動社會整體形態向某種世界性普遍同一的模式演變,理論預設性強,而實證依據不足。參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學者大多數偏重從經濟角度審視整個社會,“資本主義”在多數情況下既被作為一種經濟體系,也被作為一種社會形態類型。其背后的思維邏輯是,經濟體系會自然而然地確定整個社會的基本制度。但這是一種要素決定論的思維——無論經濟在整個社會體制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它都不能單獨“決定”整個社會體制。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初看是在討論經濟生產方式,實際的指向卻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體制,這是論證難以通透的原因之一。
(2)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促發資本主義說,提供了一種從信仰傾向角度解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的研究范式。后來一些評論者借助此一范式解釋20世紀中后期亞洲幾個國家的經濟崛起。這種范式對關注信仰方式于社會結構推演的作用有啟發意義,但因夸大宗教倫理引導新質商業精神的作用,忽視經濟、政治等諸多其他重要領域,并不能透徹說明明清時代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趨勢。
(3)伊懋可《中國歷史的模式》,提出“高密度陷阱”說。他承認明清中國經濟有一定發展,但依賴高密度人力投入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最終陷入發展停滯。他的所有分析資料都借助二手或更間接的資料。其說之重要性,一是雖然最終判定明清時代中國經濟還是陷入了停滯,但表達出嘗試擺脫中國歷史長期停滯說法的意圖;二是提出了明清時代中國經濟結構的一種模式說。該書對后來興起的加州學派影響很大。
(4)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強調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就已存在的商業世界體系的中心,白銀和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他雖沒有使用明清中國的原始資料,卻具有非常寬廣的世界眼光和理論性,比較深刻地闡釋了明清中國與世界大變遷的關聯。不過,他帶有依附論者刻意從非歐洲范圍梳理現代起源的主觀傾向,夸大了白銀和中國市場對現代世界興起的作用,沒有把前現代經濟、社會體系與現代經濟、社會體系之間的差別說清楚,當然也沒有正視明清中國的社會結構究竟如何的問題。
(5)加州大學黃宗智的明清經濟內卷化理論與伊懋可的高密度陷阱說很相似。“內卷化”指一種系統在發展到某種模式之后無法轉化進入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黃宗智將之重譯為“過密化”,指明后期以降“總產出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的經濟模式,這種通過過密化而實現的增長,不僅不會導致小農經濟讓位于大規模生產,甚至會因為單位勞動力報酬更低而阻礙雇傭勞動生產的發展,也稱“沒有發展的增長”。該說作為關于中國農村經濟結構的假說,對認識直到晚近的中國農村經濟結構意義很大,但是作為解釋明清中國社會結構和歷史趨勢的研究,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生產中的“過密化”與土地、人口數量高度相關,江南在明前期就已經出現土地不足,人口密度偏高,而其他諸多地區并無同樣、同程度的問題。而且明清繼替,全國農業可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就全國而言,“過密化”未必構成普遍事實。
(6)加州大學的另一位學者彭慕蘭提出“大分流”說。該說用GDP作為一個比較的尺度,判斷17世紀中國江南地區的經濟水平與同時期英國約克郡相當,到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發展水平才“分流”,而“分流”的重要原因是歐洲開始大量使用新的礦物能源。不過,把江南地區孤立出來與英國的一個郡比較,是無法說明作為整體的中國的社會歷史趨勢的。與伊懋可的高密度陷阱以及加州大學其他學者的研究方式類似,這種考察把歷史問題過分經濟學化,把經濟從復雜的社會、文化、制度中抽離出來,假定其在很大程度上單獨運行,這作為旨在建構模式的經濟學方法無可厚非,但作為旨在解釋歷史的方法顯得建構性過強而忽略的關聯事實過多。
如果窺測前人研究更深層的思想背景,還可以看到從魏特夫、馬克思到黑格爾,再到16世紀前后歐洲旅行家和傳教士言論影響形成的東方知識和東方意象中,有一條歐洲中心主義推演的線索。中國多數學者不贊成中國歷史停滯論,但反駁的路徑,大多是通過主張中國歷史符合世界歷史普遍規律切入,而他們心目中的“普遍規律”又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經驗為中心概括出來的,從而在研究的過程中常常陷入兩難。
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歷史停滯論緊密糾纏,其背后的思維取徑都與歷史單線進化發展觀和單一因素決定論有關。要突破中國歷史停滯論,就要突破歐洲中心主義;要突破歐洲中心主義,就要突破線性歷史發展觀;要突破線性歷史發展觀,就要突破歷史的單一因素決定論。
我們不能通過傍依前人來解決原初的問題。歷史的判斷和解釋不能與證據反悖,理論無論多高深,如果不與證據契合,就有修正的余地。我們可以把前人的研究路徑和結果做比照分析,辨析得失,嘗試梳理出一種最大限度規避其局限而又與證據最大限度吻合,同時在反向推論中找不到重大反證的研究路徑來。
我在研究中注意3個原則。一是結構分析,把所有社會視為“系統”,避免任何決定論,無論是經濟決定論、政治決定論還是信仰決定論,主張從整體構成的要素、方式、功能等多重角度來把握社會形態及其前景。二是實證,追求將所有理論性認識建立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所有前人的理論只被當作思考的資源,而不受其規定,不強找證據以就理論。如果發現理論與事實不合,就修改理論。三是文明史觀。歷史演變的最大差異在于文明的差異,文明作為最大的社會共同體,會在演變中形成各自特有的文化精神,滲透到其成員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制度中,從而,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推演潛質和傾向。各文明在逐漸增多的接觸中會有所融合,但也會長期保持各自的文化精神和社會組織方式的特質,因而不可能走同樣的社會形態演變道路。在這種視角下,明清中國與同時期的歐洲之差別不能完全用先進和落后來區分,也不能完全用經濟尺度來區分。
這樣看,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的方法論主要是在對已有方法進行批評性審視基礎上做出“綜合修正”的結果。這項研究最初是為梳理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后來調整為現代性在中國發生的緣起問題。但在保持對現代性在中國發生緣起問題的追問同時,我們還需注意,從社會結構與歷史推演的趨勢意義上說,明清中國究竟在發生什么?后者肯定與現代性有諸多關聯,但未必所有情況都可以被納入現代性發生的視角下來闡釋。至此,研究的問題擴展到從基礎概念層面開始重新認識明清社會和現代中國,從而具有了更多方法論和研究視角的意義,不再是對一個特定問題的解答。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的要點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研究的基本目標,是就明清時代中國社會結構、形態特征及其演變的由來與趨勢做出判斷。用最簡短的方式來概括迄今已經提出的看法,該說主張: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并沒有陷入停滯,而是發生了多方面的發展,并與該時代的全球化運動相關聯。依據其結構性特征,明清中國應被稱為帝制農商社會,而不是封建社會。這一社會的重要特征是,農商經濟共同構成社會基礎且與帝制國家體制形成共生格局。其演進的基本趨勢是,在帝制農商社會基本框架下繼續發展,有更大規模市場經濟化的前景,但沒有西歐同時發生的那種資本主義、議會民主政治的前景。該時代的中西方文明有交結,但推演路徑不同。具體而言,包含下列認識:
(1)明清中國社會沒有停滯,有多方面發展,尤其表現在商品經濟和市民生活方面。各種關于明清中國發展停滯的論說皆不符合歷史實際,但與“現代性”性質契合的“發展”并非均衡地展現在所有領域。
(2)明清是中華文明內聚運動基本完成的歷史時期,這是與“現代性”之發生不同的另一種意義上的發展,是中華文明歷史演變的特殊表現。
(3)明清時代中國的國家體制是帝制而不是封建制。帝制是中央集權的,由皇權、郡縣體制、官僚體制作為骨干支撐,不是層級分權的。帝制與大規模市場可以共生,封建則趨于自給自足或者地方市場。封建制作為歷史孑遺在明清時代依然存在,但并非國家體制的主導體制。明清帝制常態運行且趨于強化,并非處于自我否定、瓦解過程中,也沒有明確的向任何其他體制“轉型”的動向。從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從而自我瓦解的邏輯來看明清社會不得要領。
(4)明清社會不是完全封閉、“閉關鎖國”的,也不是完全開放的,是有限開放的。有限開放是帝制體系的內在性質,并不瓦解帝制,且可以提供對帝制的支撐。基于這種有限開放性,中國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歷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貢獻于早期現代世界經濟轉型,也受到早期經濟全球化的一些影響。
(5)明清商品經濟發展與帝制國家體制形成一種共生態。該時期形成了白銀貨幣體制、貨幣主導的國家財政體制,商業資本繁盛,出現較多雇傭勞動關系。這些現象在抽象的性質意義上與現代社會具有很大契合性,意味著具有很大的商品經濟發展前景,但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并沒有構成對帝制體系的解構,也沒有顯露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全面特征。明清兩王朝在明清商品經濟發展變遷中并非頂層設計主體,也不是一味阻礙者,而是調適適應者,是新水平商品經濟與帝制國家體制共生并榮格局的參與者。
(6)明清中國沒有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跡象。古代科技不足以推動工業革命,沒有工業革命則不可能形成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這一角度看,明清中國不僅事實上沒有,邏輯上也不可能先于歐洲發生工業資本主義。
(7)明清思想學術仍以儒學為主流,沒有文藝復興,更無啟蒙思潮。中國古典文化不曾斷絕,故文藝復興無從談起,梁啟超、胡適等人關于清代漢學是中國文藝復興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儒學有諸多優長,但并不孕育現代社會。
(8)明清國家政治、政治文化基本在傳統軌道上運行。其間具有歷史意義的轉折之突出體現:一是士大夫政治在明代出現了高潮,而在清代基本消失;二是貴族政治在明代趨于沉寂,在清代卻趨于復興。中外史學界都還沒有實現對明清政治歷史與經濟歷史推演之間關系的透徹說明。
(9)明清社會結構變遷也與帝制體系互洽。明代社會自由度增強、庶民文化發達,清代社會層級化增強、庶民文化繼續發展、社會控制強化。這些變化與帝制體制持續發展并行。明清宗教也由帝制國家統攝,多元并存。
所有這些要點皆表示,明清中國社會構成一種學術界以往熟知的各種理論、模式說都不曾具體闡釋的形態。對這種社會形態的探索、論證,有助于認識現代中國起源的歷史邏輯,也可能會推引出諸多歷史研究方法方面的新認識。
幾點回應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的核心主張已經初步表達出來,但還有若干重要側面有待專門論述,這里就同仁提及而我先前注意不夠的問題略做說明。
(1)既然明清時代農業依然是社會經濟的第一基礎,農業人口依然是帝制國家統治的基本對象,“為何將這樣的社會稱為‘農商社會’”?既然商業是帝制體系的內在組成部分,早在帝制初期甚至帝制時代以前,商業已經在經濟結構中占有一定比例,為何斷言直到明清時期才進入“農商社會”而不是更早?這些追問顯示出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中迄今比較模糊的一個側面,在把明清時代商業經濟的系統量化數據基礎上,才可以把這個問題說得非常清楚,而目前為止,這樣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在實現量化分析之前,把明清時代稱為農商社會的著眼點主要有3個。
其一,“農商社會”是從結構特征角度上擬出的稱名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農業和商業皆構成社會經濟體系中的支撐性產業,其重要性皆超過其他產業,并形成普遍認可商業價值的觀念的社會。與之相對應的,是商業占比很小并被普遍漠視的社會。商業在這個時代,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結構中僅次于農業的支撐性產業,其合理、合法性得到從政府到民間的普遍認可,市場、貨幣、商業都市的發達都達到空前水平,并促使國家制度、政策發生了深刻變動。
其二,明清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與全球化過程同步,深度卷入了當時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流動,與宏闊的全球經濟格局、體制變遷密切關聯,與現代社會的全球興起關聯,從而具有了與中國以往時代的商品經濟繁榮不同的屬性和大背景。
其三,帝制并不絕對排斥商業,而且會為商業提供大規模市場秩序條件、統一貨幣、大空間物流。但是,早期帝制對市場、商人管控過嚴,貨幣形態變動不居,勞役和實物賦稅比例很大,人身依附關系普遍。商業的自由發展空間在宋代大為改觀,但宋朝管理區域空間狹小,多政權并立使得制度環境穩定性低,且屢有更改。明初商業黯淡,到明朝中葉以后才進入商業持續發展的不逆轉過程,且覆蓋了廣大的地域空間。
(2)明代的白銀貨幣運行和貨幣財政體制發展是否意味著國家轉型?回答是否定的。明代發生了從實物為主的財政體制到貨幣為主的財政體制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意義主要在經濟領域,其次也涉及國家政治,但經濟層面的含義是確切的,政治層面的含義是不確切的。明清國家體制沒有發生明顯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轉型”。賦役制度和財政制度都與國家形態(類型)相關,但如果要以賦役制度或財政制度為著眼點來判定國家在某個時期轉變了類型,不能僅僅局限在賦役或財政領域,必須對國家類型做個直接的觀察。“國家”的“型”和性質判定,不是一個單純經濟問題。
(3)帝制農商社會說主張明清時代對外方針皆為“有限開放”而非“閉關鎖國”,但在講到與清朝同期的江戶時代日本時稱其為“閉關鎖國”時代,當時中國和日本皆有一定量的對外貿易,那么何以說法不同?說江戶時期日本“閉關鎖國”是沿用學術界習慣用法,這樣講的學者一般是指德川幕府在1633到1639年間5次發布涉外禁令,雖然17世紀的日本文獻中并沒有使用“鎖國”字樣稱呼這些禁令,但這些政策具有主動切斷日本與外界主要關系渠道的意味。同一時期的中國清朝,只在臺灣統一之前有遷海之令,一旦統一,立即展界、開海,并沒有同樣明確持久實施的切斷中外往來的鎖國政令。其實,無論江戶時代日本還是清代中國,都沒有處于與外部世界完全隔離的狀態。